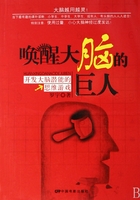要是被父亲知道,自己的女儿整日去青楼,与那里边的花魁是师徒关系,还教着那样不知羞臊的舞,不得把燕柔儿那层皮拔下来。燕柔儿还未及笄,虽然模样娇艳,但毕竟还是个少女,燕家虽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但好歹也是个大户人家,更何况有着四王爷这层关系,燕柔儿虽然是个庶女,日后找的夫君也不会很差。如今却自毁名节,要是被外人知晓纷纷宣扬,那时燕柔儿就不光是燕柔儿了,还连带着整个燕府的名声。
燕景铄整日浸染在花街里也就罢了,燕柔儿在众人面前展现暴露衣着……唉……
燕小凰不禁叹了口气,要是想要印证醉花楼里的人是不是她那庶妹,如今倒也简单,去那醉花楼里边问问那师傅今日有没有去,便晓得了。若是那师傅照常去了,那一定是认错了,若是不在,就有可能是正受着毒发痛楚的燕柔儿。她的身份去醉花楼是万万不合适的,旁的不说,要是被眼前这个小子知道了,她恐怕以后也没有底气教训他去烟柳之地了。可是叫谁去好呢?素锦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去那里也不合适,看来还是要想一想人选了。
她用糕点堵住燕景铄的嘴,“别叫了。”
“怎么会是她?这……姐……你确定那女人身上也有那样子的一条疤痕?”燕景铄吞下糕点,情绪渐渐冷静,语气旋即变得十分冰冷。
他拍着衣袍上沾的碎屑,随即索性站了起来,活动了下双腿,给姐姐面前空空的茶杯填满,又坐下来,品了一口茶。像是瓷器般白净的脸上与之前玩世不恭表情不同,此刻严肃认真的望着燕小凰,食指弯曲,骨节有节奏的轻叩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是他的老习惯了,小时候一有着兴奋的事情,就不停的敲着桌面,被燕母和大哥管教多次,无果后只能放任他有着这个坏习惯。
燕小凰指腹揉着发疼的耳廓,板起来脸低声警告着,“我自然是可以确定她身上有这条疤痕的,小时候她神智还未恢复的时候,你也不是不知道,她最喜欢粘着我了,我经常帮她洗澡呢……对了,这事还没有调查清楚,你可别去外边嚷嚷,省的打草惊蛇。”
燕景铄别扭的一撇头,像只骄傲的小公鸡,语气愤愤,“哼,想到那时候你那么疼她,我就来气!照顾她都不如照顾一条狗,姐姐若是养了一条狗,如今还会讨好你对你摇尾巴呢,结果那女人呢?整日里陷害你,这次居然敢叫那燕暮彦欺辱你,我看老天爷是有眼睛的,她中毒真是报应。”
“好啦好啦,你说话这么大声叫旁人听去了,要是有人和周氏告状,姨娘在父亲吹吹枕边风,父亲又得教训你。”
燕小凰本想说完让燕景铄说话小声点,哪知道这一下子,反倒宛如一条无形的导火索,使得燕景铄身上的火焰迅速涌起,激起他的叛逆之心,令他比原本的语调加了一倍音调,不停的吼着。
“我才不怕呢!如今我亲姐姐被那可恶的女人欺负了,我说两句父亲还要责怪我!哪里有这个理!”
她戳着弟弟气鼓鼓的两腮,问道:“你能证明这事与燕柔儿脱不了干系吗?”
“这……”燕景铄面有难色。
“做不到的话,就闭嘴。我知道你心疼姐姐,但是姐姐何不心疼你呢,你要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打伤了,母亲得为你哭一场,我也得难过一场,大哥在边疆不知道这消息就算了,要是知道了,也得气的上火。谁会笑的最开心?还不是你最憎恶的那燕柔儿?”她瞧着弟弟仿若霜打的茄子,蔫蔫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知道弟弟知道错了,她语气也软了,“好啦,不谈这个事情了,话说回来,你趁早给我离那如意姑娘远一点,要不下次我告诉了大哥,让他把你好好修理一顿。”
“姐……”
“叫娘也没有用……”
燕景铄瞧着燕小凰严肃的目光,他乌黑的眼睛滴溜溜一转,转移话题,“以后我就不和如意姑娘来往了,你就别告诉母亲了,关于燕柔儿我也想起来一点,那人首次见到我时确实显得有些慌慌张张,手足无措打翻一盘糕点,还不小心的被桌子绊倒,狼狈的爬起来后就跑掉了,如今想起来可真是怪异极了。”
“是很怪异,燕柔儿何必去青楼当师傅赚银子呢?母亲当家主母的大气还是有的,虽然恼着姨娘那边,但该给她们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
燕景铄抿着唇,思忖几秒,脸上浮现一丝窘迫,声音干巴巴的附在她耳边说道:“听说燕柔儿沾上了点麻烦事。”
她疑惑的皱眉。“何事?让她不得不用这种法子筹钱?”
“之前她不是开了个小铺子么,卖着姑娘家家的东西,我可没有去过啊!和我一起经常去醉花楼的朋友……这个只是传言,因为我和他关系好,在酒桌上他喝的迷糊了才愿意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本来我以为是他说的胡话,直到联想到今天发现的事情,才发现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那只能算是酒肉朋友!”她一拍桌子,认真的说道。
“恩恩……就是酒肉朋友了,酒肉朋友也是朋友嘛。家里的三妹经常去燕柔儿的店里买着东西,回来用完,那处……咳咳,那、那处就是女人的那处……咳咳,用完之后沾染了什么病,开始长着红疹,刚开始燕柔儿就给她找个郎中治一治,哪里知道后面会越来越严重,听说如今已经溃烂,那张家三妹整日以泪洗面。”燕景铄尴尬着磕磕巴巴的讲着,“现在出了那事,燕柔儿为了不让人来府上闹事,不让父亲知晓,不得不用钱给她嘴堵上。”
她皱着眉,心里想着仅仅是棉花,怎么会害成这样,难不成是为了缩减成本,偷偷用了不干净的布料?她不禁有些同情那张三姑娘,要是染上这种病,哪怕以后治好了,也不容易找个好婆家了。
燕景铄又补充着,“都怪她非得在那里边加什么草药,乱加些香草还有其他草药,那姑娘自来对草药就敏感,哪能受得了这个。”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那么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