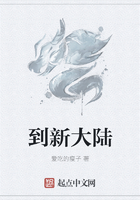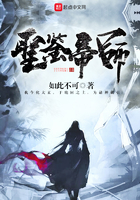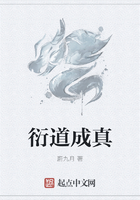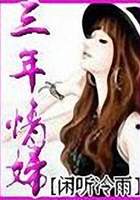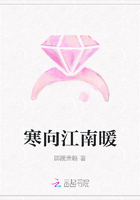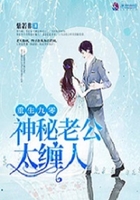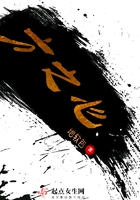十月一十七日于登基大典毕,凤霞嘱咐众人方今尚未一统,连年战事百姓举步维艰,万不可铺张浪费、沽名钓誉、怠惰因循、不思进取,更不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十月一十八日,罢乐,改易官职职阶。
封耿秉文为右柱国,正一品,领兵十万向西追击邓晟;封李进为上护军,正二品,领兵五万向北戍边备盗;永忠赐卢姓,封昭毅将军,正三品,仍旧护卫京畿。其余将军按功劳、德行各有升迁。
封宋基为左丞相、郦纪信为右丞相。因民之便制定律法,务使公正简便,不得使民疑虑无所适从;勘定山川河泽、府库人丁;又裁定各将士官员功劳品级;擢德才兼备之人,授府州郡县官吏,赴各地上任,规定三年一考,不称职者由替补人员当场继任;与他国互通来使。
着永忠派人寻访往日故旧,凡有恩者,观人所好以报恩,但不可违悖公序良俗、国纪礼仪,尤其当厚谢陈氏一门。
当此大业初创、百废待兴之时,一切从简。似此论功行赏、逐次议定;集中兵力、慎选将领、平叛讨逆、军需用度、给养护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办学重教、开科取士;修好外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凤霞在太学外游荡的时候,尝听人言:凡才与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连绵不绝。便在局势稍稍稳定之后,带上永忠,轻装简行,化妆成一般富家子弟,往长安各处微服私访,广纳挚诚之言。
一日,二人骑马来到长安东南郊二十里处,见有一处私塾,适值午时光景,一位先生正端坐堂前读书,想来定是在为孩童备课。凤霞看这先生肤色深黑,眼圆脸长,伏犀骨耸起,让人望去便有一股正气,便与永安下得马来,口称来讨杯水喝,便与先生分主宾坐下攀谈。寒暄过后,凤霞便问道:“先生,这连年战乱,孩子们是否愿意好生学习,将来做什么有出息?”
先生前倾说道:“私以为,方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必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允文允武,因材选用。大多孩子在几岁时便能看出其志向,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个孩子志向不同,这从小便能看得出来。然后做老师的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好生引导,让他往正确的方向努力。社会也应该营造出一个公平开放的氛围,允许那些无害于他人的正确思想和尝试在社会上流动,似那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而不能禁锢百姓思想、以愚民为要。”
凤霞以为然,点头称是。
先生接着说道:“每个学生天生的智慧、精力、情趣都不一样,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去做高官名将。有些孩子喜欢发明创造,那就让他去做手工手做、去读方志这类有关的书籍;有些孩子喜欢史料古籍,那就用吕氏春秋这类书籍勉励他;有些孩子自幼身强体壮,喜欢舞枪弄棒,那就用以德为先、保国安民的兵法书来规劝他;有些孩子看起来将来会做工,那就让他们读些竹林七贤一类能时时自我排解的书籍;有些孩子不爱读书,只能教他们识字,能识别字面含义即可。”
先生喝了口水,继续说道:“当然,一切都是变化的。有些孩子本来不爱学习,却在十几岁忽然开窍,奋发努力,反而又强于其他弟子;有些孩子遭遇变故,致使情趣大变,转而往其他方向发展。诸如此类,为师者不得不察。当然,读书是一方面,人的志向是另一方面,听说当今天子不爱读书,却能再造乾坤,想来其中必有道理。”
凤霞接口道:“时也命也,所谓时势造英雄吧。”
先生看了凤霞一眼,接着说道:“孩子们还小,还没有什么分辨能力,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如果国家能给每个孩子提供一些学习的场合,比如喜欢手做的孩子,可以去国家的科学部门组织的场合参观并学习,那对他的启蒙和成长之路将会非常有裨益;那些喜欢与同学交易的孩子,可以锻炼他们的思维敏捷和反应能力,长大或为外交人员、或为商人;那些爱好布阵演兵的孩子最好有专门的军校,培养后为朝廷所用;而那些喜欢做工与精力不足的孩子,可以根据长安附近所需人处,教他们学习耕织洒扫、计量估算之法,让其早日联通社会。”
凤霞深以为然,连连称是。
先生又说道;“承蒙公子不弃,方才说得笼统,不知公子是否有疑虑处?老朽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凤霞忙道:“都懂了。先生可否教我,我经常能听到、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比如动物说话、非人类说话、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不知何故?”
先生怔怔看着凤霞说道:“老朽不知,大概是这世间真有人力无法探知之事吧,凡人静守本心即可,就像孔圣人那样‘子不语,怪力乱神’。”
凤霞又问道:“似此这般,如之奈何?”
先生站起来说道:“公子面相异于常人,因屈尊问老朽孩童教育之事,老朽定当如实回答,现在公子问的事,让老朽想起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愿公子自爱,老朽还有私塾要教,就不留公子了。”
凤霞还欲说些什么,永忠闻言,忙拉住他,再三向先生道谢后,便要匆匆离去。
老先生看了看永忠,又说道:“公子,教育乃国家大事,不可不仔细行事,万不可因老朽今日之言,便把孩童分个三六九等,过早泯灭了他们的心性、堵塞了他们突破现有阶层的道路,那样老朽就成了罪人了。老朽做罪人自当在地府谢罪,而国家人才的流失才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损失。公子在百忙之中当时时检验下人所作所为,万不可画虎不成反类犬,做出适得其反的错事。”
凤霞忙深揖一躬,带着永忠径自走了。
一路上凤霞感慨万千,诚愿老者做自己的良师益友,但又想到自己只问了自己虚无缥缈的琐事,而不是国计民生,心下惭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