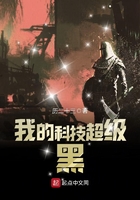那张观疼得嚎叫,可抵在末路,他退不得;前有沈琛,他又不敢。这时只好往两边挪动,可沈琛不肯作罢,双腿换着教训,只当是拦个蹴鞠。
没一会儿,张观发冠散乱、蓬头垢面,整个人都灰蒙蒙的。
沈琛出了一半的气,伸手抓起他的衣领,将他丢去角落。这青年身板瘦削,不想气力不小,上天下地都不在话下似的,哪里看得出一点心梗症的影子。
“道咒背得倒是熟练,想你学了个头就当自己功成。不吃苦还想发财,白日做梦也要有个限度。”沈琛气笑,“我问你,‘彩门’里头‘三仙归洞’那手,是个什么要领?”
张观眼底发昏,哪里听得进这些。沈琛哼哼鼻子,一栗子敲在他脑门上。
他又问:“‘落活’的冷火,都藏在什么地方?”
张观清醒了些,瑟缩地试探:“……袖子里?”
“呸!”沈琛气道,“什么都塞袖子里,你当真有什么百宝袋?学个鸡头就想做凤凰——滚开,别叫我在新城瞧见你。”
张观只当是见了祖宗,被打骂得破胆,哪敢再提收不收徒的事儿,手脚并用地爬了出去,影子化在冬阳里。他太过狼狈,连着路人都纷纷驻足往他看去。
巷道又暗又小,风更冷些。我讷讷地没说话,倒是沈琛打了个颤,骂道:“鬼天气,都作到狗腚里去了。”
他很快又收敛火气,眉目含笑、神色轻松,负着双手得意洋洋地踱了几步。
“诶呀阿砚,你怎么脸色不好?”
这厢还是嬉笑着的,绕着我走了两圈,最后弯下腰凑近我,连鼻息都轻浅清晰。
我哽了一下,不知要说什么,便不经脑子胡说道:“你骗我。”
沈琛挑挑眉角。
“哪里骗你?”
我说:“原地暴富——结果一个铜板都没摸到。”
他哈哈大笑起来,几乎要背过气去:“你看,这不就是。”
沈琛不知从哪儿变出个囊鼓鼓沉甸甸的麻布袋子,被坚硬物什填充出些许棱角。他掂量几下,内中东西便磕出细碎的声响。
我眨眨眼,这才懂得他听了故事怎也一点不为所动。感情是那张观张口就来,不知沈琛早已识破、仍编撰着悲惨经历。
他骄傲极了,鼻尖儿快要促到天边去。一下开了钱袋,数出十两碎银。
我虽心觉怪异,可咱没必要与银子过不去——有钱不赚是傻子。
毫不犹豫接下,我摆摆手。
“两清,告辞。”
新城东边喧闹繁华,我又喜欢热闹,便有意不往冷清的地方去。租了间客房,那掌柜见我面生,果真想讹诈我。
我知道街边小传里,世外人家入世皆是懵懂。我琢磨着咱也不是痴傻,但凡是看了书温习过功课的,总出不了大问题。
我与他讲究:十铜一晚不能再多,我本长住,什么不是花销在这店里?
这客栈朴素,没得精装漆镂。外来人客在此晃悠,多半不差钱,为的舒坦都去大酒楼里,相比之下这处人就少了。
掌柜的硬着脖子,手指按在算珠上,生硬道:“二十铜。”
我正要还价,忽瞧见一丰腴女子从后厨探出头来。与之一同的,还有浓重的熏香滋味。
我瞧她面色,便对掌柜道:“十五铜。”
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