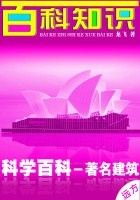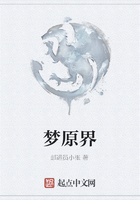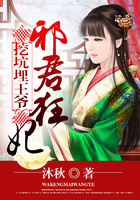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09年第8期。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谭冰若先生召我去他家,一同观赏刚刚托人从日本带回的录像带——瓦格纳那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入夜,在谭先生那间当时看来还相当宽敞的客厅兼书房里,就我们师徒二人,对着电视机,在瓦格纳时而激越、时而低回的乐声中,一边品咂小点,一边小声交谈。因录像是在日本制作,尽管演员、乐队都是西方“老外”,但字幕却是日文,我的第一外语是英语,完全不懂日文,只能听谭先生讲解。记得谭先生当时兴致不错,对剧中音乐和演员演唱常常赞不绝口。临了,在我走之前,谭先生半开玩笑对我说:“偌大的一个中国,关在屋子里看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此时此刻也许就我们两个人吧!兴许有人会说我们是神经病?”
这幕小小场景,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其时,我正师从谭先生在上音音乐学系攻读硕士(西方音乐史专业)。当时的音乐院校,招生规模很小,研究生更属于凤毛麟角的稀少品种。我们那一届研究生(1983级),上音全院总共就招了四名,钢琴系、作曲系、音乐学系、管弦系各一名。而谭先生门下,很长一段时间中也就我一个研究生(大概直到1985年以后,先生才又招入其他研究生)。因此,谭先生给我上课,常常是一对一的“小灶式”,而且总是在他家中。现在回想,那真是一种别样的“豪华”:一位名教授,仅仅指导一名研究生——这种光景,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恍若隔世,恐怕更是绝无仅有了。
师徒二人,一带一,整整三年里,我就这样跟从谭先生就学,并开始真正步入音乐学之路。说老实话,在考入谭先生师门之时,音乐学这门学问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音乐史中究竟有多少堂奥,这对于二十岁刚出头的我,说有“一知半解”那都是过誉。那套当时在国内专业音乐(学)界几乎人手一套的“光华版”二十卷英文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The New Grove 1980),直到我入谭先生门下,才知道其重要性——但随后就吃后悔药:因为“不懂行”,没有及时买下,等反应过来,书店里早已脱销,真是追悔莫及。“光华版”《新格罗夫》的第一次印刷质量最好,价格也便宜,装帧挺括,字体清晰,偏蓝的绿色外套封面上用烫金字,煞是好看。但既然“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无奈之余,只能等随后的第二次印刷。结果,这第二次印刷不仅价格上涨,而且质量也大打折扣,字迹清晰度下降,灰白色的外套封面也显得土气。至今,摆在我书架上的还是这套显得陈旧甚至有点邋遢的灰白色封套的《新格罗夫》。每当我翻阅这套辞典查找资料,总不免有些犯嘀咕,心想要是能早一点跨入谭先生师门,手中捧的就应该是那套绿色封面的《新格罗夫》了。
说起《新格罗夫》,我正是在谭先生的驱动下,才开始熟悉并频繁运用这部大辞书的。在我硕士一、二年级时,先生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教学方式:不是他给我直接讲授,而是要求我将西方音乐史的主要内容自己整理并每次回课给他。当时的中文书刊中,二十世纪之前的内容还较容易找到一些参照。但关于二十世纪的音乐,不仅很难找到中文资料,而且即便有,也是零敲碎打,不成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势的逼迫下,我只能直接向《新格罗夫》“求援”。为了到谭先生处回课,我几乎天天“泡”在学校那座优雅而清静的“老洋房”图书馆楼(1949年前曾是比利时领事馆),主要就是待在三楼的外文阅览室,查看《新格罗夫》中的二十世纪音乐条目。在回课中,先生不断给我鼓励,并及时通过他的日文材料给我补充,这自然更增加了我阅读外文并将其消化成自己知识储备的信心和乐趣。一段时间下来,我已将《新格罗夫》中一些二十世纪重头作曲家的条目看遍,并记满了整整一大本有关这些作曲家生平、创作及风格的笔记。也正是通过如此这般对《新格罗夫》的集中阅读,我不仅对二十世纪音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熟悉了学术性英语的表述方式,英文阅读速度和理解力均大有提高。谭先生在上课时特别提到直接阅读原文的重要性,并曾指出有一位他就学时的同学在写论文时,由于没有查对原文,结果将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和德国作曲家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完全搞混淆的错误。
除个别上课之外,谭先生还要求我同时参与或旁听他给其他本科生和进修生的相关课程。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应该是到谭先生家中,大家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聆听相关的音乐作品,并进行相应的讨论和交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远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找到相关的音像资料。谭先生一直用心收集各类卡式磁带等,堆放在他客厅兼书房的书橱里和各个角落中。谭先生会翻看一个笔记本,上面分门别类记录着各盘磁带的编号和内容,以利查找。我们一起围坐在谭先生家中的沙发或椅子上,一边享用谭先生给大家准备的茶点,一边听谭先生讲解并听赏当时还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现当代西方音乐作品,诸如马勒《第八交响曲》、蒂皮特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乔治·克伦姆的《远古的童声》等。记得我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读到而是从音响中直接感知贝尔格那部“前无古人”的重要歌剧《沃采克》,就是在谭先生家中。谭先生特意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了唯一的一本声乐—钢琴谱,对我特别优待——和另一位进修生共同看谱聆听,其他学生则只能“光听不看谱”。谭先生按照幕次顺序,每一场之前先讲解故事梗概和音乐结构,随后播放录音。因为该剧时间很长,我们似乎只听了其中的第二幕,但就这样也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就我个人而言,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因为我似乎第一次切身感到了,针对如此“反常”的剧情和人物,只有使用“反常”的无调性刺激音响,才能够达到这般富有爆炸力的效果。
后来,开始有了歌剧的录像带。谭先生总是想方设法找来,并邀请大家到家共同欣赏。有些特别珍贵但并不适合“普及”的歌剧录像,他会询问我是否有兴趣来看——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一次,谭先生弄到了歌剧《蝙蝠》的录像,很是高兴,特邀音乐学系的所有本科学生(一共也就七八个人)和我一起到他家观赏。《蝙蝠》当然是一部悦耳动听而且特别“搞笑”的轻歌剧,谈不上深刻,但从头至尾贯穿无伤大雅的风流趣闻。那天,在场的学生们包括我都非常愉快,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到第三幕,由于舞台上的滑稽表演,有时甚至放声大笑。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一情景,是因为通过谭先生的讲解,我第一次领悟到,这部歌剧的“搞笑”不在音乐之外,就在音乐本身:比如第一幕中那对相互不忠的夫妻(爱森斯坦和罗莎琳),他们的“心猿意马”和虚情假意,就切切实实写在音乐的音调性质中。幽默效果的主要产生源是音乐本身,歌词反而成了帮衬。真正的音乐戏剧中,音乐应该承担什么功能,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
现在回想,尽管当时在谭先生门下,我并没有认真地触及歌剧理论本身(我的硕士论题是有关钢琴音乐从浪漫主义到印象主义的风格转变),但通过谭先生的带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歌剧剧目观赏和理解经验,这为我日后真正走入歌剧研究与批评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多年以后,当时也曾在谭先生班上就读的进修生、现任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副主编的田可文教授曾与我谈起,说我的学术风格和路线,其实有很多谭先生的影子在。我暗自思忖,老田的这个观察,大概不无道理。除了痴迷于歌剧这一点我与谭先生相像之外,我在音乐上跟随谭先生的路线好像还体现为另一方面。谭先生一直强调音乐理论和音乐学者应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并为此身体力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音乐爱好者开设各类普及讲座,并赢得很大社会反响。而我近十多年来,一直特意针对“乐迷”,特别是知识分子爱乐者撰写普及性文章,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并走入音乐,这从某种角度上看,不知是否可算作是对谭先生思路的某种继承?毕竟,音乐学的理论研究和写作,如果缩在音乐界内甚或仅仅封闭在很小的专门圈子里,其真正的社会文化意义又如何谈起?
光阴似箭。转眼,通过我的同学兼好友万建平(现任香港城市合唱团声乐教师、指挥)结识谭先生,算算至今已有二十六七个年头了。现在的谭先生,尽管上了些年纪,但依然每天沉醉于音乐中,从事歌剧和演唱的教学。每当乐声响起,谭先生仍会情不自禁地提气挺胸,优雅地随音乐点头晃动。我作为谭先生的学生和晚辈,在此祝愿敬爱的先生在音乐的陪伴下,颐享天年,舒心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