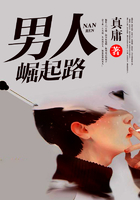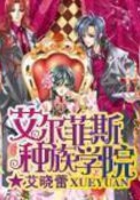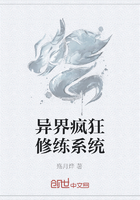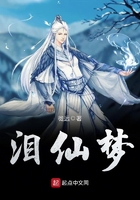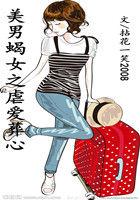一、对主要审美走向的分析
近年来,在创作上呈现出几条大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题材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意识的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首先,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其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对农民问题讲得最多、最透彻,中国革命被称为农民革命,中国文学里写得最充分的也是农村和农民的形象。“五四文学革命”曾以启蒙精神揭示沉默国民的灵魂,往后的“革命文学”则大力描绘农村革命史诗,以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为之留下了大笔财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乡土有着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但事情已经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尤甚。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神影响力上依然是以农村为重头戏的话,那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何以会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中等收入族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因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了。
有人认为,未来代表汉语言文学发展水平的,不再是乡土文学,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和后现代问题,但并没有估计得那么重要,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才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文学将从根本上丧失力量。的确,“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似乎越来越不在文学视野之中,不少文学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国问题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急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环境主题、乡土语言、底层意识等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马山庄》、《好大一对羊》等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发挥写实主义的感染力的同时,努力超越题材表层的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但类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现在,文学界强调“三农”问题重要,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的声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号召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还是用熟知的一套观念写农村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接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是怎么呼吁也没有用的。
第二,随着题材重心的大幅转移,“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的关系构成了当今审美意识中非常突出的矛盾。这不是指哪一种题材,而是渗透于几乎所有题材中。人的欲望固然从来都有,但在今天,也许由于利润法则的刺激,也许由于商品化、实惠哲学带来物质对精神的覆盖,总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无形中成为文学描写的重点。在大量作品中,围绕各种欲望展开的矛盾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权欲、钱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暴发欲、破坏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习见的场景。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欲望化写作”,有人干脆自称是“欲望现实主义”。这是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密集图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也是某种生活真实的反映。例如,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批评文学中的性描写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为文化符码,洗脚屋、桑拿房、壮阳药、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既然如此,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写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写。
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意蕴深藏的都市文本毕竟不多。比如,这种欲望化倾向表现于某些官场小说,是辞气浮露地渲染贪欲,腐败,孤立地而非整体性地表现“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来越弱。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都市小说,是商业化影响下的浓厚的大众文化趣味,突出展现物欲渴求和感官体验,主人公活动的场所不外酒吧、歌厅、咖啡屋、发廊、商厦、股市之类。这被称为时尚化文学,它的土壤是发达的时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女性主义小说,是注重私密体验,解构启蒙话语,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独特性及其人文诉求,表现她们在与男权、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声。不可否认,性是这类创作的敏感点、中心点,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往往是从这里入手的。这当然无可厚非,其打破传统观念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肯定。然而,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内涵稀薄。它们超越人文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要真正深刻起来是否应该再超越性别话语,回到人文话语?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使这种“个人化”日渐“干涸化”,生发不出崭新的意义,整体上缺乏足够的精神维度。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少作品不能令人满意,根源在于,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不足,没有高远的道德理想吸引,没有对人性的深刻分析,没有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大力肯定。这里,“身体写作”也许是个关键词。有的论者强调,身体是写作的起点,作品的思想、意蕴、语言,无不带有作者身体的温度,他们批评不“从身体出发”的写作是“面具写作”,他们说,如果传统作家注重的是“精神”,那么新生代作家注重的是“身体”,而“身体”不可避免地与欲望联系在一起。就尊重个体反对禁锢而言,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文学的根本审美特性是精神性的,“身体”与“写作”之间,最不可缺少的中介仍是灵魂和精神,与其推崇“身体写作”,不如鼓励“灵魂写作”。因为精神的缺席,才有了从“身体写作”滑向“下半身写作”的恶谑一途。
第三,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也是贯穿在当今文学审美意识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无疑是一大进步。于是,知足常乐,健康长寿,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物质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虚幻意义,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生活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影响到文学,便是近二十年大幅度向真实生活的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归,向写实主义的回归。“新写实”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说的大受青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衰,“朴素现实主义”的流行,均与此不无关系。比如池莉的受欢迎就值得研究。有人称她的语言是“唠叨文体”,这种“唠叼”可能正是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庞大,其生活化、实惠化的话语现实,是市民心态和趣味的对应物。
这些世俗化思潮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持续不变日渐凝固化的文学状态,未免显出了疲惫之态(不错,“韩剧”也是家长里短、芸芸众生,但日常化的背后似有道德自信、伦理激情)。其中与文学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软所造成的明显空缺,大有关系。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肯定需要开拓精神的激扬。但是,我觉得,在扬弃了伪崇高和伪浪漫之后,我们的文学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没有现实的英雄偶像,人们只好到古代传奇、新武侠小说、好莱坞大片中去寻找替身、寻找满足,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终非长远之计。从《英雄无语》、《解密》、《西去的骑手》等一些尚能发出审美异调的作品的受到注意,从《三国》、《水浒》、《长征》、《英雄》等影视片的热播,不难感应到此种消息。“一地鸡毛”式的仿真写法开始让读者不耐烦了,但要写出现实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难度依然很大。有人作为一种成功秘诀介绍说,写现实要写普通人,写古代要写英雄,把写现实中的崇高视为畏途。看来,当代文学要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
第四,解构历史、消费历史与历史理性精神的矛盾,是当今审美意识中的又一重大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表现出强烈的重述历史的欲望,这其实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企图通过重新阐释历史来肯定现实中欲肯定的东西。总的看来,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突出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可说是个大转折,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也与突出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密切相关。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极端:无条件地讴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学。
有些作品在歌颂帝王时,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皇帝塑造得可亲可爱可敬,十分高大全,无形中在张扬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集权政治。连张艺谋的《英雄》也未能逃出这一思路。它们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实在脱节。当然,怎样做到在肯定圣君贤相时把一些很难不夹带进来的消极思想剔除出去,无疑是创作上的大难题,需要深入辨析。随着市场价值介入历史题材领域,另一倾向也在左右创作:制作者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争宠、夺嫡、篡权、谋位方面,形成了一套以权谋文化为中心的构思模式和叙事策略。他们表示,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不能说毫无根据。那么,老百姓究竟为什么喜欢?从深层来看,还是因为触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场让人联想到现实官场,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让人厌恶,又让人艳羡。与此同时,是“戏说”的风靡一时——把历史作为消费对象,作为喜剧和闹剧的原料库,不断“搞笑”,不过是拿历史做由头而已。历史学家格外看重的“历史真实”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应该看到,历史题材创作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解构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反应,带有某种必然性。即使某些戏说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让青少年误读了中国历史,那问题就大了。显然,这一领域存在着纷纭缭乱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做得太离谱,已违背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此五色杂陈之时,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就可以了。
第五,作为当今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改写改编中出现了所谓“人性化处理”问题。这已不是单个现象,而是趋之者若鹜,形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我以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对红色经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读甚至加以改写改编,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红色经典如《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改编,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编,都是例子,《悲惨世界》被改编了七次之多。
我国一些红色经典的被重新发现,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它们并不是简单化地扣上一顶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宫的。艺术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作家宣称的思想与作品实际的形象系统,错误的观念与充满血肉的人物,当时的美与现在的美,都有可能构成多重价值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以描写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红色经典本来没有太多市场价值可言,可是,事物的两面性在于,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实又是具有某种“潜价值资源”的,只是有待于发现。什么“潜资源”?首先是,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匮乏的英雄情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但是,英雄的个性化、性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有可能成为新的卖点。这也许就是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认,它的背后有市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