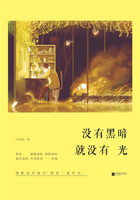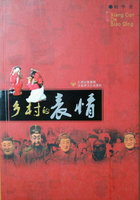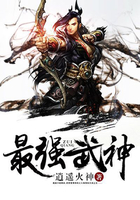王熙风在《红楼梦》里第一次接见刘姥姥时,随口说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大有大的难处”。彼时彼地的王熙风口出此言,一方面当然带有几分“端架子”、“摆谱”的意思,另一方面也确确实实泄露了她在荣国府初掌家政企图励精图治而受到上下左右掣肘的难言之隐。不管怎样说吧,这句名言饱蕴了王熙凤一份治家理财的经验和智慧,一种为人处世的精明和练达,甚至还闪现出了某些朴素的辩证法眼光。而且,这句名言还充分表现了汉语言的神奇魅力,它简朴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之间的鲜明反差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弹性和张力,使它实际所可能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特定语境所规定的治家之谈,它甚至可以成为“×有×的×处”的公式而随意套用。——譬如,在我们即将展开的关于长篇和短篇等小说样式的讨论中,就可以很方便地这样做了。
我们先说“长有长的难处”。
是的,写好长篇确实不易。因为它所要求的构架的宏大与严谨,人物的繁复与多样、主旨的深厚与丰满、文气的磅礴与连贯,才情的充沛与丰瞻……任何一个作家要想将这一切驾驭得得心应手,都不能不感觉到嘎嘎其难,也正因为其难,人们才往往把长篇小说的成就视为衡量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水准的标尺。同样因为其难,人们也才常常告诫那些初学写作者,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稀里糊涂地干长篇,而是要从短篇开始练笔,由短而长,先易后难,如此这般,语重心长。
一般说来,这种劝诫是正确的。尤其相比较长篇而言,短篇小说的确篇幅短小、人物单纯、结构简单,是比较易于学习和掌握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短有短的好处。但且慢,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短篇小说好写,甚至仅仅把写作短篇看成是创作中、长篇的一个过渡,一个“练笔”阶段,从而忽略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要素,那就误会得比较严重了。我们既要看到“短有短的好处”,更要注意到“短有短的难处”。
短篇之难不见人言为时久矣。
短篇何难?
首先,短篇小说是有崇高地位的,它和中篇、长篇鼎足而立共同支撑着小说的庞大家族,它决不是中、长篇的附庸或“副产品”(有些人总喜欢把中、长篇的“边角料”处理成短篇,这种做法并不聪明)。文学大师中固然更多的是因其长篇而成名,但同样也有像梅里美、莫泊桑、契诃夫、茨威格、欧·享利、都德、鲁迅等一批主要是用了短篇来奠定地位的小说大家。同样作为世界名著的一部短篇和一部长篇,其容量和分量当然是有大小与轻重的差异,但它们的艺术晶位却无疑具有相同的高度。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我们只能说长、中、短篇小说都各有价值、各有千秋、各有特点,要经营好其中任何一种都决非易事。换盲之,也就叫做“各有各的难处”。
笼统地说,短篇小说难就难在一个“短”字。这似乎有了一点悖论的意味了:易也在短,难也在短。
是,也不是。这要分两层意思来讲。其一,对于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初学者而言,短篇因为其短,它总是便于分析、便于揣摸、便于把握也便于临摹,一句话,学习创作,从短篇“入门”易;其二,入得门来之后,你还想继续登堂入室,窥其堂奥,得其真谛,写出她道的短篇精品来,那就大不易了。因为其短,首先在篇幅上就有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正好比“戴着镣铐的跳舞”,你就不能像在长篇小说中那样纵情挥洒,天马行空了。而且,短篇的短,又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短小而已,形式的短小同时也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必须精良。准确地讲,短篇小说应该叫做“精短小说”。它不是短而空、短而泛、短而滥,而必须是短丽精——精悍、精巧、精致、精美,短得有内容、有意思、有看头、有味道……所以,短篇小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鲁迅语);它最重剪裁取舍和谋篇布局;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是高质量的,从而保证人物的生动、情节的慎密或意绪的流贯与意境的浑成;它对语言的要求尤为苛刻,甚至遁篇不能容忍有一句废话——如果说在一部总体上比较出色的长篇中有个别章节写得比较“水”还能叫做“瑕不掩瑜”的话,那么在一篇数千字的短篇中哪怕是出现一个小自然段的“漏汤”也极有可能破坏全篇的和谐,甚而导致整部作品的“砸锅”……如此看来,短中取精又何其难哉!
怎样才能做好短篇,无疑是一个大题目,不可能在这里说得明白。我只想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短篇小说的形式问题,即短篇小说首先必须是真正的“短”篇小说。
简单问题解决起来并不见得简单。如前所述,短篇小说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决定了它的内容,研究、写作短篇小说首先就要解决一个“短”字。短篇不短,何谓短篇?然而毛病恰恰就出在这里。像鲁迅所说的把一个短篇的材料硬拉成中篇的人固然是对短篇(当然也包括中篇)艺术的轻慢,同样,将一部中篇的内容硬塞进到一个短篇里去的做法也并不是对短篇艺术真正的尊重。遗憾的是,遍览今日小说界之情状,不能不让人感叹短篇艺术之知音难觅。根据我的大略记忆,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届全国获奖短篇小说中,万字以内的短篇佳作确属麟角凤距,相反,两万字左右的“大短篇”倒时有所见。短篇创作中长风日炽,精品渐稀,短篇不短,已成通病。无怪乎数年以前就有人大声疾呼:“吁请海内文豪,从此多写‘短’篇”。
因此我的意见就是:要想写好短篇,不妨从“短”做起。
引发我上面一大篇老生常谈的,正是此刻置于我案头的张慧敏的《短篇三题》。它们起码从形式上可以称得上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紫色故事》5300字;《红雨》5100字;《寻找辉煌》4700字。我的略嫌冗长的开场白,其实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这一组“短”的短篇的褒奖。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短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好的,这一组短篇究竟“短”得怎么样?是不是短而精,“短”得有没有一点道道?等等。这就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了。
下面我来具体谈谈张慧敏的《短篇三题》
《紫色故事》是一枚匠心独运的“小果实”,它的核就是那张淡淡的紫色的“小纸片”。这纸片是什么东西?作者借村长之口告诉我们“是杜三的立功证书”。究竟是不是呢?老练的村长“笑笑”,而聪明的作者却虚晃一枪拨马走了,腾出笔墨去交待杜三奶奶和杜三的“奇遇”了。给读者留下一个感觉:这里面好像有点“情况”。
淡紫色的鞋垫是这枚小果实的外壳。杜三奶奶在夏日老槐树的浓荫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缝制它,缝制它仅仅是为了一个深深的念想,一个长长的等待。在“我”第二次到杜家时,看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场面:无数的荆条箱子里有无数的紫色鞋垫,无数的紫色鞋垫上有无数的猫、龙和蝴蝶,而且都成双成对,相依相偎……紫色鞋垫的“壳”越包越厚实,越包越沉重,它不仅是对那个“核”的呼应,更是对“核”的成熟与爆发的催化与期待。终于,在“我”第三次到杜家的那个暗夜的煤油灯下,“我”捧起“小纸片”鼓足勇气大声地脱口而出:离——婚——证——明!
字字千钧,倏地砸碎了那颗包藏甚密的“核”,并胀破那层厚实沉重的“壳”,使无数的紫色鞋垫进散开来,在我们眼前弥漫起落英缤纷般的“紫雨”……
给这颗“小炸弹”引爆的是那个欧·亨利式的结尾。我敢贸然地作一个判断:一百个读者中肯定会有九十九个想不到鄢张紫色纸片竟然是一张“离婚证明”!在“立功证书”和“离婚证明”之间,二者相距何止万里。正是这种巨大“错位”所形成的张力凝结成了全篇小说的情感的核,同时也就成了它的结构的“眼”。整个《紫色故事》缘此而发生,且因此而发展。在端出悬念(纸片是什么)的同时,明确指示出一个大有疑问的恩情走向(“立功证书”),然后再隐隐若若地给出几个暗示(“死亡通知”?“烈士遗书”?“请战书”之类)来诱惑人的思路。最后,我们的种种猜测和阅读期待全部落空,真正的答案“远在天边”而又“近在眼前”。乍看之下,出入意料而又似乎是在情理之中。这也正是著名的短篇大师欧·亨利小说结尾的惯用伎俩。张慧敏可以说对此有所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