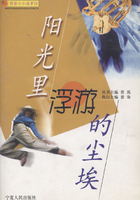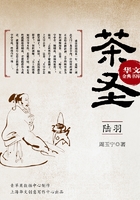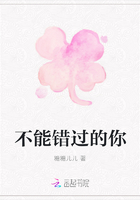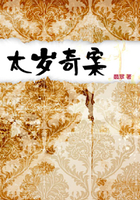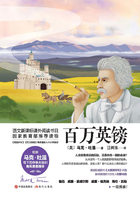读了李陀发表在1988年10月29日《文艺报》上的《昔日顽童今何在》,觉得他对近二年小说的竭力鼓吹和近二年小说批评的愤懑指责虽然不无一定道理,但使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题目——昔日李陀今何在?
我所谓的“昔日李陀”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大致有三个形象。一是1982年前后作为“四小风筝”之一的李陀,他和当时其它“三小风筝”(高行健、刘心武、冯骥才)一起,不仅倡导“现代小说”(他提出《“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而且身体力行,以《自由落体》、《七奶奶》、《余光》等一系列探索小说给中国文坛吹来一股“西风”,造成了一阵子小小的骚乱,可以说为1985年的小说革命埋下了伏笔,其荜路褴缕之功不可没。或者说也因此基本上奠定了李陀的先锋姿态和在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大体位置。二是1985年新潮小说和新潮批评遥相呼应浩然作势之中的李陀,此时他的小说创作已挂笔两年无新作问世,可他全力为新潮小说推波助澜,擂鼓助威,卓有成效地荐举过阿城、马原、莫言、刘索拉等新进作家,还兴致勃勃地参与过“寻根”文学的理论研讨等活动,转眼间似乎又给人们留下了新潮(亦可套用他自己的话叫“顽童”)批评家的印象。三是1987年中的李陀,这个时期他的形象稍稍复杂一些,我不得不多花些笔墨来加以追述。
由于诸多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原因,1987年的新潮小说(或者说新潮小说舆论)呈显急剧退潮之势。正当一部分批评家在研究新潮小说运动中逐渐变得冷静、苛刻,甚至即将由“捧派”“变脸”而成为“骂派”之际,李陀却对“有不少批评家在他们的批评文字中很郑重地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缘起和特征”等现象发出疑问,认为“这些想法和说法都缺少根据,都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实际,反而容易造成很大的混乱”。(见《告别梦境》载《外国文学评论》87、4)也就是说,当一部分批评家准备对“现代主义运动”(虽然实际上有没有、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现代主义运动”尚可置疑)进行全面反思和着手单篇作品批评时,李陀则干脆对整个“运动”(或潮流)的真实性表示不信任,从而进行抨击。在一些公开场合(例如1987年秋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讲座)指责“伪现代派”们无病呻吟、矫情造作,甚至还激烈地宣称:这些现代派的作品我一篇也不看。
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就使文学界很多人(我差不多也属于这一“党”)“误解”“李陀变了,他又反起现代派了!”直至1988年初,李陀在第4期《北京文学》上撰文《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不得不以一个“声明”开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赞成中国人搞什么‘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极力申辩是在“当现代派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成了铺天盖地的‘一窝蜂’,并且有不少评论家在郑重地讨论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缘起及其特征的时候,才对评论界用‘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来描述、评价当前的种种文学现象表示异议、对许多作家争当现代派表示不赞成。”还正色道:“这和‘反’现代派有什么关系!?”。
尽管李陀反复坚持“‘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我还是对近年中国文学中的现代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先锋、探索、试验小说种种称谓之间有什么明确界定和本质区别不甚了了(我认为这仅仅是称谓的不同罢了,面对的现象其实是共同的)。即使如此,我仍然可以尊重李陀的从来不“反”或压根不赞成中国人搞现代派的意见,也可以把他的诸多言论都看作和“反”现代派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认定有一条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1987年中的李陀对现代派小说也罢新潮小说也罢——的现状极不满意。换言之,第三种形象的李陀是对新潮小说持低调评价的李陀。
那么好了,有了以上的简单回溯,我们再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本”作为参照来读,就难免会油然而生地反诘一句;昔日李陀今又何在呢?
当然,这种反诘也许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其一,作为一个作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断予以调整,停止一段创作或把兴趣与精力转移到理论方面,都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过问;其二,作为一个批评家,也完全可以根据某一种文学现象或潮流的消涨起落的发展变化,作出相应的也许是更加成熟的发展变化的比如说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评断,与别人也是没有多少相干的,但尽管如此,我想人们还是有理由要求李陀把对新潮小说重新褒扬说明得更加有理有据一些(事实上李陀也是1985年的“顽童”之一),而不要仅仅是居高临下地振臂一呼或断喝一声“好”或者“不好”,从而引起一片大哗,挑动一场“混战”,获得某种“效应”。
问题好像就出在这儿。
只要我们摊开《昔日顽童今何在》一文来仔细观瞧,就不难发现李陀对新潮小说的喝彩,不过就是在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新进作家的名单之后便断言他们“是怎样剧烈地改变了、并且继续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甚至比1985年的变革“更为激烈”、“更为彻底”云云。至于具体改变了什么,又是怎么改变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又在哪里,统统语焉不详,究竟是李陀胸中不详呢,还是笔下不详?我宁愿信其前者。
如前所述,虽然说1985年的李陀差不多成了一个新潮批评家,但产生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似乎还在于他凭着敏锐的艺术直觉不断地推出新人,而不在于他在新潮小说理论建设方面有什么出色创造。因为今天看来,他在后一方面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文论。相反,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辑古钩沉中倒有一些不俗的见解。至少在我个人的记忆中,还依稀记得他评张洁的“现代儒生”一文中对儒文化的批判;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对“营造意象”古典美学的弘扬;序贾平凹《商州》中对汉石刻艺术的研究等等。重提这些史实,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李陀主观上多么想参与新潮小说的批评运动和理论建设,可事实上却走了一条与当时更为年轻也更为纯粹的新潮批评家们(如黄子平、南帆、吴亮等人)完全不同的路子,甚至毋宁说正好相反,他走的是一条企图从古典美学传统中重铸当代小说美学的路子(当然,这两条路子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至于此后两年多,当少数青年批评家逐渐沉静下来,开始运用成套的西方批评方法来解析新潮小说(并不像李陀说的那样,建设发展批评学完全以放弃对文学的关切作为代价。比如李劼对近年新潮小说的宏观研究和语义分析,就比较切实和有成效),进而艰难地推动新批评运动不断深化时,李陀就显得更隔了,或者说基本没有或者干脆说基本不能介入了。
这种主观愿望和客观效应相悖离的现象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李陀的艺术营养源在十年以前还主要来自两条渠道,一是西方十九世纪经典名著,“我带着一种狂喜的心情一部接一部地阅读十九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梦境……一个出于对十九世纪的文学艺术的迷恋和向往而形成的梦。”二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世界上大约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使我减弱对这部(指《红楼梦》)伟大而奇异的作品的迷恋。”《红楼梦》如此,前文所述的汉画像砖,“营造意象”等古典艺术同样使李陀沉醉。这两个艺术营养源对一个作家数十年(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滋养与浸润,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了,凝定成为了一种恒固的审美场与艺术经验。尽管后来李陀认识到“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是毫不犹疑地向十九世纪告别——准确地说,是向那种对十九世纪的迷恋情绪告别,向那种觉得十几世纪较之二十世纪对自己更为亲切、更为熟悉的幻觉告别,向一场做了多年的白日梦告别”(以上引文均引自《告别梦境》)并且孜孜矻矻地从本世纪上半叶的卡夫卡读到本世纪末的克洛德·西蒙,但在潜意识中要真正“告别十九世纪”或者用“二十世纪”取代“十九世纪”并不容易(而我国新潮小说运动恰恰是在当代西方文学背景下展开的,新潮小说尤其是后新潮小说作家们的艺术营养源主要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艺术)这第一方面的原因就造成了李陀与新潮小说运动的第一层“隔”。
至于第二个方面就不仅仅是艺术范畴的了,而是包括整个的人生历程,和人生历程后面的政治、经济、哲学、道德等等大文化背景。在不同的大文化背景下经历的人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及至思维方式,使李陀不仅与西方现代艺术很难溶合(不是理智上的认同),与中国新潮小说作家也格格不入。——例如迷失、绝望、孤独、虚无和游戏人生以及反理性、反价值、反文化等心态情思,在更大程度上只属于刘索拉、徐星尤其是余华、玉朔、格非、苏童们。他们的这种心态情思固然有一部分来自西方现当代的哲学、文艺思潮,但更多的是生长于近年中国的复杂现实,发源于各自人生的生命体验。这第二方面的原因也就造成了李陀与新潮小说运动的第二层“隔”。
两个方面的合力,牵引了我在前面所勾勒的昔日李陀三种形象的演变:从1982年新潮小说的创作家→1985年为新潮小说摇旗呐喊的批评家→1987年对新潮小说犹疑不定的批评家。以至到了1988年发出《昔日顽童今何在》的空洞责问的时候,李陀差不多只剩下一副焦躁的而又有点束手无措的新潮小说运动的组织家的模样了。这样一条轨迹表明,几年过来,李陀离时下的新潮小说运动实际上是越来越远了。
这是一种值得研究需要正视的现象。
这是我国新时期文化开放以来文学艺术急剧转型期中间出现的非正常“隔断”——不同年龄层次的作家之间的“隔断”。同时这又是一种“代沟”。“代沟”谁也不能跨越,“代沟”是人类的宿命。
这种宿命当然不只属于李陀。——比如在理论方面,有谢冕从当初为新诗潮摧枯拉朽式的鸣锣开遭到晚近对“后新诗潮”“疲惫的追踪”的蜕变(至少不如王干、于慈江们干得轻松自如);还有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挑战,还有靳大成、陈燕谷的《刘再复现象批判》等等。又比如在创作方面,仅就探索小说而言,余华们有别于刘索拉们,和更早的王蒙一路相较,就愈发地大异其趣了(王蒙是聪明的,虽然“现代派”的“春之声”由他率先唱响,但他很快即意识到与青年新潮小说家们其骨子里的“文化精神”的差别,便不再与他们掺和,依然我行我素地走着自己“半新半旧”的路)。
指出这些,丝毫不意味着抹杀李陀们过往的成就(某些贡献还特别令人尊敬),也不意味着宣布他们今天已经“过时”。照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无新无旧的,更无越新越好的道理,艺术的更替决不像科技的发展那样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一种艺术经验的积累,艺术范式的发生、发展直至成熟,往往需要漫长的时光,需要漫长时光的筛选、淘汰和验证。当今中国小说正处于一种失衡运动中,究竟谁能生长得更好,也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比较鉴别。时下的新潮小说虽然又有“二度崛起”之势,但我也不赞成像李陀在《顽童》一文中那样以偏概全当作近年的小说主潮。我认为它也只不过是一种路数,而且是一种探索试验中的路数。我支持这种探索,并愿意热情地及时地肯定探索中的发展(可参见《1985~1987:新潮小说的“二度剥离”》)。但对这种小说总的前景,我不愿过分乐观。一年多以前我持这种看法,现在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可参见《说“冷”话“热”》)。我还认为介入不了“新潮”也没有什么不好,清醒地意识到介入不了而干脆不介入或者还更好。其它可走的路还很不少,譬如李陀自己倡导的借鉴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当代文学两结合的“现代小说”就不失为一种建设目标,而且还极可能是一条更有希望的路。关键是要踏踏实实去走,而不要把过高过大的希望寄托在发动或组织一场又一场的小说革命的运动上。如果每个人都找到自己,长其所长,走自己的路,那么就可望真正形成不止一种“新潮”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化文学格局。
话说到这儿,我想也该郑重声明一句:我与李陀素来无怨无仇,和他打这一番笔墨官司也决不是和他个人有什么过不去,只是他使我注意到了以上现象。他的“昔日顽童今何在”的一声喝同,在我听来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从反面的意义提醒人们:李陀下一步的选择恐怕不应该是继续领导“新潮”,而是恰恰相反——告别“新潮”。
1989年元旦于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