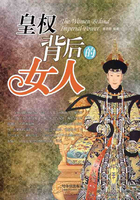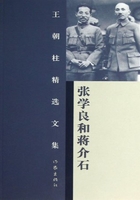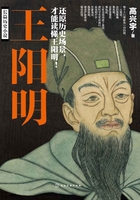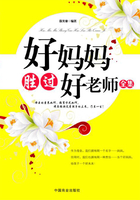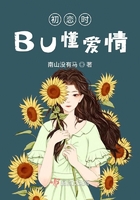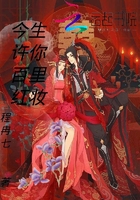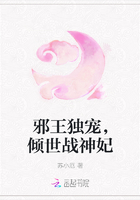一
打开三联新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看到的是作者曹聚仁在满架图书前清癯的半身像。那是我曾经熟悉的形象,那书架所在的天台小屋,也是我曾经闲坐过的地方。在“曹聚仁”三字的签名之下:注着“一九〇〇年——一九七二年”,它提醒我原来他也是世纪同龄人,和为他说过公道话的夏衍同一年出生;再过大半年,到明年七月,就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一九四二年的事。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的《大公报》编辑部里,那一天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军人模样的客人,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听别人说,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作家兼教授的名字。这时又知道,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就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更知道,他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既是中央社,又是蒋经国,在我那年轻而又单纯的头脑想来,不敢恭维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那时我只不过是管收发兼管资料的练习生,也不可能去接近这样一位作家、教授、大记者。虽然如此,他那一身军装和一条皮带,却给我留下了一个较深的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如在眼前,尽管那在抗战的当年并不是少见的形象。
再见到他却是在十三四年以后的香港了。军装当然已经卸下,在上海当教授时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自然更不复见,而是洋装在身,却经常有一个布袋在手,是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布袋,塞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点他自己所说的“土老儿”的味道,形成了“土洋结合”。
二
曹聚仁是一九五〇年从上海到香港的。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抗战胜利后,他一直住在香港”,显然是记忆有误。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回到了上海(这以前,他离开了《正气日报》,去了上饶的《前线日报》),一边教书,一边还替香港的《星岛日报》写通讯文章。按他自己说,上海解放后,他对新的城市政策感到“惊疑”,最后终于下了“乘桴浮于海”的决心,到海外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客观的观察者。
他一到香港,就在《星岛日报》上用特栏的形式,发表引起左派迎头痛击的《南来篇》连载文章,大谈解放后的内地形势,主要是上海。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以史家之笔自命的他,对建国初期的新气象有赞有弹,自然是应有之义。今天回想起来,那些议论尽管未必都很恰当,却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在左派人士的眼中,这还了得,分明是一个“反动文人”,逃亡到海外,大发“反动谬论”,这头“乌鸦”真是无法容忍!于是纷纷写文章反击,其中最尖锐的当然是早些年已经点名叫他“看箭”的杂文名家聂绀弩。我当时也在学写杂文,也不免拿了曹聚仁充当箭靶子。
虽然如此,右派也并不怎么能接受他,对他是戒惧而存疑的。他虽然对中共诸多批评,但并不像别的一些反共文人只作诬蔑谩骂,而且在笔底也从来没有什么“共匪”出现,这在那些国民党的“忠贞之士”看来,就带有几分“非我族类”的气味了。因此,他也就难于避免来自右派的讥嘲。
就这样,他是左右不讨好,但于右较近。因为他毕竟在抗战期间做过中央社的战地记者,毕竟在蒋经国手下替他办过几年《正气日报》,毕竟从大陆的“竹幕”中出走南来。他和右派是有往来的,和左派就只是“鸡犬之声相闻”而已。
后来,他在《星岛日报》的客卿地位也失去了。却和一家亲国民党的晚报《真报》接近起来。
这其间,他和徐、朱省斋以及后来到了新加坡当起那个国家外交官的李微尘一起,办了创垦出版社。出丛书,还出了一个杂文、散文的小型刊物《热风》。
尽管他又成了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在香港写观察大陆的通讯,还有李微尘这样的关系,却始终去不了新加坡。在香港的二十多年中,除了五十年代中后期多次回大陆进行采访工作外,他哪里都没有去,包括台湾。
这里特别提到台湾,是曾经有一种流言,说他要去台湾做说客,说服他的旧日上司蒋经国走和平统一的路。流言后来又变了,说蒋经国移樽就教,坐了一艘军舰,开到香港海外,接他上去商谈。他所接近的《真报》,还刻了鸡蛋大的标题字,当做头条新闻刊出。
这件事也使热衷于和平统一的我,闹了一次笑话,犯了一次错误。我在《新晚报》上,转载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消息”,发表了一些一厢情愿的议论,推波助澜,煞有介事,直到后来受到来自北京的严厉制止,这才停了下来。这就是所谓“和谈宣传”。在这件事情上,原来怒目而视的两个人,这时却似乎有了一些共同的语言,因“和谈”而讲和了。事实上,我们的交往要在那以后好几年才开始。
近年从《懒寻旧梦录》中看到,原来周恩来当年曾对夏衍说过,曹聚仁“终究还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他虽然既不能去台湾,也没有在香港见过蒋经国,却是早就在上海写下了一本《蒋经国论》的,尽管没有后来江南的《蒋经国传》影响大,却成了江南为蒋立传时的一份参考资料。不过,现在知道有这本书的人是很少的了。
三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左派开始接近的,只是猜想,五十年代中期,周作人的一些文章在“形中实左”的刊物上发表,又结集出版,可能有他的穿针引线的功劳。后来终于从《周作人年谱》中得到证实。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穿针引线,使他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开始了“北行”,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到北京和其他地方进行采访。他会见过周恩来、毛泽东,他直到鸭绿江边去欢迎中国志愿军的凯旋归国……以后的几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北行一次或不止一次。这些旅行,使他写成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和《北行三语》这三本书。这些都是发表在《南洋商报》上的文章的结集。
“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周恩来对他的评语。
作为记者,他有过一次独家新闻。一九五八年炮轰金门,开始了好些年的海峡炮战,这是一件大事。他较早得到这一消息,把电讯发到《南洋商报》,报纸显著刊出这一独家消息之后几小时,预定的炮弹才从大陆上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射向金门。在北京看来,这当然是并不愉快的泄密事件。
老牌的《循环日报》以新的姿态复刊(其实是全新的创刊),使他的新闻工作重新面对着香港的读者。他担任了主笔性质的工作,从评论、专栏到副刊文章都写,多的时候一天要写四五篇,够他忙的。这家报纸的主持人林霭民,曾经长时期在《星岛日报》工作过,广州解放时,以“广州天亮了”的特大字头条标题,不容于星系报纸的主人胡文虎。这虽然是编辑部的事,作为负责人,他不得不和编辑部中有进步倾向的朋友们离开了《星岛》。新出的《循环日报》是以中间面貌出现的,定下来的方针是“中间偏右”,办起来却是“右”则不足,而“左”则有之。
作为同行,曹聚仁既在“形右实左”的报纸工作,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有了交往,翩然一笑,不谈往事。也许这以前就接触而渐渐接近了,因为他虽然还是标榜“中立”的自由主义者,时时要发些和我们不同的议论,但他的文章早已告诉我们,实在不能称他为“反动文人”了。
我们早已不再骂他。从嘲讽到骂他的是右派。嘲骂他最多的是:他说过如有机会,他愿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自己。他说这话是诚恳的,真心的,尽管他当年到过北大荒作采访旅行,却没有看到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那里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实际上是怎么样过日子,不以为那是折磨,只相信那是“修身”。
我们成了朋友。就年龄,特别是就学问来说,他实在是我的前辈。但我就是没有把他当老师对待,甚至对他送给我的那一本本他的新出的著作,也没有好好地阅读过。对其中的一些,如《鲁迅评传》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相看的,没有好好看它。以为那一定充满了歪曲,尽管不是恶意的;不以为那里面自有他可取的见地,和一些被别人舍弃了的关于鲁迅的真材实料。
他也替我们这些左派报纸写文章了,不过不多。就是后来《循环日报》由于亏蚀太多,办不下去,只留下了《循环》派生出的《正午报》,他写作的地盘大大减少了,也只是在左派报纸当中调子最低的《晶报》上写些《听涛室随笔》之类每天见报的专栏。他以前在上海办过《涛声》周刊,这时在香港,离海更近,听涛声就更易了。尽管参加过《循环日报》的工作,他还是愿意和左派报纸表面上保持一些距离,以显中间;而左派报纸对他的一些中间性的议论,也有些敬而远之,怕惹麻烦。
六十年代以后,他就似乎不再北行,“文革”狂潮一来,当然就更是行不得也,不可能再挥动他的“现代史笔”,夹叙夹议,而只能谈谈生命,讲讲国学了。
四
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场合,我们谈到了周作人的文章,彼此都认为,如果由他来写回忆录,那一定很有看头。就这样,曹聚仁就向北京的苦雨斋主人催生了那部《知堂回想录》。
一九六〇年前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在《新晚报》上发表,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当时《新晚报》把它当做争取读者的王牌,特别增加了一个每天见报的《人物志》副刊,连载这篇“宣统皇帝自传”。后来《知堂回想录》也就是在这个副刊连载的,同时刊出的还有另一较短的连载,写“绿林元帅”张作霖的一生。因此周作人在谈到这件事情时说:“在宣统废帝以后,又得与大元帅同时揭载,何幸如之!”
不幸的是开始刊出还不到两个月,它就不得不停下来了。这倒不是作者预言过的,“或者因事关琐屑,中途会被废弃”,而是因事关大局,奉命腰斩。人在香港,虽然在做宣传工作,照理应该信息灵通,但我当时却实在懵懵懂懂,不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对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就已经在酝酿严酷的批判了。像《新晚报》那样大登周作人自传式的文章,当然是非常不合时宜,非勒令停刊不可的。
在刊出以前,我还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但想到这里面有关五四以来文艺活动的资料相当丰富,颇有价值,就舍不得放弃;而且这原名《药堂谈往》,后来改名《知堂回想录》的几十年回想中,抗战八年那一段是从略的,基本上不发生作者自我辩解的问题。考虑又考虑之后,终于不忍割爱,还是决定连载。这里说的爱,是认为资料可贵,而文章却已不如以往的可爱,缺少盛年所作的那一份文字上的隽永和光彩。
周作人是一九六〇年底在曹聚仁鼓动下开始写这一回忆录的,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写完,前后差不多两年。原稿辗转到我手上,至少在一年以后。再加上我的踌躇,刊出时就是一九六四年秋天八九月的事了。写了两年,拖了又几乎两年,刊出不过两月就被“废弃”,作者的不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从曹聚仁写给他的信中要他不要“错怪”我就可以知道。
我也打算过,转到在我有份参加编辑工作的《海光文艺》中连载它,但这一月刊只在一九六六出了一年就停了,那是间接死于“文革”之手的。因此连载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后来,在曹聚仁的努力下,《知堂回想录》又从头到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由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书。他在《校读后记》中还提到我的“大力成全”,而他“不敢贸然居功”,尽管他是写作这部回想录的原始建议人。实际上,我才真是“不敢贸然居功”呢。他建议,我不过附议而已,这是一;出书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猖狂之时,就算真是对这书有功,谁还敢居?这是二。我曾经建议他删去这句话,同时建议删去卷首的周作人一封信,里面对鲁迅墓有意见,对许广平也有意见。后来再印时撤销了那封信,却没有删去关于我的这句话。今天回想起这些前因后果,还不免有些歉然。
五
作为一个在国门之外的自由主义者,曹聚仁并不怎么顾忌“四人帮”。
在“文革”初期,他所编著的一本大型的图文并茂的《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出版了,正是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成,仿佛在和江青她们力捧的样板戏大唱对台戏。书里面保存了不少“四人帮”所要消灭的戏剧、电影、曲艺的资料,是他花了不少心力才搜集整理得那么丰富的。
这使人想起,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也是一本以图片取胜的书。
在他一生的著作目录上,《中国抗战画史》差不多是一个转折点。这以前,是在上海出书;这以后,《蒋经国论》以后,就转到香港出书了。
上海出的,有抗战前的《笔端》、《文思》、《文笔散笔》和《中国史学》;有战时的《大江南线》(不在上海,是上饶前线出版社出的);有战后的《中国抗战画史》和《蒋经国论》等。
香港出的,有《酒店》、《到新文艺之路》、《国学概论》、《中国剪影》、《中国剪影二集》、《乱世哲学》、《中国近百年史话》、《蒋经国论》、《火网尘痕录》(这是马来亚出的)、《蒋畈六十年》、《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万里行记》、《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现代中国通鉴》、《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分甲编和乙编)、《秦淮感旧录》(分一集和二集)、《浮过了生命海》、《我与我的世界》、《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和《国学十二讲》等。
这三十多部书(据说全部编著有七十多种,但我只知道这些书名),只有六种是在上海出的,把《大江南线》算上去也不过七种。而在香港出的,就不算马来亚出的《火网尘痕录》,也还有二十四种以上。
这样一排比,很容易就看出,人们熟知的上海作家曹聚仁,实际上可以说是香港作家。他一生的著作有五分之四是在香港完成的。而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二,他在香港生活、工作有二十二年之久(最后的大约一年在澳门养病)。
曹聚仁二十多岁就在大学教国文,是学者。他对国学,也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思想有研究,早年记录过章太炎的演讲成为《国学概论》,晚年自己又写出了《国学十二讲》。这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是他去世一年后才出版的。此外,他又以史人自命,有志于做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家。著作中有史学、史话、画史、评传、现代通鉴、中国剪影,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在上海活跃的时期,他是和鲁迅很有过来往的作家。《酒店》和《秦淮感旧录》都是小说,都是后来在香港写作的。早年在上海写的多是散文,《笔端》、《文思》、《文笔散笔》都是那时的作品。晚年的《浮过了生命海》是他一九六七年大病后出的散文集。
抗战开始以后,他就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大江南线》就是战时写下的记者文章。这以后,他一直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北行》三语,《采访》四记这些就都是他辛勤工作的记录。战后在上海的大学里,他还教过新闻学。
他留下的著作在四千万字以上。作为学者、史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的一生真是辛勤的一生!
六
一个人的一生,有些言行引起人们的争议,那是很自然的事。
曹聚仁三十年代在上海,既接近鲁迅,也受到一些接近鲁迅的人的责难。如聂绀弩,就因为办《海燕》而对曹聚仁大为不满,在这件事情上和别的事情上,对他以尖锐的杂文相加。直到六十年代,还在一首题自己的杂文集的七律中,写下了“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的句子。不过,后来绀弩了解了曹聚仁在香港的情况,也认为应该笔下留情了。
和绀弩同是《野草》斗士的秦似,在七十年代末期,写文章称曹聚仁是“反动文人”。而在八十年代之初写的诗篇中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的嘲讽。把他和汪精卫对比,更超乎“反动文人”之上,就更要使人惊异了。今年夏天秦似到北京吊绀弩之丧,有机会和他两次闲谈,酒后听他谈诗词,病榻前听他谈写作,可惜并没有谈到我所知道的曹聚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诗句,要不然就不会放过这一话题而不展开争辩的。
此刻曹、聂、秦都已经先后成为逝者,除了伤逝,就不可能在他们任何一人面前有所评说了。
汪精卫,不能比。反动文人,上海时代恐怕不能这么说,香港时期就更加不能这么说了。尽管他的文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人们对它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异议,事实俱在,到香港而又北行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努力宣传新中国的新气象的。在今天看来,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局限,他也还有过过左的议论呢。他笔下可能有无心之失,却没有恶意诬蔑。
在为和平统一事业的努力上,尽管他有过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因此而产生什么具体的活动我不知道,但明白内情的当局却并没有对他作出严重的否定。六十年代以前,他的夫人邓珂云得到批准,从上海到香港探亲;七十年代之初,他卧病澳门,邓吉雷又带了女儿曹雷到澳门看护,直到他去世。这些当时一般人不大容易办到的事,也可以使人思过半矣。他死后,也是左派为他公开治丧的。
还需要提一提,他的大儿子在参加三线建设中牺牲。对这一不幸他表现得平静,没有什么怨言。这也是使人对他不能不起敬佩之情的。
曹聚仁在他“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开宗明义就说:“我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又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经过希望、失望之后,晚年却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的。不讲什么虚无的话,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总是不会错的吧。
他被讥为“乌鸦”(我也这样讥讽过他),不以为有什么不好。“乌鸦”之来,是因为他早年办《涛声》周刊时,用乌鸦做它的“图腾”,当时恐怕有就是要讲不怕人厌恶的话之意吧。许多年后,他说这是报喜也报忧,不取喜鹊不报忧只报喜。总之,原来是《涛声》标志的这个“不祥之物”,后来却成了他的别号,而他也就承受了下来。记得他有一次北行到了东北,回来后写了一个斗方给我,上面写的是他的一首七绝:“松花江上我的家,北望关山泪似麻,今日安东桥上立,一鸦无语夕阳斜。”就是以乌鸦自况的(第三句可能记忆有误。第一句是说当年流行的抗战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平日在一些约会上见面,闲谈中他这金华人总爱谈他们家乡的名产火腿,说是金华火腿之所以味美,是因为每做一批火腿时,中间一定有一只狗腿夹杂在内,这样才能使所有猪腿味道更加美好。他说得一本正经,听的人有信有不信。但他每一次有机会时,就总不放弃他这狗腿论。以至于他还未开口,在座的两位上海老作家的另一位叶灵凤就抢先说:“听啦,听啦,我们的曹公又要谈他的狗腿了。”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把话缩回去,还是照谈不误。
他另外又爱谈自己做咸菜的技术,说那也是美味,一定要用脚踩踏才够好。他还做了送人。这表现了他在“未完成的自传”中所说的,“我永远是土老儿”的风格。真是土老儿!
他晚年的住所,是香港岛上胡文虎花园旁边一座四层楼天台上搭的临时居室——陋室,三间相连的小房,是客厅、睡房、厨房,也全都是书房,处处都堆了书,他人在书中,一个人度过了一个个春秋,“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是书生!
七
面对着《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是应该说一声“惭愧”的。
当年以《听涛室随笔》的专栏在报上发表时,我没有看它;他身后由旁人整理,用《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新话》的书名出版,我也还是没有读过。直到北京三联再加整理,出了新书,这才读了。
从随笔到随笔,现在恢复了随笔之名,不过不是《听涛》,而是《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说是新书,因为它已经大加增订,把香港出《十二讲》时删节的三十段文字和未被编入的十八篇文章都补进去了。使它更加丰富。
说来有趣,曹聚仁早年听章太炎作国学十二讲,详细记录,整理成为《国学概论》一书;而现在这本曹聚仁的《国学十二讲》,却由章太炎的孙子章念驰增订整理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中间,相隔了一个甲子——六十年。章念驰说这是历史的巧合。实在是文坛佳话。
所谓“国学”,曾经也被称“国故”之学,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现在“国学”这名字已经不大有人用了,越来越少人知道了,明明白白地称为中国学术思想是适当的。不过,我总觉得现在这个书名可以删去一个“史”字,就叫《中国学术思想随笔》也是可以的,而且更加简单明了。
曹聚仁以史家自命,也很以国学自负。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那本《国学概论》。当年他听章太炎演讲而作记录时,只有二十一岁。他是替邵力子编的《国民日报》的《觉悟》副刊做这一工作的。由于演讲者是国学大师,内容深奥,一般记者根本记不下来,他却占了原来就有国学根底的便宜,胜任愉快。后来他因此受到赏识,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但在《觉悟》发表这些记录时,还加上了批注,他说那是对当时的复古运动消毒。他还因此被陈独秀称为国学家。而他晚年写这些随笔时,由于思想更成熟,也就更自负,说这“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
他说,他是以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把前代的学术思想重新解说过;批判那些腐儒的固陋,灌输青年以新知。
他在讲国学,但他清楚表示,反对要青年人去读古书,尤其反对香港教育当局对中学生进行不合理的国学常识测验。他嘲笑那些在香港大中学里任教的腐儒,这使人如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斗士的英姿。
他在讲国学,用的是新观点,他的文字也是清新的,雅俗共赏的。能把艰深的旧学讲得通俗易懂,不枯燥,吸引人。读着它时,颇有当年读《文心》的那种乐趣。《文心》是他的老师夏丏尊和叶圣陶合作谈文章作法的书;这本《随笔》谈的是学术思想,而讲得这样深入浅出,就更不容易。
读这《随笔》,一边感到乐趣,一边又感到惭愧。真是十年深悔读书迟!
通过读书(不仅仅这一本《随笔》),对这位可以为师,终止于友的前辈,有了更多的认识。忍不住写下这些我所知道的一鳞半爪,希望对他后半生不尽了解的人能增加一些了解。就算是对他去世十五周年预先作一点纪念吧。
他和别人一样,当然不是完人,这里只谈他的大处和晚年,并不求全,就恕我不作乌鸦,不报忧,只报喜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回忆曹聚仁先生
一年容易,看了朋友在报纸上发表的怀念文章,才记起曹聚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他是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澳门去世的。我曾经和一些朋友到澳门去送他的丧。对于他,并没有忘却;但对于他的去世,却不是怎么记得那准确的日子,一切就好像昨天或前天似的,没想到一转眼三百六十多天就已经过去。真快!
人的一生,也是真快!他是生活了七十年以上的日子才结束生命的,比一个世纪三分之二的时间还长,但在朋友们眼中,却还是很短,还是希望再长一些,更长更长一些,然而,这却是永不可能的事了。
他晚年时,朋友们都叫他曹公,这自然是因为他有“吾家孟德”的缘故。奇怪的是,他生平以历史学家自负,却并没有好好地为他这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祖先写一本有分量的传记。他晚年很想完成那部《现代中国通鉴》,可惜已经来不及。
说来不敬,我认为他并不是很好的史学家,由于他的治史并不那么谨严。我甚至认为他不应该立志做一个史学家,因为他一贯认为不可能有真正真实的历史,史书所载,往往是假象。以一个“历史的不可知论”者,又怎么可以去写历史呢?
他好像也颇有兴趣做一个理学家。他虽然有些迂夫子的味道,听说却也颇有一些不一定很潇洒的风流。这只是听说,如果不可靠,如果他泉下有知,希望他一笑置之,或含笑更正,像生前一样。
在生前,他不止一次,一点也不生气地说过,我是根据错误的传说和他开玩笑。
何止开玩笑,我还骂过他呢。他生在五十年代之初由上海南来,我就针对着他,写过几篇东西,那时和他还没有认识。后来相识了,谈起这事,彼此一笑。
他南来之后,又三度北行,还写过三本北行纪事的书。这是一个老记者的观察,一个老作家的文章。
他原在上海做大学教授,抗日战争一起,就穿上戎装,做了战地记者,二十多年前在桂林,曾经见到一位穿草绿军装,腰缠皮带,个子不大的人,听别人说那就是“乌鸦”——这是他并不以为不敬的外号。外号之来,只是因为他从前办《涛声》月刊时,用来乌鸦做封面,曹乌鸦并未因为他可厌如鸦。记得有一年他在松花江畔赋诗,就有“一鸦无语夕阳斜”的句子,可见得他自己也以鸦自命了。
他的一生,兼学者(史学和理学)、(文艺)作家、(新闻)记者,留下的作品很多,但他晚年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却是人不是书,是他所钟爱的女儿、电影演员曹雷。
曹雷在上海,她的母亲邓柯云也在上海,而曹公的骨灰也已运回上海。幽冥虽隔,却在一地。他在泉下如果知道曹雷生活、工作得很不错,应该更加满意的吧。
我常常觉得他有些糊涂。不过,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殷殷以台湾和平统一于祖国为念,这就是十分清醒的想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