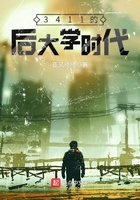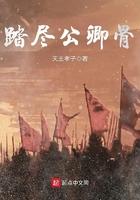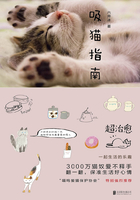冬天,除了打窑洞,起粪和铡草是干得最多的活儿。饲养员隔一阵就要给牛圈和羊圈撒一层新土,半年左右就要起一次。起粪不需要技术,只是那股酸臭眯眼的气味十分难耐,不过干一会儿嗅觉就麻木了。积粪足有一两尺1969年冬,西回村男知青与社员在云岩河畔留影。左起:社员、丁哲元、社员、王云章、聂新元、张继廉。
厚,冻得硬邦邦的,一镢下去,粪土四溅,经常溅到脸上。起出来的粪要担到窑背上堆放,就算装得不满,可还是很沉,总觉得窑坡比平时长了许多、陡了许多。铡草时我总爱找队长的老爸作搭档,老汉特别健谈,跟他干活儿不寂寞。老汉跪坐在地上,将干草压在腿下,双手掐住,一寸一寸地送到铡刀的根部。我是扶刀把的,他把草入好了,我就猛地用力向下铡去,主要靠巧劲儿和爆发力。另外,铡刀一定要磨得很快,否则干草没有被一下铡断,反而会掐不住乱跑,很容易出事。在陕北,干草主要是指玉米、谷子、荞麦、糜子和各种豆类的秸秆,大牲畜特别爱吃,全靠它熬过青黄不接的季节,所以我们三天两头都要铡草。
初到农村的最大快乐是没有了学校的派性斗争和出身论的精神桎梏,虽然是粗茶淡饭、整天辛苦,但感觉轻松、愉悦,吃得饱睡得香。到了生产队,第一个和我们进行集体谈话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天仁。这位军人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很有水平,他简要介绍了大队情况,对我们提了要求和希望,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一点也不做作,听了很舒服、很踏实。队长王兴章为人老实厚道,不善言辞,全靠着干活吃苦、以身作则,把生产队管理得井井有条。生产队很少开会,开会也都是在晚上,说完事就散会。有时让我们念一段《毛选》或别的学习材料点缀会议,时间稍微一长,坐在炕上的准打瞌睡。
到了农村,形式主义的做法和空洞的说教离我们远去了。我们队有一户富农,一户中农,一户有历史问题,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在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中,我丝毫看不出大伙儿对这些家庭背景不同的人有任何歧视。王宾是中农,他识文断字,还曾在村里当教书匠。那户富农的生活显得比别人殷实,但他们父子两代人干活儿、理家的确很利落,别人不能不佩服。不知是家族关系还是农民质朴,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西回村也没有阶级斗争的战火硝烟,民风依然那样质朴纯真,村庄依然那样平静祥和。
适应生活
我们村坐落在塬上,当地把这条塬叫西回塬。古老的黄土高原在长期的气候地理变化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貌。我理解,“塬”是黄土高原的主体和主要地貌。站在塬上向四周望去是一马平川,看不见起伏的山峦,它就是最原始的黄土高原。后来由于不断的水土流失,黄土高原被冲出了无数纵横有致的沟壑,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没有被冲毁的平地叫“塬”,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叫“川”,被溪水冲出来的叫“沟”。塬在高处,川在低处,两者过渡的坡降地叫“峁”,川里的开阔地叫“坪”,河川的转弯处叫“湾”。论生存条件,川道明显优越于塬上。
生活一天也离不开水,但吃水和用水最让我们头疼。塬上没有水源,全靠涝池里的雨水供人畜使用。涝池有一个篮球场大,开口挺大,但水面很小,夏天一池死水,冬天干枯见底。涝池水腐殖质多,有股异味,只能凑合洗衣裳,刷牙洗脸着实不敢用它。我们常用蒸锅水刷牙洗脸,几天不刷牙不洗脸是寻常事。下雨时,把闲着的盆都摆到窑洞外面接水,以便备用;下沟干活时,把脏衣服带去洗。夏天,沟里有个“淋浴”的地方,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澡。天一凉,几个月都不洗澡,不论男生女生,不长虱子反而很稀罕。
沟底是岩石层,石壁湿漉漉的,人们在有泉眼的地方修了一米左右见方的水槽,四季有水。我们吃水都是用毛驴到沟里去驮。从住的地方到水槽大概5里地,一路羊肠小道,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因为驴少,又不能过度使用,生产队根据每家情况排出驮水的日程,一般是隔两三天驮一次。
水桶是木制的,50多厘米高,固定提梁,上盖封死,留两个对称的圆孔,用来进水和出水。桶架呈“A”形,交叉处横穿一根铁棍,可以活动。出发前,先把厚厚的垫子搭到驴背上,再放上桶架,系好前后和下方的绳子,以防止桶架滑落。放水桶时,先将一只桶放到架子的顶部,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到架子内侧的同时,把顶部的桶迅速放到架子的外侧。最后,将水桶和架子拴在一起就可以上路了。一只桶装满水足有50斤重。开始,我只会装空桶,盛水的桶就得找人帮忙装。看到老乡都是一个人驮水,甚至体形比我瘦小的都行,我当然不甘心。开始驮水时出过不少洋相,心里特别打怵。有时三番五次地装不上对面那只桶,屡屡砸到驴腿或者驴屁股,驴也不配合了,它一跑,我更没招儿,哭的心都有。有时由于绳子没有系好,或者不会吆喝,驴突然加快脚步,水桶甚至连带桶架从驴背滑落下来,到家就剩下了半桶水。为了避免尴尬,我总喜欢跟别人搭伴去驮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盼望用驴驮水,因为这总比自己背水强许多。农忙季节,驴要承担很多场院的活儿,我们就得下沟背水;冬天下雪路滑,驴不能下沟,也要靠背水。回想起来,也许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插队的那一年才真正懂得节约用水。
砍柴是又一件让我们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们插队的地区当时还没有开采煤炭和天然气,做饭取暖全靠烧柴,日久天长,村里从娃娃到老汉几乎都练就了一手砍柴的绝活。老乡从来不误工专门砍柴,他们都利用出工间歇或收工后的一点时间砍柴。老乡砍柴显得很轻松。他们能连蹿带跳地到达陡坡上长满灌木的地方,选择质地硬、个头大的灌木,连根带茎一起拿下。由于土崖坡度大,长长的根系不是扎向纵深,而是沿着地表散开,老乡用小镢不一会儿就能挖出一棵连根带茎的灌木,其根部又粗又长,比茎枝更耐烧,只要砍上三四棵甚至一两棵就能满载而归了。我们到不了那种令人生畏的地方,只能在地势好的地方砍柴,而这里早已经没有木本柴火,全是艾蒿一类的柴草,需要晒干以后才能用,而且燃烧时间很短,我们的几捆柴也不顶老乡的一捆耐烧。老乡的柴垛总是堆得高高的,而我们则是砍多少,烧多少,有柴无垛。捆柴很有讲究。老乡砍完柴一般是就地取材,把草或者荆条拧成长长的草绳用来捆柴,镢把离开草绳一段距离插入柴捆,以避免行走时草绳与镢把直接摩擦,从而可以安全无恙地回到家。我们拧的草绳不结实,常常走到半路就断了。背柴有时会很紧张。当走在一侧是崖壁,另一侧是沟壑的羊肠小道上时,总是不自觉地向内侧靠,一旦背上的柴捆蹭到了崖壁,就会给人一个向外推的力,而且越向里靠,向外推的力越大,刹那间真有些胆战心惊、举步维艰。
除了下雨、下雪,一天干三晌活儿,吃三顿饭是雷打不动的。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先干两小时活儿再吃早饭。下午,太阳落山了才收工。一日三餐简单而且有规律。早饭是米汤和馍馍,馍馍是用糜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发糕。
中午饭和晚饭以面条为主,面条是用杂豆面、荞面、白面和在一起做的,味道和口感还不错。餐桌上基本见不到炒菜,常年都是“老三样”:食盐、辣椒面、酸菜。在陕北,只有夏秋才能见到一点点青菜,其他时间只有土豆。为了适应这种环境,陕北人能把各种菜都做成酸菜,从年初吃到年底。陕北酸菜的味道不同于东北酸菜,介于四川泡菜与北方咸菜之间,用来拌面着实能增加食欲。开始,大家轮流做饭,没过多久就全由女生轮流了。遇到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我们就一起上手改善伙食。雨后地上会长出很多木耳状的菌类,当地叫“地软”,它没有任何怪味,却带有淡淡的泥土芳香。毛毛细雨似停非停时,我们便全体出动采集地软,谁一旦发现了,都会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显得很有成就感。接受大自然的赏赐的确无比开心、浪漫。回来以后可以美美地吃一顿鸡蛋地软饺子。去公社赶集、交公粮是改善伙食的好机会。
饭馆的小烩菜一毛钱一碗,里面有粉条和炸豆腐,大烩菜两毛钱一碗,外加几片猪肉。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吃大烩菜,其香无比,甚至有过年的感觉。
生产队偶尔会有牛羊坠崖,这也是改善伙食的机会。头一年,国家免费给每位知青400斤原粮,作为秋收之前的口粮,直接到公社粮库去领。我们需要三天两头磨各种面粉,到了用驴紧张的时候,人推碾子是寻常事。我们还养了一口肥猪和一群母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学做农活儿
当时,陕北的农耕技术非常原始。春耕时节,在比较平缓的地块用牛来犁地、耙地,通常是派经验丰富的人干。我曾试图体会过几次,的确是干不了。首先是不会吆喝牲口,牛不听我的话,让它往东它偏往西。其次是扶不好犁。犁地时不仅要左右晃动犁把以掌握方向,还要适当用力将犁把提起,用力小了,犁会顺势越扎越深,牛感觉太重拉不动,就停下不走了;用力一大,犁会吃土过浅,牛感觉轻飘飘,会突然加速快跑,这时需要把牛倒回来重新耕一遍,否则就会造成断垄。耕地只是少数人能干的活儿,多数人是在坡地上用老镢翻地,老乡叫掏地,其中自然少不了我们,一干就是一两个月。老镢的镢面有20多厘米宽,是专门用来掏地的。掏地是联合作战,大家顺着坡地的下沿一字排开,第一个人顺着地边一镢挨一镢掏,第二个人在其后一米左右,在第一行上方20厘米左右落镢,掏出第二行,依此向后、向上类推,就像一部多铧犁,从地的一头掏向另一头,然后再折返回来,往复掏西回村男知青与社员在云岩镇。左起:王云章、丁哲元、聂新元、亥子(社员)、张继廉。
到坡地的上端。春季天干物燥,坡地干活儿扬尘很大,我们每次掏完地都蓬头垢面、精疲力竭。手上早就结满了厚厚的老茧。一次,有位女知青掏地时,一不留神把前面男娃娃的裤子划破了,露出了屁股,娃娃气得直哭,好在没有伤到人,女知青吓得够呛,这事自然成了一段趣话。
在我们插队的地方,除了小麦以外大部分农作物都实行点播(穴播)。播种时3个人一组,前面的人用老镢挖坑,中间的拿粪,即把挂在胸前的笸箩装满搅拌好的粪土,两只手交替着将粪扔进坑里。后面的人下种,再顺脚将土回埋、踩实。3人当中,下种最轻松,常常是年纪大的干,拿粪最辛苦,知青首当其冲。拿粪的人不仅总要挂着十多斤重的粪笸箩,还要跑来跑去地装粪。风干的牛羊粪和上土以后基本没有气味,并不脏,只是一天干下来会有些腰酸背痛。
夏天,最大量的农活儿是锄地。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管三垅,依次排开,锄起来就各自为战了,锄得快可以先到达地头休息。开始,知青的新锄没有磨出来,加之不熟练,不仅锄得慢,有时还连草带苗一起锄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学会了锄地,并且从中品味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我从年初到年尾在生产队整整生活了一年,见识了几乎全部农活儿,细数下来,除了犁地、耙地干不了,其他的都能干,只是熟练程度不同而已。
大概是由于干活儿风风火火、冲劲儿实足,老乡送我一个绰号叫“丁疯子”。
生产队从一开始就按最高的标准,即一天10分作为我们男生的报酬,女生是8分(也算不低的)。我们队的知青除了生病以外,几乎没有误过一天工,就连到街里赶集也尽量公私兼顾。其实一个工就值三四毛钱,但我们在意的似乎不是钱,而是普通的行事准则,即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认认真真、中规中矩,要对得起良心,不能被别人看不起。
难忘趣事
插队生活虽然单调,但也充满乐趣,许多故事是从未发生过而且也不会再发生的,印象格外深刻。
陕北地区严重缺医少药,我们队有个叫金栓子的赤脚医生,找他看病也要掏一定的工本费,老乡遇到头疼脑热一般都是硬扛。那时,我们对中医的针灸疗法已有耳闻,于是萌生了用针灸这种比较经济的办法为老乡解除病痛的想法。我们很快就置办了一套针灸用具,并找来针灸书籍研读。出乎意料的是,老乡对待此事的热情比我们还要高,每次都是老乡找上门来请我们去扎针。一开始,我要带着针灸书,根据病人描述的症状,在书上查找用针的穴位,后来渐渐地有了经验,就把书甩开了。我学会了用三棱针放血,用长针治疗,掌握了进针位置、运针力度、捻针节奏等技术要领。通过针灸,有的病人症状有所减轻,有的变化不大,但是老乡依然信赖和感激我们,这让我们颇有几分自信和成就感。我一直很放手,以为无论效果如何,总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当知道了位于喉咙下方的天突穴距离肺尖很近,如果进针的方向和深度掌握不好就会出危险时,我着实有些后怕,因为我曾多次在天突穴用针。我还给别人做过肌肉注射。前不久回村时,老乡还提起当年我给他打针时,半天也推不进去药。可能是病人太紧张的缘故,推药特别费劲儿,直到针头都弯了药还没有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