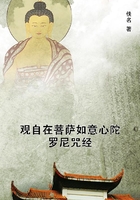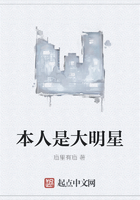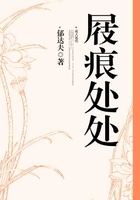荀子具体举例:客观万物的形状、颜色、纹理,用眼睛来区别它们的不同;声音的清、浊、和谐、不和谐,用耳朵来区别它们的不同;甘、苦、咸、淡、辛、酸,各种特殊味道,用口来区别它们的不同;香、臭、芬芳、腐气、腥、臊、马膻气、牛膻气等各种特殊气味,用鼻子来区别它们的不同;畅快、烦闷、喜、怒、哀、乐、爱、恶、欲,用心来区别它们的不同。以上这些论述,无疑说的是人的感性认识作用,这在形成不同的概念的过程中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的认识并不就停留在此,仍要前进,天官之一、或日天君——“心”的作用远不只是上面讲的一点。
荀子认为“心”还有“征知”这种理性认识作用。
“征”是检验。理性能检验观念与事实是否符合,从而作出判断,这种作用叫“征知”。荀子所谓的“征知”,是指理性进行比较、分析、判断的活动。正因为“心有征知”这种理性认识活动,凭着耳朵可以识别声音,凭着眼睛可以认知形状,能如实地把握关于声音、形状的概念,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要检验,首先必须有感性经验,而那是靠各种感觉器官接触相应的外物,如耳朵接触声音,眼睛接触形状、颜色等而获得的。如果感官接触外物却无感知,或者“心”进行检验,即把概念与事实比较,却不能作出判断,那么,人们会说这是“不知”。
荀子这里既强调心有“征知”作用,又指出理性思维依赖于感觉经验,较为正确地阐明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
三、制名的原则
荀子在正确地论述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及二者的关系,即论述了名的认识论基础后,提出了制名的原则及方法,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名之枢要”。它包括同、异原则,单、兼原则,约定俗成原则,径易不拂原则,稽实定数原则。
同、异原则是说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就用一个名去指称,对本质不同即不同类的事物就分别用不同的名去指称。
单、兼原则是指名的语词表达方面,有时用一个汉字即可表达如马、牛、羊、山、川之类对象,那就用一个汉字,这样的名称为单名。有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表达一些对象,如白马、骊牛、高山、大川之类,这样形成的名就称为兼名。
约定俗成原则是说某个客观对象用什么名去反映、指称与某个名到底应指称、反映哪个(类)对象一开始不是固定的、不一定是合适的。某实用某名去反映、指称,某名反映、指称某实,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的过程,即要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虽然名的形成是“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但好的名却是有固定标准的,即“径易而不拂”,意为好懂、易记、准确清楚而不易引起误会,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为“善名”。
最后一条稽实、定数原则,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同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区分为不同的类,而“定数”是通过考察对象的实质以决定“名”的数量。
其实质是从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和变化来具体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四、名的种类
关于名的种类,《荀子》一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称谓。诸如:新名、旧名,散名、善名、宜名、实名,刑名、爵名、文名,单名、兼名,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等。这是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即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名进行划分的结果。这些不同种类的名大致可作如下区分:
首先,对于荀子所处的时代来说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名,还是新创制的名,分为新名、旧名。
其次,依据对治国是否有直接关系,将名分为刑名、爵名、文名与散名。其中刑名、爵名、文名与治国有直接关系,可称为专有名词。《荀子·正名》篇中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法律名称殷朝较为详备,沿用之。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及五服三百六十官,这些规定等级的名号——爵名,周朝的完备并且在荀子时代变动不大,故从之。文名指各种礼仪之名,周礼非常详备,规定细微、具体,据说有三千三百条之多,故沿用之。另一类,与治国关系远不如刑名、爵名、文名那么直接的名,如马、牛、羊、山、水之类,称为散名。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对世上万物所取之名,称为散名。遵从中原各国的约定俗成之名,这样,远离中原、交通不便、有不同风俗的地区,也可以根据散名交流思想。
第三类指在制名过程中用到的一些称谓,如宜名(合适的名)、实名(某一具体事物的名)、善名(好的名,具有“径易不拂”特点的名)。
最后一类才是依据内涵、外延不同特点而划分出的单名、兼名,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这才是从逻辑角度对名的种类的区分。
五、名的谬误
荀子名学体系中最后一个重要理论是名的谬误及其防止,这就是名的“三惑”说。作为战斗的唯物论者,荀子的正名思想体系是在与各种“擅作名以乱正名”的谬论作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他不但从正面论述了制名的目的(“所为有名”)、名的客观基础(“所缘以同异”)、制名的原则及方法(“制名之枢要”)及名的种类等问题,还从反面论述了“乱名”之害,即名的运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及防止的方法。这就是“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的“三惑”说。
《荀子·正名》申说: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
所谓“以名乱名”就是看不到概念(名)的确定性,用偷换概念以混淆概念。其实质在于没有正确区分共名与别名,即属概念与种概念。对“以名乱名”的谬误,荀子提出了两条防止以名乱名的原则或方法:一是检查一下某个名的本来意义即“所为有名”;另一方法是实践检验,从名的作用来考察,看这些说法与通常的说法哪个行得通。
所谓“以实乱名”,《荀子·正名》中指出:
“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
杨惊注:“牛羊日刍,犬豕日豢”,泛指家畜。这种谬误的实质,荀子认为以上命题都是根据片面的、个别的事实提出来的。用个别的、片面的事实去淆惑名的本来含义,就是以实乱名。荀子为纠正、克服“以实乱名”的谬误开出的药方,一是考察不同的名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即“验之所缘以同异”;二是“观其孰调”,即看哪一个说法合乎人情,为人们普遍接受。以上两点做到,就能防止、禁止以实乱名的混乱说法了。
所谓“用名以乱实”,《荀子·正名》中说:
“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
前已述,荀子认为名的根本作用在于“名足以指实”,“名闻而实喻”。如果名的含义可以任意解释,造成名不足以指实,名闻而实不喻,这就违反了制名的根本目的。故“以名乱实”,就是用混淆、偷换概念来歪曲事实。防止此种谬误的办法,荀子提出只要用共同约定的名的定义来验证一下,指出其自相矛盾之处,就能禁止、防止以名乱实的谬误出现。
荀子认为名实关系之间可能产生的诡辩情况只有这三类。总的来说,荀子的概括、分析批判是颇为细致、深刻的。
六、荀子名学体系的不足之处
荀子在继承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对名辩学作出了巨大发展与贡献,在中国名辩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是其主要方面。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荀子名学体系的不足之处。
其一,荀子的名学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的,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的。荀子研究、论述、运用名学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名学的研究与发展,而是如何使地主阶级统治长治久安,达到“治之极也”。在荀子心目中,名学是一种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单独的一种以思维的形式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荀子认为,名以指实,名定而实辩。这都是指正确的名。如果名达不到指实、实辩的目的,那就是“乱名”。
“乱名”多起来就会造成思想混乱,从而引起实践上的混乱。所以,荀子极力反对“析辞擅作”的“乱正名”的思想活动。否则,必然会引起人民的疑惑,从而辩论、争讼,而这是一种“大奸”行为,与伪造符节、度量一样的大罪。
“乱正名”的严重后果是“贵贱不明、同异不别”,会使得“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就是说如果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不能通达无阻,统治者的事业就难免发生困难而陷于失败。
相反,如能及时克服“乱正名”这种“大奸”行为,名不乱而正,则老百姓思想统一了,老实而听话,当然就容易驱赶役使,统治阶级的事业就容易获得成功。“名正”而不乱,那么统治者的法令就会得到遵守,统治阶级的寿命也就可以延长了。这使得荀子的名学理论带上了鲜明的统治阶级的烙印,因而必然导致名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与意义的否定。
其二,由于历史的局限,荀子对于思维的内容与思维的形式未能作出明确的科学区分。荀子的名学像后期墨家的辩学一样带有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深深的烙印,这是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一个特点,一定意义上也是其缺点。这是荀子混淆名学自身作用与名学应用,把二者混为一谈,因而把名学看成是思想统治工具的认识论根源,这就妨碍了他对思维形式名、辞、辩说及其规律的进一步研究与贡献。
虽然,在先秦,是荀子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提出了最科学、最接近传统逻辑的关于名、辞、辩说这些思维形式的定义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