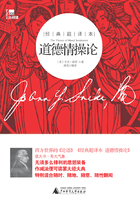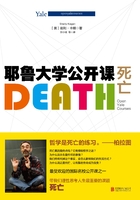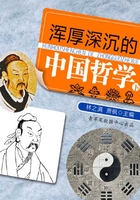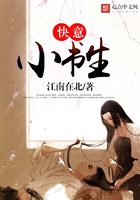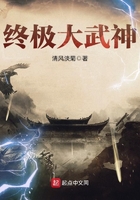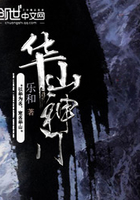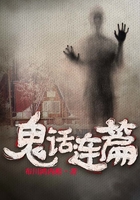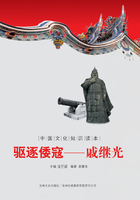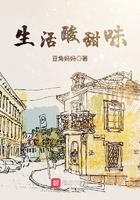文子跟李耳来到函谷关后不几天,突然接到他的学生范蠡托人送来的书简,说是他现在陪同越王勾践率领大军与吴国交战,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越国国力兴盛,眼下正是报仇雪恨之时。一旦胜利后,他会按照李耳送给他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教诲去做的。范蠡忘不了文子领他在京都拜见李耳时的情景,他有一件宝贝东西要送给李耳,那是他在卢氏的一个地方(即现在的卢氏县范蠡镇)拾到的,现在他老家的一个地方放着,叫文子立即去取。
文子接到书简后,去找李耳。可李耳那天刚好外出,找不到,便找尹喜商量该怎么办。尹喜正与楚国的一位大夫交换文书,那位大夫准备小憩后返回。文子急急忙忙把事情说了一遍,尹喜略一考虑道:“李耳外出,不知几天返回。现在你要去楚国范蠡的家乡取东西,刚好这位楚国大夫正要返回,你们同路岂不更好?等取回东西再交给李耳也不迟!”
于是,尹喜叫孙景给文子牵了匹白马,打发他和楚国的那位大夫上路了。
文子照着范蠡给他写的书简,骑马过卢氏来到楚国南部宛地的一个地方(即现在的南阳内乡县),那是范蠡的家乡。
文子下马询问范蠡过去住的房子,可问了许多人,都摇头说此地没有叫范蠡的。这下,文子可为难了。难道范蠡给他写的地方不对?他取出书简,又把这个地方仔细看了一遍,明明是在这儿,怎么人们会不知道有此人呢?这时,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看到文子在纳闷,便问了他关于范蠡的一些情况。当文子讲了后,这位上年纪的人忽然拍掌大笑:“你原来说的范蠡,就是我们这里的范疯子呀!我们只知道他叫范疯子,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范蠡的。他原来住的地方,就是前边不远的那间破茅草屋。”上了年纪的人用手给文子一指。
文子朝前一望,那间破茅草屋已倒塌一半,像一堆垃圾堆在那里,会有什么宝贝东西!心中不免有些恼怒。何况这位上了年纪的人说他是疯子,总是有它的由来。别看他是范蠡老师,但只管把李耳过去教给他的学问全都倒给范蠡,从不过问范蠡过去的事。于是,便问道:“老先生,范蠡过去怎么会是疯子,能讲给我听听吗?”上了年纪的人说:“那有什么不能讲的,在我们这里,他的疯子事是家喻户晓的。也正因为疯子的事,他后来才发了迹,由小官爬上了大官。”
“那您就快给我讲讲,”文子催道,“我还没有听说过疯子能当大官的!”
“你既然千里来了,不嫌耳朵累的话,我就给你讲讲。”
范蠡年轻的时候,狂放不羁,为世人所不容,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狂骂世道不公平,是远近有名的酒鬼。
文种当时是宛地这里的地方官,得知本地有一个狂放的书生,就派了一位小官去请范蠡。有人早早把这件事告诉了范蠡,叫他务必小心做好准备,不要像往常那样喝得醉醺醺的,像个疯子似的乱骂。
范蠡听后,不屑一顾:“是他来请我,又不是我请他,准备什么!”
那天,一位小官骑着匹马,刚走到范蠡住的村边,就见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手里提着酒瓶,喝得满脸通红,身上沾着猪粪,摇摇晃晃走了过来,对着骑马的小官喊道:“你就是文种派来的官吧!告诉他,哪有这样请我的。你,你快给我滚回去,这哪是干大事情人的做法!”说着,他把酒瓶朝马头摔去。马一受惊,把那位小官摔了下来。小官没有去追受惊的马,而是恼羞成怒,挥着马鞭朝范蠡身上抽来。范蠡在地上打了个滚,像碌碡似的滚走了。
小官回去以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文种讲了。文种听后,范蠡的那句话总是在脑际回旋:这哪是干大事情人的做法。他觉得这话有理,于是,第二次让小官抬着大轿去请范蠡。
这位小官让人抬着轿,又来到范蠡家。一看门上落着大锁,放下轿后,把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就是不见范蠡的踪影。眼看天就要黑了,一个放羊娃抱着一身烂衣服,摔到轿跟前,“范先生讲了,他的身上有点痒,去找一位医生看病了,叫你们把这衣服抬回去,就能交了差!”
小官只好把范蠡的脏衣服放进轿里,抬了回去,向文种交差。
文种瞧着脏衣服,真的有点气恼了,“不识抬举的家伙!”他用脚去踢那脏衣服,脏衣服一滚,露出了一块白帛布。文种拾起来一看,只见那上边用苍劲刚遒的流利笔锋写着:“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这不正是自己心中所想的吗?”文种拿了起来,不断地念着。“怎么这位疯子范蠡知道自己的胸中大事。定倾者与人,定倾者与人……”他嘴里不断喃喃自语。
求贤若渴,文种当即叫仆人给他收拾行装,他要连夜去见范蠡。可天黑路远,不能行装前去。
第二天天刚亮,文种就步行着去见范蠡。范蠡呢,这天也早早起来,向邻人借了套新衣服,穿戴整齐,在家门口迎候客人,嘴里不断说着:“今日有贵客,我也要以礼相待。”引得旁人都叽笑他,“你两次都把人家给疯走了,今天哪会有贵客来,真是白日做梦!”
话音刚落,文种就走上前去,握着范蠡的手道:“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前两次多有冒犯,请您多多包涵。今天我是专到府上求教,请多多赐教!”
“走,到屋里坐。”范蠡像老朋友似的把文种拉到家里。他俩整整在屋里谈了一天一夜,谈得是那样投机,那样亲切,两人都相见恨晚。
他俩在屋里谈话,一会儿鼓掌大笑,一会儿掩面大哭,共同的语言,撞击命运,撞击人生。笑吧笑吧,笑到太阳落山;哭吧哭吧,哭到月亮升起。原来他俩早就相互倾慕,相互敬佩。
总得要有分手。文种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范蠡则步步相随远送。文种说:“我等你到来,完成大事业!”范蠡说:“时机一到,我定会前去找你的。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就这样,他俩相互告辞。过了些年,范蠡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决定去找文种。他走的路线正好经过卢氏,不知怎的,在卢氏的一个地方又停了些时候。
上了年纪的人讲到这里突然停住,想了一下说:“前些日子卢氏来了几个人,到范蠡住的地方翻腾了一阵子,说是范蠡在他们那个地方教老百姓养蜂,教老百姓修渠引水、灌溉良田,还抽出时问给老百姓看病,在那里留下了一串串好事。他们为了纪念范蠡在那个地方做好事,就把原来叫榆树沟的地方叫范蠡了,所以他们到范蠡老家来找纪念物,说是修庙祭祀用的。说不定你要找的宝贝叫卢氏的人拿走了。”
文子听了上年纪人的话,走到塌倒的房子跟前,根本进不去,他翻腾了一阵,什么宝物也没有找到,只好再返回卢氏范蠡住过的地方,去寻那宝物了。
文子骑马返回卢氏,沿洛河东行,两岸青山相连,鸟声不绝于耳,山花烂漫,香气袭人。眼前洛河清流,晶莹见底,河湾中鱼群如梭,两岸人隔河相望,渔歌互答。他顾不得欣赏洛河两岸迷人的景色,只顾策马赶路,走着走着,前边的留村挡住了去路。只见村口放着许多养蜂箱,几乎把通往村子的路都放满了,成群结队的蜜蜂在村子的上空飞舞着,就像一把飞动的伞,在村子上空飘移着,遮下一片片黑影。
养蜂老人看见文子来了,连忙抱了一罐蜂蜜递给他:“尊贵的客人,请下马歇歇,喝罐范蠡先生给我们留的蜂蜜吧!一来解渴,二来清火,看你都跑得满头大汗了。”
文子也真的渴了,下马端起养蜂老人递过来的蜜罐,喝了两口,道:“好甜呀!怎么这蜜蜂是范蠡教你们养的。”他真想不到范蠡竟然会养蜂。
“是这样的。”养蜂老人像数家珍似的,讲起了范蠡当年教他们养蜂的事:
留村原来住着一位祖传养蜂的老人,每年收获蜂蜜数千斛,蜂蜡也相当多,有时他家的财富比得过一个侯。老人死后,他的儿子继承养蜂业,但不到一个月,有的蜜蜂就开始全窝飞去,可他却不闻不问。没几年功夫,蜜蜂全飞光了,他的家境也就贫困了。
范蠡接到文种的书简,叫他前去越国,可他的一位好友病了,需要几种名贵药材,听说卢氏的药材好,便到这里来找。
范蠡“出山”前非常注意一个地方的商情变化,当他在这里采了几味药后,觉得过去这里养蜂曾热气腾腾,现在却萧条荒芜,原因何在?一位老人告诉他:“从前这家老人养蜂,园里有草屋,屋里有人守护,把木头剖开挖空当蜂房,既没有缝隙,也没有烂木的臭味。那蜂房的安放也疏密成行,新旧有序,坐落有秩,窗口有方向,二十五座为一排。一个人掌管着它们,注意它们的生息,调节蜂房的冷暖,修固连缀的木架,按时用泥涂塞漏洞,除掉那些蛛蝥、蚍蜉,覆盖那些土蜂、蝇虫的滋生地。蜜蜂繁殖多了,就顺从它,分开它;少了就给予它,聚集它,不使它们同时有两个蜂王。夏天不让烈日晒,冬天不使冻成冰,狂风吹来不动摇,大雨浇灌不被浸。到收取蜂蜜时,分割出那些多余的就可以了,不能全部割光而用尽。由于这样做,使老蜂安宁,新蜂能得到生息,养蜂老人不出门就能得到它的好处。如今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园屋不修整,污秽不清除,干湿不调理,开关无节制,居处动摇不安定,出入有障碍,而蜜蜂当然不喜欢它居住的环境了。时间久了,毛毛虫爬进了蜂窝还未发现,蝼蛄、蚂蚁钻进了蜂窝却还不禁止,白天鹩鸠掠取它,晚上狐狸盗窃它,却没有人察觉,直到蜂蜜取光了为止,这样又怎么能不冷冷清清呢?”
范蠡听后十分感叹,觉得这位老人不单单是在讲养蜂,治理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把养蜂老人讲的话认认真真记了下来,不断回味着养蜂老人的这些话,又把当时各国的形势分析了一下,觉得“出山”的时机还不成熟,就决定先在这里住了下来,发动山民们来养蜂。完全按照养蜂老人说的办法去做。没多长时间,这里的养蜂业又蓬勃发展起来,而范蠡呢,则从这养蜂中悟出了治国之道。
有一次,范蠡采药归来,骑着一头毛驴在山路上走,走着走着,忽见道上沥沥拉拉洒着一溜血点儿,他下来仔细一看,血还是新鲜的呢。他趴在地上用舌头舔了舔,马上骑着驴飞跑,还嫌驴跑得慢,惊得路上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他在驴身上大声喊:“快让开路,不然少妇的命就没救了。”他策驴快跑,顺着路上血迹,来到一片坟地,那儿正在埋死人。他跳下驴双手分开人群,对着墓坑吼道:“这个少妇不能埋,她还没死!”
正埋的人都愣了,不知出了什么事。范蠡望着墓穴中棺材说:“这少妇没死,快把棺材拉上来,我来救她!”
少妇的男人一听,忙拽住范蠡胳膊,结结巴巴地问:“先生,她确实是怀孕生不下孩子死的!我们刚埋的,难道你能把死人救活?”
“快开棺材,别废话,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旁人听说能救活死人,赶紧把棺材拉了上来,迅速打开了盖。
范蠡从随身带的药囊里拿出一包药,用小姆指盖儿挖了点儿,放进少妇的鼻孔里。随后,产妇慢慢有了气儿,越喘越大,一会儿,“哇”地一声,不但活了,后来还生了个胖小子。众人又惊又喜,没想到范蠡不但教他们养蜂,而且还会医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都把他围了起来,问他是如何懂得医术的。
其实,范蠡学医已是很早的事了,只是他平时不显露罢了。他高超的医术还挽救了楚国王朝的一次危机。有一年夏天,楚王让一位有学问的衡做令尹。衡对楚国王宫的事不十分了解,便询问一位楚大夫。楚大夫告诉他,楚王年轻而庞臣又多,他做令尹不好办,于是衡就装病推诿。楚王不信,派御医前去查看。当时正是五黄六月,天气很热。可御医到衡家里一看,见衡躺在病床上,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捂着个皮袄,一点儿都不觉得热,身上还冒着凉气,整个屋子都是冰凉冰凉的。御医在屋子里冻得直发抖,连忙跑出去向楚王报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病。走到路上刚好碰见范蠡,他知道范蠡懂得医术,便把衡的病情说了一遍。这引起范蠡注意,就说:“让我再去看看。”
范蠡来到衡的病床前也被寒气打了个冷颤,他仔细端详了一阵,对御医说:“病是弱到了极点,不过气血正常!你回去向楚王报告,就说他的病吃上几副药就好了。”
御医走了后,范蠡才对衡说:“先生,你病的确实不轻,过了今天不救,明天就活不成了。”
“什么,我明天活不成了!”衡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我根本就没有病。”
“是的,你这是弄巧成拙。”范蠡指着他的床下说:“你在床下挖着冰窖,身旁又放着冰,才使你穿上皮袄不觉得热。可时间太久了,寒气已浸到了肌骨,再不治就没命了。”
衡看到范蠡揭穿了他装病的原因,大吃一惊,没想到范蠡竞观察得这么仔细,这是要犯欺君之罪的。这时他才感到后悔,忙问道:“先生,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刚才我不是当着御医的面讲了吗,吃两副药就好了。”
“呦,正像您说的,我病得确实不轻。”衡感到身体有些异样,似有一团火,从额头上升又往身下行。凡是火过的地方都冒起了血泡,他急得有些呼不出气,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作垂死的挣扎。
也就在这时,只见范蠡冲到衡身边,掏出自制的药丸,给衡灌了下去。不一会儿,衡就苏醒过来,感到那团邪火没有了,身体也好了许多,连忙起来谢恩。
范蠡连忙拉住他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叫你的家人赶紧把这几副药熬后吃了,才能从根本上治好你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