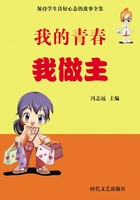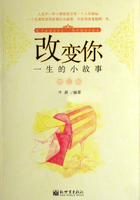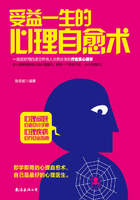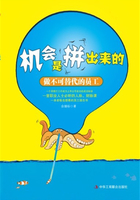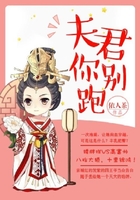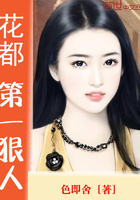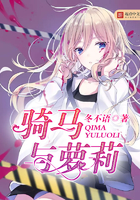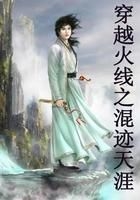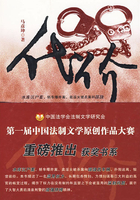系川英夫曾主张说,孩子们做作业最好不要使用橡皮。因为有了橡皮,每当做作业出错时,他们立即就会用橡皮擦去。由于教训给抹去了,同样的错误今后还会反复出现。而如果不让孩子使用橡皮,每当出错时,就在上面画一个“x”,这样,孩子们一翻开作业本,就会看到“错误的记录”,就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每一个人。然而,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别人的缺点,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则视而不见,总想方设法掩饰。对此,系川英夫写道:“这实际上是在姑息自己。如果总是掩盖缺点而不加以克服,就永远不能弃旧迎新,也将无益于发挥创造性。”系川英夫还说:“作为开发型人才,要具有灵活的思想。而要产生灵活的思想,就应当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无论是谁,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应努力加以改进。只有正视缺点,尽力弥补不足,才能产生灵活的思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6)摆脱惯例和固有观念的束缚。
我们的世界正朝向个性化的时代发展,因此,它要求人们都将具有自己的富有独特个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
在个性化时代,想象力和独创性对于开发型人才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系川英夫举例说,1976年,首次世界芭蕾舞比赛在东京举行。比赛结果,在古典芭蕾舞比赛中,苏联、东欧国家名列前茅;而在创作芭蕾节目比赛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则占上风。在那届世界芭蕾舞比赛中,日本虽然在古典芭蕾方面具有相当的水平,但在创作芭蕾方面实在太落后了。
原因何在呢?系川英夫认为:“尾随他人之后顺时适势,紧跟社会潮流,又自我限制行动,以求不越雷池一步;对社会舆论恐惧之至。这种日本社会的倾向使日本很难产生出具有鲜明个性和独到见解的新作品。换句话说,日本往往受到惯例和固有观念的束缚。”
系川英夫在对日本芭蕾舞经过一番分析后进一步深刻指出:“没有想象力,缺乏独创性。这一切都与创作芭蕾舞所要求的条件相距甚远。”因此,系川英夫强调说,作为开发型人才,就不能“亦步亦趋地踩着前人的足迹走,而是另辟蹊径,但又不能完全撇开前人的足迹。”如果“自己的思想老是跟在别人的后面,那就不可能去‘转换思想方法’,而只是‘模仿’和‘追随’别人了。……要转换思想方法,首先必须从这个框框中摆脱出来。”
想象力和独创性离不开基础知识。因此,系川英夫最后写道:“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到来,新时期要求人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好。”“你想学打网球,就不能采取随便玩玩的态度,你需要跟着一位网球教师接受基础训练,然后加入某一网球俱乐部。总之,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从拍子的拿法学起。未来的时代正是这样要求人们的。”沿着自己选择好的道路勇往直前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一旦你敢于探索陌生的领域,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世界。走一条别人不敢走的路,就会发现机会原来无处不在。
米切尔自幼体弱多病,是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剑桥大学毕业后,由于身体不好,无法到企业就职,只好留校,在微生物教研室找了一份为学生实验课做准备的工作。
他每天为学生准备实验课,同时也在考虑自己应该研究些什么。
在他上小学、中学时,所谓生物学不过是捕捕蝴蝶和蜻蜓。但是,人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生物的最小单位已经是比微生物还小的病毒。病毒究竟是生物,还是物体,已经成为研究的中心课题。只有揭示病毒机理,才能揭示这一生命之谜,这成了当时的普遍看法。米切尔明白,蝴蝶和蜻蜓是生物,但无法想象病毒也是生物。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或蜻蜓的切片,就能看到细胞外面有一层细胞膜。但是病毒没有细胞膜,就是用电子显微镜看,也仍然看不到。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细胞膜。
米切尔认为,无论谁,也无论他怎么说,没有细胞膜的东西就不能算是生物,只有细胞膜才是生命现象的关键特征。
他想,如果要研究,最好选择一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例如: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人是怎样从一个受精卵变成胎儿,然后又长大成人的?人患癌症而死,那么癌细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人要吃饭、呼吸,那么食物和空气进入体内,又是怎样变成能量的?
他想,在这些课题中,我可以解决的课题是什么?研究大脑一定很神秘,从卵到人的变化也很有意思,查明致癌原因意义也很重大。不过研究这些课题必须和其他医生合作,自己一人是无法承担的。自己一人可以从事的,只有体内能量的生成机制这个课题了。
米切尔总算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研究课题。于是他又去查阅有关文献,了解该课题在世界科研前沿的最新动向。结果他了解到了以下情况:人类摄人的米和面包到体内后逐渐产生变化,最后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在变化过程中,作为热释放出来的能量,其大部分都贮藏在ATP这种磷酸化合物中。这种磷酸化合物又是怎样生成的呢?似乎许多研究人员都在追寻这一答案。他们普遍认为,磷酸化合物生成的时候,肯定要经过一个中间物质X。他们正全力寻找这个中间物质。另一方面,神经生理学领域却发现,细胞膜上有钠泵机制。钠泵利用磷酸化合物发生变化时产生的能量,将细胞内的钠离子转移到细胞外,将细胞外的钾离子摄取到细胞内,使细胞内始终保持一种平衡的离子组合。
米切尔没有做实验,只是在脑子里反复思索:许多人都在查找这个中间物质,化学我不在行,又缺少实验经验,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从技术上说,我都没有条件去发现这个中间物质。要战胜他们,只有想出一个他们还未发现的方法来。
一天,他像平时一样,踱到研究室顶棚上吊着的木制风扇下面,呆呆地想起来。也许他眼前出现了荷兰风车的景象,总之,他突然来了灵感:细胞膜上的钠泵利用ATP这种磷酸化合物的能量,将细胞内的钠离子转移到细胞外。如果水中的氢离子代替钠离子通过钠泵从细胞外进入细胞内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大概钠泵会往反方向转吧。钠泵如果往反方向转,不就会产生能量,形成ATP了吗?
消耗电能,转动电风扇,使空气流动,产生风。另一方面,风又可以带动风车,风车又产生电能,电风扇和风车的关系与米切尔的设想是一样的道理。
他的结论是:食物的营养成分被一路分解下去,最后与氧结合,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使水成分中的氢离子被转移到膜外,当它再次转移到膜内的时候,就会使钠泵逆转,同时生成磷酸化合物,也就是体内能量的根本ATP。
1961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设想。发表后,他盼望着有谁对自己的设想感兴趣,然而什么反响也没有。
在大学当实验助手的合同已经到期,如果不能升为助教,就不得不离开大学。在大学这几年,他只是拼命思索,没有做什么实验,手边只有《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他也曾把这篇论文提交给大学,希望得到助教的职称,但大学以“该论文缺乏实验上的支持,空想成分大”为由,退了回来。这时,他已经40岁了,失去大学的工作后也无法到私人企业去就职了。
他懒得再去求人,于是回到农村,把自己闷在父母留下的几间房子里。他把放东西的小屋改造了一下,建成了自己的“研究所”。他一心要从实验上证明“ATP是钠泵逆转时产生”的设想。
知道自己没有实验经验,他雇了一名助手帮他做实验,并且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实验证据。他在学会发表了论文,但是,由于他的证明是间接性的,学会方面的反应很冷漠。
米切尔把学会的冷落埋在心里。不过,此时世界权威人士关于中间物质的研究已陷入停滞状态。有人认为ATP的中间物质X,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物质;也有人在植物光合实验中验证了米切尔的理论,认为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终于,日本的K博士从细胞膜上成功地提取了合成ATP的酶。
这种酶突起在膜的表面,当氢离子通过时,它促成ATP的合成。总之,K博士用看得见的物质证实了米切尔的理论。结果,被人们称为怪人的米切尔于197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他为什么能获诺贝尔奖呢?
不动手,总在那里沉思默想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获诺贝尔奖。米切尔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选择了生命科学中重要课题中的一个,并且使用了与许多同时研究这一课题的人们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的思维不仅涉及了生物化学领域,还涉及了神经生理学领域。从不同领域的角度去思考。才提出逆转的设想。他毫不理会来自社会的冷落,也不盲目跟着权威的中间物质说跑,而是坚信自己设想的正确性,这一切给他带来了诺贝尔奖。
如果你现在也能做到身处逆境不气馁,沿着自己选择好的道路勇往直前,那么,你距离成功也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