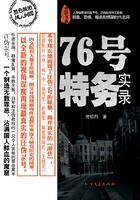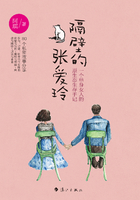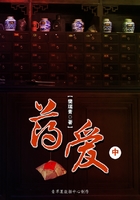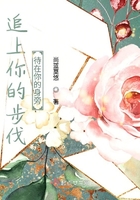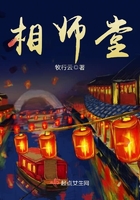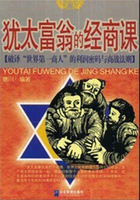黄秋耘
一九三七年仲夏,历时八年之久,对世界现代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中日战争终于揭幕了,作为这出悲壮的历史剧序幕的,就是“卢沟桥事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进犯波兰,其实无宁说,它开始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从那一天起,中日两大民族、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就投入战火之中,血海尸山遍布了神州大地。说也奇怪,这一场断送了二千万生灵的浩劫是在一个美好而柔和的仲夏夜里静悄悄地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命令:全国各大学、高级中学二年级男学生,都要在那一年暑假期间,在当地驻军主持下接受军事训练。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决定,北平学生要积极参加这次军训。一来可以借此学习军事技术,迎接抗日战争;二来可以在二十九军的官兵中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扩大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当时我们都剃掉头发,去西苑兵营报到受训。学生集训队的总队长由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副总队长由三十七师一百一十旅旅长何基沣担任(何基沣早年跟我党某些领导人曾经有过接触,读过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抗战初期入党。他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建国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分别由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营、连、排长(或副职)担任。当时华北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这次军训也着重实战训练,把制式教练放在次要地位。西苑周围的青龙桥、玉泉山、西山一带都是我们野外演习的场所,在这些风景如画的名胜地区上面,我们留下了不少汗水和足迹。
我从来未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开始几周,经过一两个小时刺杀和抡大刀的训练,就汗流浃背,气喘如牛。至于“班攻击”“抢占制高点”等野外演习,消耗体力更大。那一年的天气也有点怪,忽而烈日当空,忽而暴雨倾盆,我们的灰布军服,总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但想到学会了这些打仗的本领,将来总用得着,就咬紧牙关支撑下来了。
集训队的官兵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在二十九军的军官和学生之间逐步建立起亲密的战友情谊。记得有一位姓曹的中队长(连长)一天在接到家书后突然失声痛哭起来,给正在他那个中队里受训的黄诚同志(北平学生运动领袖,任北平学联副主席,抗战期间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看到了,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他家欠了地主老财的债无力偿还,正想将他的妹妹卖掉还债。黄诚同志一面劝慰他不要着急,一面在集训队同学中间发起募捐,一下子就募集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家就再也用不着卖儿鬻女了。边位曹中队长顿时感激涕零,这件好事也在集训队中纷纷传诵,使得二十九军官兵对爱国学生的义举十分敬佩。
七月八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从西南方面传来了一阵闷雷似的巨响。在仲夏季节,打雷是常有的事,因此并未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直到我们在操场上跑步完毕,整个总队按照号音发出的命令集合起来,排成“凹”字形队形,何基沣副总队长在队列前宣布:“昨天晚上十点半钟左右,屯驻在丰台的日军突然以找寻失踪士兵为借口,向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发起攻击,我旅吉星文团奉命坚守阵地,采取自卫行动,目前双方还在对战中。卢沟桥曾一度失守,已被我军夺回,伤毙日军二百多名,我军也有一些伤亡……我是一个军人,守土有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部下的防区内,一寸土地也不会放弃!”他竭力克制着自己,连“敌军”“帝国主义”“侵略”等字眼也不敢使用,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他的眼眶红了,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们知道,军人的眼泪总是十分吝啬的。
七月八日那一天的天气,比往常都要炎热,太阳火辣辣的,间中又有阵雨。训练的科目是野外演习,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热得难受,也许我们的血液的温度比外边的气温还要高。
“卢沟桥事变”是一场很奇怪的战争。战争打响以后,双方都没有一个劲儿打下去,而是断断续续,打打停停。大概由于我方军事当局抱有和平的幻想,竭力避免事态扩大,而日方因兵力不足,要等待援军到达,才好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两军虽然不断在前线交火射击,形成对抗态势,而后方的“和平谈判”仍然在继续进行。
根据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当时二十九军当局作了相当大的让步,除了从卢沟桥撤退中国驻军一条外,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包括赔礼道歉,惩办参与卢沟桥战役的指挥官和取缔华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等等,实际上已经达到丧权辱国的程度。
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确实曾一度达成协议,规定双方都不在卢沟桥驻军,由中国方面的保安队暂时维持治安。
在西苑兵营内部,空气始终是十分紧张的。每天大清早集训队就拉到郊外去“打野外”,直到傍晚才回兵营,以防日本空军突然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当时我方不但没有空军,甚至连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也没有。为了增强兵力,集训队总队部动员学生自愿报名入伍,入伍后就立即发给供实战使用的步枪、刺刀和少量子弹,但是没有发给手榴弹,大概是怕我们投掷手榴弹的技术还不够熟练,容易发生意外。
与此同时,和我们一起集训的南京政府达官贵人的子弟纷纷接到“父病速归”“母病速归”的急电,他们拿着这些急电向总队部的值日官请假。由于这些电报的落款大都签署着院长、副院长、部长或次长的名字,值日官根据上峰的指示,一律都批“照准”,但是又嘱咐他们离队时行动要严格“保密”,以免影响士气。其实这么多人突然离队,“保密”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士气倒不见得会有多大影响。因为无论军官也好,士兵也好,学生也好,谁也不相信这些公子哥儿有决心把热血洒在抗日前线的沙场上。他们悄悄地拿着行李卷走了,我们既没有“欢送”他们,但是也没有奚落和嘲笑他们。
虽然带点“临阵磨枪”的味道,但是,集训队的军事训练还是非常紧张地进行着的。在兵营的周围都修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堆砌起沙包,四周通道都增设了岗哨,规定通行口令,紧急集合几乎每隔一夜就举行一次,总之,一切都处在“临战状态”中。
二十九军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的同时,日本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动员了本土的三个师团、部分关东军和屯驻朝鲜的精锐部队,逐步向华北大举增兵,甚至发出了秘密的动员令。他们训令北平驻军,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以随时撕毁。
可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和平未到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七月十七日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公开演说,申明上述立场。这等于向日本人宣布,我们是随时准备妥协的,请高抬贵手,不要把我们逼上梁山。
不管庐山上的”要人“们怎么说,在西苑兵营里,我们的刺刀和枪口还是对准着模拟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稻草人。我们这些”丘九“们跟两年前已经大不一样,再不是手无寸铁,而是武装起来了,虽然是很简陋的武装——汉阳造的七九步枪、刺刀和几十发子弹。
根据今井武夫和齐燮元代表日中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冯治安为师长的三十七师和以赵登禹为师长的一百三十二师调防,由一百三十二师进驻北平。赵登禹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个稳健的、容易欺负的老好人。他当时绝对不会预料到,仅仅在十多天之后,他就丧命在日本人的枪炮下。至于学生集训总队是武装的抗日组织,当然要在取缔之列。”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躲避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那时突然返任了。他在七月十八日亲自到天津向新到任的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赔礼道歉(香月的前任田代中将已于七月十六日病故),十九日回到北平,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拆除北平城内外的一切防御工事,驻在城内的二十九军部队也开始撤出了一部分;二十一日,下令解散学生集训总队,勒令我们缴出全部武器。同时在北平全市贴出所谓”安民告示,宣称“卢沟桥事变”“事属局部地区问题,业已和平解决,望同胞安心,切勿轻信谣言”。
学生集训总队解散前,由副总队长何基沣发表“告别式”讲话。他满腔悲愤,涕泪交流,主要是向我们表白他的爱国宿愿,和这次忍痛执行上峰命令、解散学生集训队的不得已苦衷。他认为,中日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希望不久的将来跟大家在抗日战场上再见。在场的二十九军官兵和学生,大部分人都感动得直掉泪。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像何基沣这样的爱国军人毕竟是不可多得的。
我回到清华大学,喝了一斤黄酒,就蒙着头大睡。我忍受不了那满腔悲愤,认为抗战抗不起来,一切都完了;华北继着东北之后,快要拱手奉送给日本人。我的入党介绍人何维登同志跑来安慰我,说局势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悲观,仗终归是会打起来的,我们接受了一个多月军事训练,并没有白费,至少学会了打枪和刺杀的基本动作,将来总会用得着的。
我觉得,何维登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人,但他的话也不见得完全没有根据。从一切迹象看来,尽管宋哲元多方委曲求全,日军方面还是步步进逼,增援部队源源入关,集结在天津至北平一线,前方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仍然不断发生。最重要的是,中日双方的武装部队似乎都已经作出了不惜一战的决定,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罢了。
局势的发展比我们的预料还要快得多,不到一个星期,大战就爆发了。从二十八日午夜零时开始,日军对南苑兵营发动攻击,重炮声和机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之久。天亮后不久,日本空军对西苑兵营轮番轰炸,把营房和附近的建筑物炸成一片瓦砾,假如学生集训队没有解散的话,我们恐怕也很难幸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都是在南苑战役中阵亡的,一百三十二师几乎全军覆没。宋哲元命令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暂时代理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留下来跟日军“继续交涉”,他自己却率领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要员”从西直门逃出北平。二十九军在宋哲元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政策下,断送了上万名官兵的生命,日军只付出极少数伤亡的代价,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平城。只是由于驻通州的保安队在平时与我党早有联系的第一总队指挥官张庆余、第二总队指挥官张砚田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袭击冀东伪政府的长官公署,当场歼灭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以下的日本人二百六十多名,还俘获了著名的大汉奸殷汝耕,可惜在突围战斗中被他逃脱了。
鉴于日本陆、空军已向南苑、西苑发动进攻,严密封锁永定河沿岸,困守在清华园里的我们无法通过封锁线向西南方向突围,地下党和民先大队部临时决定,让同学们分散入城,暂时隐蔽,待机南下。当时公共汽车、校车、火车已经全部停开,我用挎包背上几件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骑着自行车进城,沿途经过海淀、黄庄、白石桥一带,居民早已逃散。路旁的水沟和田野躺满了二十九军阵亡将士和被流弹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紫竹院附近的小溪流全部给鲜血染红了,一片战场上的荒凉景象,十分凄惨。西直门是洞开着的,守卫城门的是临时维持治安的保安队,而不是日军,因此我没有经过什么盘查就进城了。进城后,我按地址去找过几家平时熟悉的亲友,都已人去楼空,当时我的处境真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了。我记起了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的黄宛同学(他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心脏病专家)的住址,就前去投靠他。他的母亲是大陆银行的经理,算是北平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象这样的大户人家当然是比较保险的。谁也不会怀疑他们会窝藏共产党和危险人物。当时黄宛不是党、团员,也不是民先队队员,他大概是知道我的政治面貌的,但仍然冒着极大风险收留了我,全家都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这种患难与共、舍己救人的革命情谊是非常值得珍贵的。在三十年代中叶,又是在沦陷区,一个以银行经理为女主人的家庭,在战乱中竟肯以身家性命作为代价,来庇护一个爱国青年,更确切地说,一个政治亡命者。我从这次经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哪一个阶层里都会有好人,正如高尔基所说的,在乌鸦群里有时也有白鸦的,这恐怕不能算是“人性论”吧!
当时,我们有时还能在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碰碰头,跟党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听到一些消息和指示。八月中旬,北宁铁路的平津段开始恢复通车。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决定,凡是家庭不在北平而政治面目比较暴露的同学必须尽快离开北平。第一个目的地是天津租界,然后待机乘船南下,到南京或武汉集中,再定去向。
北平距离天津只有一百三十七公里,按照一般火车运行的速度,大约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当时每天只开出一列火车,车票很难买到,而且一般要走十二个小时以上。日本宪兵队在天津终点站要检查所有的旅客,任何人的面容和举止只要稍涉嫌疑,表现出他可能是军人、大学生,或者是抗日分子,就会马上被扣留下来,严刑审讯。刚巧黄宛有一个姓凌的亲戚是在天津租界里开烟叶店的,他来北平收账,因战争影响滞留下来,算盘、旧账簿和商店图章等等一应俱全。黄宛一家让我冒充他的小伙计,这是最安全的身份。当然,我得马上学会打算盘和一些做烟叶买卖的行话。
计议既定,在八月十三日,也就是上海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我们就乘火车离开北平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乘客几乎全部都是忧心忡忡的“难民”,连上厕所也很困难,得跨过十多个人的身上。当天晚上八点多钟我们才抵达天津。车站上警卫森严,围上了铁丝网,只剩下一个出口,每个人出站时都要经过日本宪兵队和便衣特务的严格检查和盘问。幸亏我的旅伴凌老板具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总算顺利通过了。我看见有几十个男女青年给扣留下来,等待着这些人的肯定是十分悲惨的命运,即使不很快被处决,也至少会受到酷刑拷打。
我们出了车站,走到横跨华界和租界的万国桥,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十点钟,戒严开始了,守卫在桥头的外国巡捕禁止行人过桥,我们只好在桥头露宿了一夜。这一夜我们当然是无法入睡的,但总算逃出了鬼门关,心情稍为平静了一些。那位凌老板歪着头向我傻笑,他当然不知道,我是一个“危险人物”,可能连累他,甚至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过了租界,街道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熟悉的脸孔越来越多了。天津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经营了多年的“基地”,这时候,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张牙舞爪,政治性的绑架、暗杀案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因此,我们碰到熟人也不敢公开接近,只有点点头打个招呼,或者用眼色示意。我们都等候着开到南方去的轮船,但开航的外国轮船只有寥寥几艘,多半是由货轮改装成的客轮,船票的黑市价钱越来越高,而且很不容易弄到。通过凌老板的帮忙,我总算弄到了一张怡和公司“恒生号”轮船的统舱客票。说起来也凑巧,这条船我是乘搭过的,那位华人“总管”还认得我,他对我特别照顾,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给我找到一个有帆布遮头的不受到日晒雨淋的地方。
上船后没有多久,我就在人丛中认出了陶家淦同学,我把他拉到一起,共同享受这块有帆布遮头的甲板。他在船上一再问我,是plus(加)还是minus(减)(这是清华学生特有的暗语,管党员叫plus,非党群众叫minus),又瞎猜谁是plus,谁是minus,我一律笑而不答。不过。我可以肯定他是minus,在那种时候,那个场合,假如他是plus的话,绝对不会谈论这种问题的。
我的船票是买到上海的,开船前就宣布,轮船在威海卫、烟台、青岛各停泊一天,装卸货物。到烟台那天,“总管”对全体乘客宣布,由于战争的影响,轮船不打算在上海停泊了,离开青岛后就直开香港。愿意去香港的乘客可以补票,愿意在青岛登岸转乘火车去南京、上海的,也悉听尊便,可以领回部分船费。
我和陶家淦都在青岛登岸,这个滨海城市美极了,恬静得出奇。在仲夏季节,青岛通常都挤满了度假日的人群,可是那一年,长长的雪白色的汇泉海浴场沙滩上只有十多个外国籍的游泳爱好者。我们住的那家旅馆,老板已经逃跑了,只剩下一个守门的老头儿,他听说我们是从北平逃难出来的学生,没有收房租,让我们随便付点酒钱就算了。眼看到这个美丽的、可爱的城市正在准备迎接血和火的洗礼、敌人残暴的占领和劫掠,而在我们这一方,不设防、不驻军、不作任何应战的准备,只有五百名警察在“维持秩序”,我不由得感到一阵强烈的痛苦,仿佛眼看到一个美丽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女孩子即将落入强盗的手中。
我们毫无游览和海浴的兴趣,第三天就坐上了不时受到日本飞机轰炸和扫射的火车,离开青岛取道济南到南京去。陶家淦有一位在南京政府当中级官员的舅舅,我们好歹可以在南京找到一个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