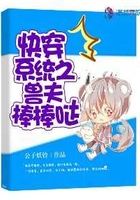灯火通明的屋里,祝新,还有一个短发红衣的女孩子,两个人正拥抱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只看到祝新宽厚的肩膀,那短发红衣的女孩把头深深埋在他的肩上,幸福地笑着,闭上了眼睛。
夏亭拉住红菲就跑,千万不能让小颖看到。
“喂,今天什么日子,好邪!”红菲气急败坏,“告不告诉小颖?”
夏亭犹豫着,“别告诉她了,让她高兴几天,反正下学期祝新就毕业了。”
“那咱们不是一起骗她吗?”红菲不解。
小颖已经买了雪糕往这边跑来了,夏亭用眼色暗示红菲,红菲闭嘴。
她们坐在开满金钟花的长廊下吃雪糕,凉凉的天气,凉凉的雪糕,凉凉的心绪。
“明天我想去K物街买双高点的皮鞋,周末跳舞,Eight-Eight实在太高了。”小颖兴致勃勃。
红菲没好气地说:“省点儿吧,有什么用!”
夏亭急忙咳嗽两下。
小颖问:“怎么了?”
红菲这才说:“你去不成,到时候你鼻头生疮!”
小颖气得要打她,红菲又装作无辜,“我失恋,你还打我?”
小颖气得牙痒,也只好作罢。
上午选修课,夏亭没修,窗外又下起大雨,她吃了早餐,恹恹的样子,打开日记,上面已经是四个“正”字了,秋子就这样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再没有人放她爱听的歌,再没有谁的声音可以让她迷醉、快乐,没有期盼和兴奋,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抓住,声音在空气里,在时间里,弥散。
她机械地在本子上写着秋子秋子,她看着她画的想象中的秋子,那幽深的眼眸,薄薄的紧闭的双唇。她本来想给他画一副眼镜,她想象中的秋子该是这样的,但她又想他的眼睛面对自己时,连一点儿隔膜也不要有。
她长长久久地、绝望地看着天空。上天,我从没奢望接近他、得到他,我只是这么远远地听着,我只想每天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够了,满足了。上天,最起码让我知道他好好活着,他平安无事,就行了,求你了。
一颗大大的泪珠啪地掉在日记本上,无数个秋子都模糊湮染在水里。
夏亭不知不觉地抱着本子睡着了。
梦里,她到处找他,每一个启示都让她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可是每一个地方,秋子都刚刚离去,她总是慢了一步。
她累了,跪倒在地上,忽然,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是的,真真切切的,不是做梦,是真的。她蒙眬地从梦中挣扎醒来,眼睛还没睁开,却清楚地听到有人在窗外说话。
“那就谢谢你了,难为你拿了这么多吃的来给我,光是鸭掌就带了五斤,够重的。”
“不客气,阿姨让你有空儿多打电话回家。”
“你也是啊,到了那边,多联系啊。”
“好的,再见。”
真的,真是秋子的声音,夏亭一下子坐了起来,她的心要跳出来了,来不及多想,滑下床,鞋也来不及穿,就拔腿往外冲去。
走廊空荡荡的。
她冲下楼梯,楼梯静悄悄的。
她跑到大门口,雨水白茫茫的。
秋子,秋子。不是幻觉,是真的,真的。
然而,她到处找他,每一个启示都让她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可是每一个地方,秋子都刚刚离去,她总是慢了一步。
她又慢了一步。
她伤神地慢慢回去,这才发觉光着的脚给小石子硌得生疼。
她冲动地去找刚才说话的那个女生,好像是二年级的师姐,住在她们隔壁的。
那屋里有几个人,奇怪地看着贸然敲门的她。
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落荒而逃。
屋外雨下得越来越大,有如白烟,一切都看不清、辨不明。
不行,我要见他,混乱的思绪中这是唯一的线索。
她的心跳得厉害,不愿多想,不想犹豫,她把那瓶子幸运星——三百六十五颗藏在怀里,撑了把小伞,冒着大雨往广播站冲去。
“我找秋子。”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或许是因为冷,她的裤脚全湿了,滴着水,头发也濡湿地贴在额上,但那瓶子安然无恙,暖暖地贴在心口。
“哦?他今天来过,不过现在走了。”开门的那个留着飞机头的男生说。
“他什么时候再来?”她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他退学了,不一定来。”
“为什么?”
“为什么啊,好像是病了——哎,海德,秋子干吗退学来着?”飞机头回头问屋里。
有个男生答道:“好像是出国留学吧,不大清楚。”
飞机头耸耸肩。
注定要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是。夏亭的心低下去,脸上还装作无事。
她轻轻地把玻璃瓶双手送过去,“麻烦你帮我转交给秋子,好吗?”
飞机头接过来,笑了,“呀,这是第几瓶了,秋子怎么总收到这玩意儿?”又看着夏亭点点头,“好吧,我们一定给你转交,放心,你不留个名字口信什么的吗?”
夏亭摇摇头,低头就走。
门在她身后关上,还可以捕捉到若有若无的一句,“秋子这小子,真是好……”
回到宿舍她整个人都湿透了,爬上小床,换了衣服,她仰面躺下,泪水凉凉地淌了满脸。
不一会儿她们回来了,进门小颖就兴奋地喊:“有辣椒薰鸭掌吃啦!”
几个人在下面叽叽喳喳地吃,小颖不住地叫夏亭下来,“你快点儿吧,这可是正宗的湖北名小吃!师姐犒劳的呢!”
红菲故意吃得津津有味,“夏亭,我吃光了,快,真好吃!”
“你们吃吧。”夏亭平静地应了一声,向墙里转过身去。
红菲蹑手蹑脚地把脑袋钻进床帘去,一眼看到摊开的日记本上秋子的画像,惊奇地叫了声:“咦,这不是秋子吗?真像,就是少了副眼镜。”
夏亭急忙转头把本子抢过去,红菲看到她的脸上全是泪痕。
红菲默默地爬上去,轻轻扶着夏亭的肩膀,“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但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哭吗?”说着,眼圈已经红了,而不知何时,小颖也凑个脑袋进来,咬着嘴,默默注视。
只有秋雨,仍在窗外潺潺。
一场雨后,紫荆花落得又多又密,层层挨挤着,像艳丽的蝶冢。她们三个总要一路绕开花瓣,不住地叫着可惜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的辣椒薰鸭掌委实有些功力的,看看小颖的鼻子,好像真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
“你鼻头要生疮了,信不信?”红菲不怀好意地指着小颖。
“去去去,只是有点儿痒。”小颖有点儿害怕,急忙拿出小镜子照照。
“就是,一个小红点,明天会膨胀爆炸。”红菲气她。
小颖黑着脸,左看右看,自言自语:“才不会呢,我今晚擦了药膏,明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那鼻头上的一点高原红却又红又肿,竟然真的长成了个大疮。
小颖气得要哭了,一个劲儿怪红菲咒她。
红菲难以置信,“天啊,我的预言这么准,难道可以做巫婆?”
小颖没心情和她啰唆,整天地坐立不安,每隔五分钟就拿镜子出来照照,三番五次想动手去挤。
夏亭忙阻拦道:“这是危险三角区,你可忍忍吧。”
“怎么忍啊,这么大个疮,我哪敢见人!”小颖又气又急,不禁滚落一颗泪珠,“丑死了,要多丑有多丑,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红菲、夏亭面面相觑,又是担心又是释然,说真的,她们宁愿她错过这次晚会,错过祝新,错过这场痛。
芦荟原汁、氯霉素针水、先锋、各种进口的药膏……任何“只要青春不要痘”的东西,小颖全部试过了,但直到晚会这天,她可爱的鼻子仍大红大紫着,红菲暗暗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形容,“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日,美若甘酪”。
雪纺纱滚蕾丝的白裙子、簇新的白色高跟鞋、银白的镶滚珠小手袋,静静地期待着小颖的白雪公主梦。而这晚,耳听着花枝招展、衣香鬓影的女孩赴会的轻巧活泼的脚步声,小颖只能把自己深藏在低垂的帘幕里,镜子里的女孩,哀怨的企盼的眼,天快黑了,奇迹再不会出现,真的不会出现了。她懊恼地把镜子扣在桌上。
小颖终于还是错过了那一舞倾情。
她什么也不知道,不知是好,还是不好?
又是一个秋夜,深秋的夜,接近冬的气息,多了沉实、冷静的夜。
她们在空旷的球场上坐着,远处喧闹着欢歌笑语,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
大朵的紫荆花旋转着飘落,轻轻地,缓缓地,像声微微的叹息。
在清凉的石阶上,红菲满捧着腮,夏亭轻抱着膝,小颖微仰着头,这么沉静地坐着。
沉静的风,沉静的雾湿楼台,沉静的星,沉静的长沟流月。
这一季很快就要过去。
有些爱,注定要藏在心里,只能藏在心里,最好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