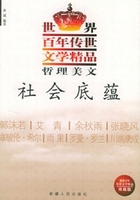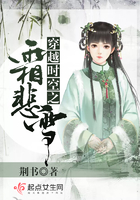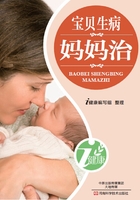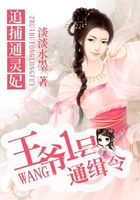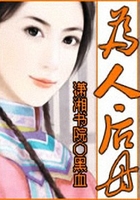【题解]
诗人以锐敏的观察力,善于捕捉蜃散、虹残、风翻白浪、雁点青天这些瞬间即逝的景物或者易于变幻的景象,以形象明快的诗笔,描绘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图,正像张籍收到诗和画后,答诗所说的“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人工下笔难”中的“物色从诗出”,其景象俨然如在眼前。那淡烟、疏雨、斜阳、蜃楼、楼阁、残虹、桥梁、浪花、雁行等等一系列繁纷零乱的景象,被诗人组合成一幅完整美好的秋景图,动静变化,浓淡对比,极富变化之致!何为“中隐”?白居易在诗中作了很理性的阐发。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中隐”可以说是白居易的创造发明。“中隐”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代,士大夫处世不外乎“仕”与“隐”两途。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世途艰险,“出仕,有宦海风波之险;归隐,有生计无着之虞。”白氏的“中隐”观念则切实可行,影响深远。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第五句以下八句即所谓“中隐”。蹇长春在其“白居易‘中隐’观念及影响”中论述得很详细。“中隐”,即在出处进退之间“执两用中”,走中间道路。“隐”在“留司官”,也就是诗人早在元和十三年(818)四十七岁时在《江州司马厅记》中所提出的“吏隐”:自求外任,或者担任闲散之职。十一年之后,几经迁徙,即大和三年(829)又由罢刑部侍郎,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仍然是一闲散官职。“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寄微之及崔湖州》)说明白居易以外任地方、闲散官为“吏隐”。这首诗则由“吏隐”而过渡到了“中隐”。“中隐”就是“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多么安闲舒适的仕隐生涯!既不同于“相逢尽说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又有别于“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清蒋士铨〔临江梦〕《隐奸》)。
“君若好登临”以下十二句,诗人采用排比句式,进一步渲染、铺排“中隐”生涯那种“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乐天知命、安稳闲雅、出处舒适的优雅无虞。诗人不厌其烦地说:你如果喜欢登山临水,“城南有秋山”;如果喜爱游赏逸荡,“城东有春园”;如果想一醉方休,“时出赴宾筵”;如果想恣纵欢言,“洛中多君子”;如果想悠娴高卧,“但自(尽可)深掩关”;这里也没有车马来客,仓猝到门前。真有“门庭冷落车马稀”之感!“君子”,犹能言善辩之士。“掩关”,关窗闭户。“造次”,造然,仓猝,急遽,突然。白居易晚期由“兼济天下”而趋于“独善其身”,形成“中隐”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其身世有直接关系。他“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瓯北诗话》卷4)尤其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加之屡次遭贬,尤其江州之贬,深晓宦途风险,从元和十三年(818)到太和三年(829),经历了十一年由“吏隐”过度到“中隐”的阶段。对白氏而言,在思想上很复杂,既有儒家的“乐天知命”,又有道家的“知足知止”,于是成为封建社会出处进退“执两用中”的一种典型。它既不同于屈原那种忠君爱国、以身殉道,终因壮志难酬而忧愤沉江一死;又不同于陶渊那种退隐田园、消极避世,虽说息影山林,而并非无意于世事。诗人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顺“时”(“时势的泰否,世运的兴替”)认“命”(“个人”的遭逢、际遇),无可奈和,在其《达理二首》、《初入峡有感》、《咏拙》等诗中一再慨叹“况吾时与命”、“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于是他认“命”了,“时耶?命耶?吾其无奈彼何……”(《无可奈何歌》)“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咏怀》)“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则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一枝足自容。”(《我身》)……直至老年,诗人仍然慨叹不已,但却以恬淡自处,这就是诗人大半生的人生领悟和仕途体验。
正因为“中隐”观念在封建时代的宦海沉浮中,既不与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又不至于招致灭顶之灾,故白居易抒发“中隐”生活情趣的“闲适诗”作倍受士人喜爱而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