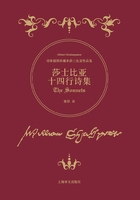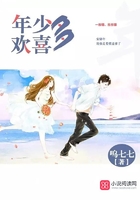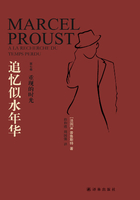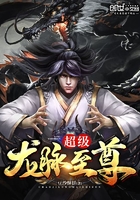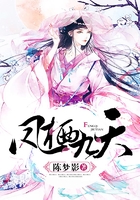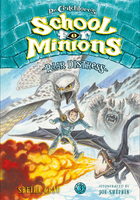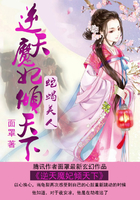【题解]
元和四年(809)作于长安。当年元稹以监察御史于三月七日离开长安,往东川(今四川三台县,唐代为东川节度使所在地)奉使审案。元稹走后,诗人同弟弟白行简与李建三人游曲江、慈恩寺,后到李建家饮酒。饮酒时记挂好友元稹赴川行程,作了这首诗。“李十一”,即李建,字杓直。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因李建排行第十一,故称李十一;元稹排行第九,故称元九。因饮酒时计算元稹行程,想必今日已经到达梁州。元稹如期到达梁州汉川驿后,梦见同诗人一道春游曲江,而且作了《梁州梦》诗及序,记述梦中事。白行简《三梦记》及孟《本事诗》均有记述。
白居易同元稹,政治上志同道合,诗歌上共称“元白”。二人友情颇深,患难与共,相互唱和诗很多,本诗仅是个中之一,且是刚刚分别四、五天,并于同一日赋诗相忆念。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这首诗是白居易曲江春游、而好友元稹刚刚离去之际,“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
首句又作“春来无计破春愁”。据当时白行简《三梦记》所记,此说应当是正确可信的。而《白氏长庆集》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其实旧时因印刷落后和传钞之故,以及作者自己事后推敲改易,出现舛误、异文是正常现象。但就本诗而言,事出有因,笔者很赞成陈邦炎先生的说法,行简所记乃初稿原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定稿。改“春来无计”为“花时同醉”,在章法上更合理,在承转上更贴切。律诗讲究起承转合,首句“起”,次句“承”,三句“转”,末句“合”。次句中“酒筹”是饮酒行令时所用的筹码。在首句与次句关系上,改后“花时同醉”与“醉折花枝”二句承接得更紧密,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使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时,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而言,“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若首句一开始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如此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而后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出全诗的风神。末句“计程今日到梁州”,“梁州”又作“凉州”,显然是错误的。在唐代,凉州指甘肃西部一带,而梁州则指陕西南部一带。当时元稹往东川,陕西乃必经之路,不可能绕道甘肃,否则也不可能按本诗、白行简记所说的日期按时抵达,故应作“梁州”,况《才调集》卷第五也作“梁州”。“计程”由转句“忽忆”而来,是“忆”的深化,主要体现着情意的表达。按常理,故人或亲人别后,居者总是不断忆念,常常会计算此时是正在途中某处或此时已到达目的地。“今日到梁州”,诗人意念所及,深情所注,即席拈来,信手写出这句,非常符合实际和常情,给人以极其真切之感。
诗人在短短的一首诗中,对朋友元稹行程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他写这首时,元稹正在梁州,同时写了一首《梁州梦》并序。诗曰:“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序谓“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白行简《三梦记》所记白诗已如上述,所记元稹《梁州梦》亦略有不同,但所记日期、事实悉同,并说:“日月与游寺日月率同。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本事诗》也有“……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的记述。
总之,这首诗“前二句以近者言,后二句以远者言,此诗家之远近格。”(《唐诗绝句类选》)诗人即席拈来,不事雕饰,“意浅情深”、“情文相生”(《删订唐诗解》),以极其朴素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真挚亲切之情谊。
白诗、元诗,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所述“合若符契”。两诗写于同一天,押的同一韵;两情“千里神交”,异地同思,相互感应,无论是内容之感人、艺术之魅力,无不给人以真与美的享受。
尤其是在文字结构上,首二句写“与李十一芳时同醉,借解春愁,以花枝作酒筹,想见其风趣。”后两句写“我辈欢娱,而故人行役,遥记征程辛苦,计此日可抵梁州。非特临觞怀远,其平日之抡指征程,关心驿路,可知矣。”(《诗境浅说续编》)同元稹的《梁州梦》一样,如实写来,既未渲染,又未雕琢,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全在其中。
在语词运用上,虽朴素、浅显,但“语尚真率,然浅而不俚,方是妙境,此诗得之。”(《唐诗解》),所谓“元轻白俗”,但如“此诗浅而较真,犹胜填词一格。”(《增定评注唐诗正声》)这正是白居易诗“老妪可解”的最大特色。
杨柳枝词八首(选四)
约大和末年(833~835)再官太子宾客分司时在东都洛阳作。“杨柳枝”,宋王灼《碧鸡漫志》载:“《杨柳枝》:《鉴戒录》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辈诗云:‘万里长江一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则知隋有此曲,传至开元。《乐府杂录》云:‘白傅作《杨柳枝》。’予考乐天晚年,与刘梦得唱和此曲词……又作《杨柳枝二十韵》……注云:‘洛下新声也。’刘梦得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盖后来始变新声,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之外,还有《杨柳枝词》:“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杨柳枝》本为唐教坊曲名。歌词形式如“一树春风千万枝”,系七言绝句,此题专用以咏柳。
其一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
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六幺》、《水调》、《白雪》、《梅花》均系曲调名称。《六幺》:一名“绿腰”,又名“乐世”、“录要”,是当时流行于京城的琵琶曲名。元微之《琵琶歌》有“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凉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笼。”《水调》:系一种音调的总名称,后来依之所制的曲子即称《水调歌》。唐代又出现《新水调》。诗人有《听水调》诗:“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据记载:“水调第五遍,五言,调声最愁苦。”此曲共有十一叠(又称“遍”或“段”),前五叠为歌,其他为“入破”。
《白雪》:本是古典名曲,唐高宗曾以其自作的雪诗《白雪》作曲辞,又有吕才所制《白雪》琴曲。《梅花》:即《梅花落》,本为笛曲,唐代大角曲有《大梅花》、《小梅花》诸曲名。上述均系当时最流行的古旧曲。所以第三句说“古歌旧曲君休听”。那么,听什么呢?第四句作了回答。“新翻杨柳枝”:即新创作的《杨柳枝》曲调。刘禹锡的诗有“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都是七言四句诗的形式,但音节和绝句不完全相同。这些曲词多为名实相副的咏杨柳之作。
其二
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
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
“陶令”:晋陶渊明,曾官彭泽县令,故称“陶令”。“门前四五树”,源于陶氏《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的故实。“亚夫”:汉周亚夫,为绛侯周勃之子,文帝时匈奴入侵,乃使刘礼、徐厉、亚夫三将军分别驻霸上、棘门、细柳。文帝亲赴诸营犒赏军队,到刘礼的霸上、徐厉的棘门,随行人等径直驰入,如入无人之境;但到周亚夫驻的细柳营时,军士戒备极严,没有将军命令,任何人也不许进入;皇帝只得以符节传命,才准放行。皇帝进入大营,亚夫持兵器揖而不拜,只以军礼相见。文帝出军门后叹赏道:“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史记·绛侯世家》)“细柳”,本名细柳仓,在陕西咸阳西南二十里。此时已不一定与柳树有关系,而后世诗人多用为咏柳的典故。“何似”,这里不作“岂如”或“哪里像”解,而是把两种事物并举相比予以品评比较。“东都”,唐代称洛阳为东都。第四句“黄金枝”特指正二月间的杨柳刚发的浅绿嫩黄枝条。“洛阳桥”,专指洛阳皇城端门南之天津桥。《两京记》:“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辟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白氏的《天津桥》诗有“柳丝袅袅风缲出”,就是咏桥边之柳。
其三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清风无限情。
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
这首不用典故,极力形容柳条柳丝的轻柔飘拂。“依依”、“袅袅”、“青青”三个重叠联绵词,将春柳娇柔、轻盈、青嫩的飘拂之态活画出来。那婀娜多姿,确然“勾引”了“清风无限情。”将柳条人格化。“白雪花繁”,形容飘飘升浮的杨花、柳絮;“绿丝条弱”描摹杨柳枝条如丝一般柔嫩娇弱,“不胜莺”——连一只黄莺儿落在枝条上也禁不住,足见枝条之柔弱!“胜”,应读平声,犹“任”、“堪”之意;“不胜”即“不堪”、“不任”、“难当”也。
其四
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
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
这首亦重在写景,是雨后的画图。“红板江桥”:苏州系水乡,水多桥多,且当时多为木板桥,涂以红色。诗人居苏州刺史任多年,在另一首诗中写到“红栏三百九十桥”,足见当时水乡木桥之多。“青酒旗”:《容斋随笔》记载,当时酒旗也叫酒帘,即张挂在酒店门口的望子,当时多以青色布制作,到宋代还有以青白两色布做酒旗的。“馆娃宫”:古代吴宫名。本吴王夫差为西施所造。在今苏州西南灵岩山上,灵岩寺即其旧址。历代诗人多写到馆娃宫,如左太冲的《吴都赋》、李太白的《西施》、唐伯虎的[江南春]《次倪元镇韵》等。白氏本诗其五亦有“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之句。“可怜”:犹可爱之意。把红板江桥青酒旗及馆娃宫前,雨歇风定之后,杨柳枝条雨后垂下的状貌描绘得如在目前。
这里选解的是第一、二、三、四首。一、二首多使用典故,重在渲染氛围和环境;三、四句重于摹写描绘,重在摹画优雅的景色。诗人运用渲染、衬托、描摹、比拟、勾勒、重叠种种修辞手法,尤其是吸收民间曲辞、民歌的平易、浅显、明白、晓畅的优点,使曲辞优美动听、琅琅上口。历代诗评、诗论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此曲(指其一)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幺’。”(《碧鸡漫志》)“刘禹锡云:‘金谷园中莺乱啼,铜驼陌上好风吹。城东桃李须叟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张祜云:‘凝碧池边敛翠眉,景阳楼下绾青丝。那胜妃子朝元阁,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风烟树九重城,夹路春阴十万营。惟向边头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诗皆仿白(指其二)。”《唐人绝句精华》云:“诗人作《柳枝词》多有寓意,非纯粹咏物也。此二首(指其三、其四)前首讥之,后首怜之也。前首(指其三)首二句写其得意之态,后二句则讥其无可贵处。后首(指其四)以红板桥比卑微者,馆娃宫比尊贵者。末二句见盛时一过,则同样无聊,故皆可怜也。于此知白居易盖有庄子‘齐物’之思想。”
唐诗人薛能有《柳枝词》五首,末篇说:“刘白苏台总近时……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也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容斋随笔》批评薛能“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且认为白诗“红板江桥……”“其风流气概,(薛能)岂能所仿佛哉!”有的评论还认为“(其四)可怜雨歇……”“无意求工,自成绝调。”(《初白庵诗评》)“(其三)咏杨柳未有不咏其舞风者,此独以风定着笔,另一种风致。只写景,不入情,情自无限。”(《唐诗摘钞》)“(其四)于闲冷处传神,情味悠然。”(《唐人万首绝句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