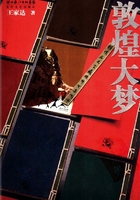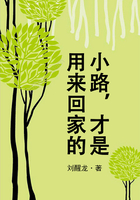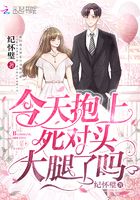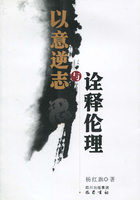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走进了位于胶东半岛的这个普通的村子。
一个人在选择某条道路之前,他(她)的脚尖其实可以指向多种方向,然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也就意味着其它种种潜在的可能与机会已经被彻底放弃。十年后的某个傍晚,我才想起,在抬脚的那一刻,自己其实就已经义无反顾了——我踏上了据称是人生伴侣的那条船,它兴致勃勃地载着懵懵懂懂的我驶向遥远而陌生的后中村。
我是被动的,带有一点点不安,以及由这种不安挟裹着的一点点惊喜,而更多的,则是由南到北的环境落差以及极度的旅途劳顿所产生的身体与心理的不适。这些让处于一九九六年腊月二十七晚上八点多钟那个时刻的我,滋生了一种近乎奴性的无所谓心态——一切都远了,淡了,在眼下,只要能给我足够的温暖与安妥的睡眠,我就权当它是后中村。
当晚,我就这么半是渴望半是盲目地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吃完一大碗热乎乎的饺子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昨夜还躺在我身边的那个男人,已经在另一间屋子里跟他的父母说话了。他们絮絮叨叨,语音很低很轻,十分渺然辽远,像夏天深夜里若隐若现的星星。穿衣,叠好绣着鸳鸯的大红色缎面被子,我像往常一样,人挪向床边,伸脚去穿拖鞋,这才发现,我的双脚完全失去了方向。
这是炕!这个炕是那么高,而且地面并不平坦。我该怎么办?如果跳下去,难免要弄出很大的声响,而作为刚进门的新媳妇,如此,未免太失风雅。
昨天是怎么上来的?这一觉睡得太沉,简直前所未有,所以我只依稀记得进门之前黑夜的黑和如刀的风。而此时,我清醒的身体却感觉到了一层薄薄的汗意,它们带着泥土被火煨透的温热,有些害羞地聚集在我的腋下、手心和脚心。
我无暇关注它们,我得找到下炕的途径。屋里几乎没有陈列什么东西,除了炕的对面挨墙放着一个高高的柜子以外,就只有紧挨着炕的一个大方桌了。它抵着墙,大部分木头的原色基本上已被酱色所覆盖,只在某些不易摩擦的部位,还依稀可见一些朱红色油漆的暗影。从炕这头望过去,大方桌上依次摆放着我和夫的洗漱用品、赭色的茶叶盒、木托盘和托盘里的瓷杯、暗红色的座式摆钟、紫色缀白花儿的塑料外壳水瓶。扫视一眼,就发现,我一意孤行所带来的洗漱用品确实非常不合适宜,它们是那么地浅薄,像故弄风姿的媒婆头上那朵俗艳的花儿。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小方桌,一样的酱红色,只是比大方桌要小六七成。它与大方桌腿靠着腿,磨磨蹭蹭的样子,仿佛是被母亲强行拽到人前的小孩。我的鞋子正挨着它的一条腿,沉默以待。
这无疑给了我启示。我抓住炕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踩过有些摇晃的小方桌,再探进我的鞋子里。就这样,我缓慢而成功地走下了炕。事实上,在我以后呆在后中村的日子里,这个小方桌一直是我日常起居的重要凭靠与依傍。
我开始舀水刷牙。也许是葫芦瓢与冰块撞击的声音惊动了他们,他们陆续走了出来,依次是我的丈夫、婆婆和公公。公公站在婆婆的背后,搓着手,咧着嘴,望着我笑;婆婆站在我丈夫的身后,也搓着手,咧着嘴,望着我笑,嘴里还叨咕着什么。和昨天晚上一样,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一脸茫然地望着她。夫翻译道:“问你昨晚睡好了没有,叫你快洗洗,好上炕吃饭。”我连忙鸡啄米似地点头。
他们俩进去了。夫却背着手,绕到我的左边,悄声说:“再不能这么晚起床了,别人家都快吃午饭了。还有,早上起床要先去问两个老人好。”我抬起一嘴的泡沫,又感到了茫然,一时竟停止了动作。
上炕上炕,吃饭吃饭。两个老人把我往炕上拽。我踟蹰地望着刚才背着手站在我身旁的那个男人。他说,让你上去就上去啊,磨蹭什么。于是我上炕。两个老人移到靠东北面的那一边,盘腿坐下,示意我坐在靠西南的炕头——紧靠着灶膛。我就依照他们的样子,盘着腿,伸直背。土炕仍然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温暖,渐渐消解了刚才还在外面洗漱时的冰凉,我觉得有一丝隐隐的惬意,像冬天坐在老家的火炉边咀嚼着刚从火灰里扒出来的烤土豆。
夫没有上炕,而是站在炕边,边吃边不时给我们倒水什么的。他每吃一样,就要介绍说,这是自家的麦子擀的面条,这是自家的花生榨的油炸的油卷子,这是妈攒的你才看见的那仅有的一只鸡在整整一个春天和夏天生下的蛋……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再度茫然了。
在后中村,我常常陷入这种茫然。可那时,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持续茫然的原因。白天,我要跟在丈夫的身后,挨家挨户去问好。有一次,在出了唤作“五叔”的院门后,我小声地问丈夫,这是什么亲戚,他说:“好像是妈的舅妈的侄子的表哥。”我疑心被厚厚的羽绒服遮住的耳朵没有听清,就请他再说一遍,夫挥挥手,说:“问那么多做什么?住在一个村子里,不是亲戚是什么?”
就把我给问住了。茫然中,我追着他的后背走着,就只记住了: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原来都是亲戚。
从此,无论走在后中村的哪条道儿上,只要遇见人,我总是要停下来,先听夫向他们问好,然后依样画葫芦:如果是长辈,就弯个腰,笑着说:“某某好。”如果是平辈,就站定,微笑着道好。在不断重复那些隐去了名字的称谓的过程中,我总是恍惚,觉得面前的他们,一律笼罩在祖先以称谓为型号而统一订制的服装里,完全隐藏了独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历史与个性。
所以,在后中村,我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能力。在十年的时间里,我总共去过四次,也迷失过四次。
其实每次的情形都差不多:出门之前,先给自己打气,悄悄地在心里说:记住去时的路,再原路返回。然后就满怀希望地开路了。走着走着,就遇到了那些亲戚,然而,在统一的“服饰”面前,我总是显得渺小而紧张,我忘了迎面而来的人到底是爷爷、叔叔还是哥哥?是三奶奶、七姑姑还是八婶婶?好不容易听明白了他(她)们称呼我什么,等我回呼过去,人家已经热情地询问我好一阵子了,可是我一句也答不上来,只能憨憨地笑,笨拙地点头——我实在听不懂后中村的语言。他们全都说得又轻又快,我常常是刚刚揣摩清楚上一句的某个单词,却又被下一句更多的方言弄胡涂了。于是,迷路总在这个时候开始——远远看见人来,我就先避过去,拐入某条方向不同的巷道。
我就这么掉进了后中村,就像一个不识水性的人突然掉进了深潭。到处都是一样的房子,无论布局、朝向、颜色、高矮、胖瘦……到处都是一样的巷道,一律泥土裸露、凹凸不平,它们在房前房后屋左屋右展示着相似的周长,像孔雀开屏……没有一棵花草树木可以为我指引方向,也没有一座打破规则的建筑物可以成为我回归的标识,只有一马平川的风不知疲倦忽东忽西地吹着。这居住着一千多号人的村子,轻易就用它强大的集中与无边的广袤包围了我,也正是这片苦寒的土地,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用它的平坦与赤裸挟裹了我……我想起曾经路过的枣庄,想起那部历史题材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张惶失措,而应该弯下腰,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智慧的人民致敬。
我还想起故乡的那些高山与流水。虽然它们也曾经把鬼子们拉进了迷宫,但它们本身的力量显得过于强大,以至于掩盖了人类智慧的发挥,或者说,它们用自己的力量奉养了人类的惰性——我的那些乡亲们,守着仅够解决温饱的土地,永远知足而常乐。而在后中村,我看不到葱郁的山、成片的草和流淌的河,我看到的是人。他们的脸一律黑红着,那是被尖锐的风吹露的红血丝;在冬天,他们从不睡懒觉,他们遵守比城里人还要规律的作息时间:七点早餐十二点午饭十八时晚餐;他们喜欢顶着风,端着黑红的脸庞微笑着穿过街巷,或者挑着鸡蛋、苹果、花生去赶集,或者到田间地头去察看庄稼们的长势;他们喜欢把房子弄成一样的格局,说是节约土地;喜欢执着过路人的手往自家院子里拽,说:上炕暖和暖和……
是的,人类原本是纯洁而健康的,原本具有积极而友爱的灵魂。在陷于迷宫般的后中村,我的思想总是很复杂,我觉得自己总是被某种东西深深地诱惑着。所以,每一次,我都不愿意打电话或者问路,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回去的路。
其中有三次,我循着人声,闯进了它的集市里。
人头攒动,声音像物品一样极大地丰富着,冷洌的空气中充涨着沸水般的气息。这是每五天后中村大集的日子。方圆三十公里、附近十多个村子的人都汇集过来了。汇集过来的还有来自这些村子之外的鱼肉蛋禽、蔬菜水果、油盐酱醋、衣帽鞋袜、锅碗瓢盆……五彩缤纷,应有尽有,像鱼满江粮满仓,伸手一抓,都是沉甸甸的。这里不分类,不分工,不专业,只在二百多平米的院坝里一溜一溜地摆上东西,吃的挨着用的,喝的傍着穿的……唯独玫红的纸包着的一卷一卷儿的鞭炮、一幅幅红底黑字的对联兴头头地摆在院坝的四个角头。
卖鞭炮的老人好像是为了证明货真价实,又好像是不甘寂寞,每隔一会儿就要拿出一小串鞭鸣放鸣放,把一些乱窜的孩子都笼络在自己的身边。大人们也就乐得自在,一门心思在旁边瞧着对联,笑着左指右点。卖对联的也心领神会,人家指到哪儿,是要还是不要,他一瞅一个准儿,随即把买家儿要的对联挑出来,卷起,再用橡皮筋一卷一卷扎好。我常常就看痴了,觉得买对联的和卖对联的简直就是云影与波心,在闹腾腾的集市里,尤其是在鞭炮声里,即使摒弃了一切语言,他们彼此的心思却仍然一丝一缕都映在对方的心里。
我也忍不住要买东西了。第一次,买了一双布鞋——鞋帮是黑色灯心绒,脚背处带一个扣眼儿,塑料底,超市里九块钱一双的那种。
我问蹲在地上整理鞋摊的大嫂:“这鞋怎么卖?”她停下忙碌的动作,仰起头来,立刻就有一绺头发被风吹在了脸上。
麻利地一扒拉,头发就藏在了大红的围巾里,然后她眯缝着双眼,反问我:“啥?”
我只好搛起一双布鞋,比划着说:“这个,怎么卖?”她懂了,伸出四个手指头,说:“四元。”我惊了一下,心里叹道:真便宜啊!可是,出于习惯,嘴里却说:“能不能少一点儿?”她盯着我,满脸的惊讶。
突然,旁边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强婶,你咋一个人在这里啊?这里不还价的。”扭头一看,原来是邻村五哥的儿子,也是从外地回老家过年的,昨天我们还打过招呼。
原来如此。我红着脸付了钱,就仓皇地出了院坝,被那个年龄比我大一截的“侄子”护送回了家。
后来的两次,我就不再还价。于是,一切变得干净利落,成交的过程全都简单得只剩下最后定音的一锤。不还价真好,它使得买东西的人心平气和,卖东西的人心定气闲,更让我快意的是,时间就像春天的青草,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我缩着脖子,双手捂在裤兜里,东逛逛西瞅瞅,看着那些熙来攘往的人在冰冷的空气中热乎乎地流淌着,像热气蒸腾的河;我走在大红大绿大黑大紫土里土气的衣服们中间,或者穿过鸡喊鸭叫的阵群,忽而感动,忽而感伤,有时觉得自己高于这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低于这一切……总之,我像个司令,在五颜六色的物品中逡巡,仿佛有所思,仿佛有所感,但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个悠哉游哉的光杆司令很快就会被发现,再然后,就会被不由分说地完璧归赵。
在后中村,我就像一个走失的孩子,总是反复而被动地幸福着被找回。
第四次走回家,终于比较完全地依靠了一次自己。
正月初二下午四点多,久阴无雪的天终于浮现出穿着一身红边儿灰布裙的云彩,我一时兴起,就信步走向后中村的街道。走着走着,云彩变淡了,逐渐与苍灰的天融成了一体,太阳也出来了,惺忪,灰白,无精打采。环顾四周,所有的院门都贴着大红的春联,但是,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人声,一排排房子也没有投下半点儿阴影,像沉默的森林。我掉转头,却不知该走向哪个方向。
我在内心开始和后中村抗拒。我站着不动,竭力搜索记忆之库:比如刚才走过的那些春联,在它们喜庆的横竖撇捺里,又蕴藉着哪些微小的区别足以标记我的行迹呢?
然而,鞭炮陡然响了起来,是那种彻天彻地的响。响声从天空中和脚底下向我传来,不由分说主宰了我的脚步。
当我循着响声拐过一家屋角时,我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院坝,类似我老家七十年代生产队仓房的院场。人群肃穆,只有鞭炮在响。鞭炮们都被绑在竹竿的顶部,长长地垂挂下来,而且,在每一根竹竿的中央,全都绑着一块红布。竹竿由每一家的年长者把持着,一律竖立着排队等候。当前一家鞭炮的响声接近尾声时,后一家的长者立即将竹竿伸向院坝,指向西方,然后,由这家的壮年男丁点燃鞭炮。我看到我年迈的公公执着竹竿,看到二哥用火柴点燃了鞭炮……鞭炮之声几无重复,但也从不间断。
所有的女人们全都围在四周,排列成一个圆圈。从我站到婆婆背后的那时起,鞭炮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宣告结束。这时,一个老者走出人群,站在厚厚的鞭炮碎屑上,向着东方的人群喊了一句什么,就见圆圈忽地断开,女人们走到各家男丁的阵群之后。老者转过身,面朝西方跪了下去,所有的人也都跟着跪了下去,磕头,然后站起来,再跪。如此,反复三次。我看见我七十二岁的婆婆缓慢地跪下,双手撑向大地,再缓慢地向着太阳西沉的方向,叩首。
我看见整个后中村的人虔诚的头颅和躬成虾状的后背……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样的送年仪式,承载着怎样的心情?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背景?苍天在上,大地在下,太阳在上,泥土在下,感谢,感谢这一切赐予万物的生长!后中村的男女老少们,端着黑红的脸庞又走过了一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年要走了,得好好送上一程,给天地跪下吧,给时间跪下吧,就以人类所能够表达的方式!
人人的裤腿沾满了灰尘,但没有人掸掉。太阳还剩下一道隐约的白弧,像半开的眼。天色暗了下来,黑夜即将为明天铺开褥子。我跟在公婆和哥哥们以及夫的身后,走进后中村自家的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