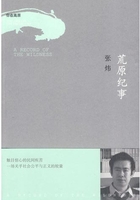“坐火车来的呀。我跟双周一个老头,他闺女在解放大楼工作,给我说,咱去西安玩吧。去就去,谁不敢吗?俺俩就来了。咱庄上还没有人来过西安哩,想叫你爷也来,他说他老了走不动了,叫我替他来看看西安的景致。家里吃食堂了,人民公社一年多,人都吃不饱,你看看我饿成啥了。”
不管怎么说,爹这身自我感觉很好的大袍子是不能再穿了。他翻自己的箱子,所有的衣裳对爹来说都小,同一个单身楼里的山东人王大个拿来了自己的一身工作服:“叫大叔先穿上。”
章柿跑去撕了布料,拿着那个大袍子,叫裁缝量了尺寸,加快做一身衣服。写申请找厂领导签字,爹被免费安排在招待所住下。有关系好的职工买了水果、点心,拿着自己省出来的粮票来看望章守信。章守信的做派还是抱拳、鞠躬,张口闭口叫年轻人王贤侄、李兄弟,叫女职工刘大姐,引得大家开心地笑,他也不管,仍然我行我素。
章柿少有地幸福,因为他看到爹对他的生活如此满意。他上班的时候,爹就在生活区自己转转,还交了几个老年朋友。有时候他还没下班,爹就拿着饭票、饭盒去食堂把饭打回来。章守信觉得这个食堂比家里的食堂好多了,这里能吃饱。几天后,他悄悄告诉章柿,同样是二两饭票,打米饭比买一个馍划算,一个馍吃了不饱二两米饭就能吃饱。从那以后,他就顿顿打米饭。
星期天,章柿带着爹去城里转,去革命公园,去钟楼,去解放大楼。爹也不舍得买啥,只是新奇地看呀看呀,见啥都稀奇。还找到了双周闺女和他爹,两家走动了几回。双周闺女找领导批了条子,叫他们买了优惠价的布料,给奶奶、娘、胡爱花一人买一件上衣料子,给章楝买了双网球鞋。几个月存的钱花完了,可他很高兴,人挣钱干啥?就是给亲人花的。过一个月就又有了,这就是公家人的好处。
章守信提出,要去王宝钏的寒窑看看,马上有单身汉说:“那有啥好看的?俺家就是那的,一片麦地,一个破窑,远得很,不通车,在大雁塔东还有好几里。我每个星期回去要骑车两三个钟头。”
“是哩,你娘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可总是在戏里听说寒窑,破就破吧,看看就知是咋回事了,也好回去给庄上的人喷喷。”
“好,这个星期天我向车间借个三轮车带着你去。”
“要啥三轮车,不是大雁塔东几里地吗?咱从大雁塔下车,上上大雁塔,走去就中了。几里路算个啥,你娘当年给你送馍走了六十八里,何况咱这大脚哩。”
星期天,爷俩从东郊出发,先坐车到大雁塔,掏四分钱买了两张票,上了塔。在塔顶,章柿指着东北方向给爹说:“那一大片树林里就是我们的厂房。”
出了慈恩寺,两人一路向东,走了半个钟头,来到那座破土堆前。也确实没啥好看的,真的像季瓷所说,看景不如听景。
沿着快要泛黄的麦田边小路,两人往回走着。
“快割麦了,我得回家去了。招待所只准住一个月,天热了,跟你挤一张床上,可不中。这一个月我在你这都吃胖了,一胖,我也就显白了,再穿着这身衣裳回去,村里人可能都不认得我了。”
能听出来,爹的口气是安慰和幸福的,还有那么一点自豪,好像他已经看到村里人羡慕的目光。他的心里也有一些话想说,他总觉着有些话他永远说不出口。他和爹隔着什么,这是一层不能说的东西。爹从没有打过他。爹那么赖的脾气,打过娘,打过槐,打过楝,在集上跟人家打过架,一蹦多高在街里骂过人,可就是没有打过他,不但没打过他,好像还总是有点额外的小心。他依稀记得小的时候,节高叫他带肚儿,爹大发雷霆,去节高家门口蹦着骂了,可回来对他还是那么好。他偷眼看了爹一下,啊,没有一点像的地方,爹高大,壮实,深眼窝,大眼睛,双眼皮,而我,跟他太不像了。
粗暴的性急的爹,内心里对我有着怎样温存的想法啊。
二人只管边走边说话,对面来了人也没注意。那人灰头土脸,拉了个架子车,低头走路。就在错开身子的一瞬间,那人又回过头来,一声惊呼,扔了架子车,扑过来一把抓住了章守信。
“守信!我没认错吧?你是守信,没错没错,是你,爷们呀……”那人说着,哭了起来。
二人惊呆在路上,这个地方怎能有人认出咱哩,还一下叫出名字来。细看那人,头发乱蓬蓬,脸上流着泪,因为太激动,脸扭曲着,那眼睛,啊,左眼不好。
“有福叔哇!”章守信也大叫一声,两个人架着对方的胳膊,形成一个圆形,望着对方的脸,百感交集,在路当间先是正着转,又是反着转。天哪,真的是你呀,再转了一圈,正像是戏台上故人相遇一般。都太激动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泪眼相望。
“叔哇,十来年了,到处都没你的信儿,你日子咋样啊?也不想回去看看?”
章有福长叹一声:“咋不想回,做梦都想哩,你看看我这一身打扮,就知我日子咋样了。”
当年,桃花在他耳根说出那句话,他恼得不行,夜里躺床上睡不着:我还在这河西章待着干啥呀,叫人不拿正眼看咱。他“呼”地从床上起来,收拾仅有的两件破衣裳,一路向东,过了颍河,他成了离开家的人。他无牵无挂,走到哪儿是哪儿,他有力气,不愁没饭吃。走一路,给人干一路活,不但管住肚子,还挣了几个麻钱。最后,他留在一个大财东的家里,先是给他家种地,后又给他家看院子,再是给他家管长工短工。章有福本是个聪明人,除了一只眼看不见,心却透亮,或者因为一只眼看不见,心更明亮,比一般人多那么一窍。他不断得到大财东信任,同样的事叫他去办,总比别人想得周到一点,做得好一点细一点,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人就听着舒坦。几年后,他当上了大财东家里的一把,也就是说大财东把家里一切杂事交与他料理,要谁不要谁,给谁吃稠的给谁喝稀的他章有福一人说了算。他把几百亩地经管着,也算是天助,接手头一年比哪年打粮食都多。大财东将地里收的麦子给了他十分之一,他卖了粮食置了一块小小的宅子,说了个有点瘸的媳妇,在大财东家的边上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当然他也没少克扣长工短工们。有些人,他对上头有多少温柔就对下头有多少残酷,越温柔就越残酷,这是一个定理,他只需对一个人负责,他只需一个人认定他是好人就中。这使得解放那年当政府抓了大财东时,当地农民不答应,他们一致认为大财东是个好人,没有亏待过他们,该杀的是这个外乡独眼儿。那时他正在外替大财东办事,还没有走到家,见他那瘸腿女人从对面跑来,塞给他一个小包,叫他快跑,千万不能回家:“这里面有几件衣裳,还有钱,快走吧,回去就没命了,那些人说把你拉住就要枪毙。”
“那你咋办?你跟我跑不?”
“我肚子里有了,不想跑了,你跑吧,到哪儿去躲躲,过两年风声轻了你就回来。我先住回娘家,我是本地人,他们不会咋样我的,你可一定得回来找我。”
“可这儿还有给掌柜的钱哩,我是去替他要账去了。”
“唉,他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了,还要啥账。”
“那不中,你拿回去,给他。世道一会儿变一个样,他要是过两天又中了,那咱的脸往哪儿放。”他把账目、钱,一五一十给媳妇交代清楚,这才转身跑了。
先是跑到洛阳,在那儿待了半个月,钱快花完了,亲眼见到街上拉着地主恶霸游街,游完当场枪毙。当枪声“砰”的一声响起,他的魂差点没吓飞。
听说陕西的活好找,西安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钱,弯弯腰就能拾一张。他搭上火车,一路来到西安,很低的价钱买来人家不要的架子车,自己拾掇得能走了,在郊区给人打零工,拉砖拉煤拉柴火,啥活都干过。他这才知道,天下到处都一样,那就是守信家说的那句话,钱难挣,屎难吃。眼看一年又一年过去,他没有攒下钱,只攒了越来越多的思念,常常在夜里梦到河西章,梦到河水溢出来流得满街都是,梦见龙王庙的香火飘得满村子烟气,梦见桃花,梦见章四海。
梦醒来的时候,他听到的不是柔软的河水般的乡音而是硬邦邦的西安话,心里那个忧愁滋味,他一生都记着。后来人家再叫他出门,他说,哪都不去,他只守着河西章,老死在河西章。最难受的是他心里的思念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陕西人好是好,可说话石头般坚硬,落下来能把人脚面砸疼,他们就是给你吃食的时候,也不会说句和气话,只命令般地说,你吃你的,你吃你的,哪像俺老家的人,不咋哩,用好听话先淹住了你泡软了你。自己也四十多的人了,在外面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还不如回家算了,找到自己媳妇,领回河西章,过自己的日子。都十年了,我就不信那些人还记着要枪毙我哩,就算要枪毙,我也得埋到河西章,总比老死到外面强吧。一个人的日子,再有个病呀灾呀的,就更难受。可是混成这样,身上凑来凑去只有打一张车票的钱,我这么要强的人,出来十几年,总不能空着手回河西章吧。
“回去吧,叔,没事了,好多当时跑出来的人都回去了。河西尹不是还有一个当过商桥镇镇长的,那时说要枪毙,也吓跑了,去年也回去了,一点事没有。”
“真的?”
“真的,爷,政策变了,去年毛主席发布特赦令,好多人从监狱里出来了,何况你这,更没事了。”章柿说。
“回去吧,叔,我过几天要回哩,叫你孙子给咱俩一人买张车票。他现在在东郊天河厂上班,你看,这衣裳是他撕料子给我做的。还有双周那老头,咱仨一起,回家吧。”
回家吧!回家吧!再也没有比回家更幸福的事了。章有福拿了章柿给他写的天河厂地址,拉起破架子车,回到自己住的村子收拾东西去了。
来时俩老头,回去仨老头。
章有福下火车后没有跟他俩一起往西走,他去东边找他的瘸子媳妇和孩子。
章续强一听说叔要回来,花了大半天时间把他那小破屋收拾了一下。桃花也不再计较从前的不愉快,尤其听说他去东边接他媳妇和闺女,她这当嫂的紧赶慢赶,东挪西凑,给缝出一床铺盖来。
章有福一家三口迟迟疑疑地出现在村头,好多人上前来迎住了,这个说:“有福你个兔孙跑哪儿去了,连个信儿都没有,你再回来晚点我这辈子就见不着你了。”那个说:“有福叔,走了有十来年了吧,咦,头发都白了,这要是在旁的地方,我可不敢认你。”有个漂亮人物说:“有福爷你还认得我不?我是节高,你走的时候,我才十来岁。”章有福使袖口潦草地擦擦泪,拉住闺女的手,给她指着面前的人,这个该叫叔,那个该叫哥,这个嘛,别看他那么大的个子,还得叫你姑姑哩,说得章节高龇牙一笑,真的张口叫了声“姑姑”。来到自己的那个破屋,一看到里面有床有铺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骨堆到房门口,捧住头,“嘿嘿呀呀”地流泪。想当年他离开的那天晚上,对这个村子是多么恨啊,竟然发狠说他再不回来了。桃花已不再年轻,风采尽失,她晃着松松垮垮的腰身来到院子里,拉住小闺女的手,对那瘸子媳妇说:“刚回来,有些东西得一点点置办,破家值万贯,少双筷子都不中,这两天就先到前院吃饭吧。”马上有热心人对瘸子媳妇说:“这是恁嫂。”
晚上,扯成长条条躺在床上,章有福立即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