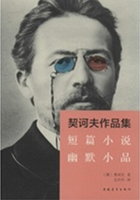“惜萱对你这么好都是我的功劳。”
“啊呸呸,你少在她面前揭我的短我就该烧高香了。”
呜……我从来不做坏事,为什么厄运连连?
面对进来的惜萱,我简直想扑进她怀里抱头痛哭,可是惜萱一句话令我不得不憋住泪。
“姑娘,算起来已经过了一日了,裘府再找不到人,怕是要拿陆皓天开刀,咱们现在去救他吗?”
对呀,我倒把那个小鬼给忘了。
救吗?当然,怎可能不去救,不过眼下关着陆皓南的地方肯定加紧把守,或者这些被当成禁宠的男子已经被转移到了别处。
然而单凭听那些百姓的言辞,裘老爷的双手已不知沾了多少条性命,依旧逍摇至今。仗的就是儿子身为一方大官。
不过,眼下正巧有一个人能将一切黑暗尽数扫平,当然,老娘不会蠢得去找他,国是他的国,朝庭是他的朝庭,清理门户自然是他自个儿的事。
对,是他的事,不过身旁皇帝日理万机,也许有很多事不知道。那么我不介意提醒一下,好歹遂君我骨子里也流着皇室的血液,哪怕改朝换代,实在也无法做到视百姓疾苦为无物。
我冲他们勾勾手:“反正陆皓天是关在柴房里。我给你画张地图,你先去这里看看陆皓南在不在,若是在的话,把人救走在说。至于后面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
随后我大大方方跑到隔壁,用力敲了敲门。纵然是隔着厚厚的门板,亦能感觉得到里头流溢出来的严谨的气息。
不一会儿,门开了,是一个面无表的侍卫开的门,他的脸冷的就像盛夏天里面前搁了一块降温的大冰块一样的感觉,我有点后悔冒然来了,面对这么个冰柱似的哥们,我虽有想溜的心却没溜的胆儿,按常理来说只要我脚步稍微往后退分毫,立马就会被当成踩点的刺客,然后一剑毙命。
眼下我只能硬着头皮站在那里,小心翼翼将视线越过他的肩侧,对面夜离歌端坐书桌前,桌上摆着厚厚两摞子奏折,少说有十个高手守在他四方严阵以待。
夜离歌见来的是我,眼前一亮,快速放下笔向我走来。
“遂君,朕想不到你会过来。”
矮油?当着侍卫的面都用上“朕”了,哼!看着架势还想牵老娘的手,呸呸!色鬼,老娘来办正事的。
我摆起正色来,咳了一声,板起脸色:“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你听不听?”老娘没蠢得示意这货让侍卫们走开。
一来这个暗示似乎像极了夫妻俩说悄悄话,我是良家妇女,不想让这货产生误会,更不想给小恨戴绿帽子。
二来嘛,能跟在夜离歌近身保护的侍卫都是高手之中高高手,不但嘴巴严密而且武艺高强,万一这货在此期间出了什么事,天大的冤枉都得由遂君我来背,到时候哪怕长满身的嘴都说不清。
可怜我好不容易遇到心爱的小恨,还没来得及嫁出去,就要死翘翘于一个莫虚有的罪名,何其不冤?
他眼神一闪,对于我显然的疏离掠去几抹失落,却很快以笑意冲淡:“好,什么重要的事,朕听着呢。”
那似笑非笑的德性,仿佛笃定老娘即将陈述一个有趣的笑话。这点似乎跟小恨一模一样?为什么这帮死男人都把老娘当成傻子来看?
唯独小饼,从没有这样过,但平时都是我拿他当傻子。
“本城县令姓裘你知道不知道?我听说他仗着朝庭命官的身份不仅欺压百姓,还欺上瞒下,坦护他那个身犯数条人命的亲爹。”深吸一口气,我有点痛恨为毛来的这么急,没把话想好?瞄见夜离歌已经悠然抱臂斜靠,等着我接下去说呢,老娘只得临场发挥,硬着头皮上:“你是要问我他爹是不是真犯罪是吧?我告诉你,明儿一早你到楼下吃早点,一个桌上挤八个人,有五个人聊的都是这个事。他爹经常买小倌,把人弄死就直接扔到乱坟岗去,没人敢去告发他。你身为皇帝也该管一管吧。”
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反正没几句话说得我嗓门都冒烟了。可那货不急不燥,竟然随手拿起一本奏折翻了起来。
你个老母的,我狠狠攥拳头:“喂,说完了我走了。”
“遂君。”他唤住我,将手中的奏折递过来:“这是扬州巡府呈上的奏折,你看一看。”
“不看。”你老母的,看了老娘就死定了。这点自觉我还是有的。
他大爷也不恼,居然好脾气的跟我将奏折收了起来,再次面向我时眯起了眼睛:“你说的朕都已经知道了,不过依朕看来,你似乎并非专门为此事而来。”
你老母的,毒。
我定定神,刻意扬起骄傲的脑袋:“矮!你的话我听不懂。反正要说的都说了。信不信随你。”
没等他同意,我撒腿跑回自已所屋子里,“咚!”锁紧门,背后紧紧靠着门板,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里面惜萱紧张又不解的看着我。
我冲她摆摆手,想说话却发现嗓子在冒烟了,于是奔到桌旁大口灌了水下肚子里去,才抹了把嘴巴:“没有后顾之忧了。咦?洛朝阳呢?”
“他已经去裘府了。姑娘,您说没有‘后顾之忧’是什么意思?”
“就是洛朝阳把人救出来后,就没我们的事了,有人会办了姓裘的一家。”应该会吧,连三品巡府都上了折子,当皇帝的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贪官污劣,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要不想步我父皇的后尘,就尽管放手任姓裘的继续鱼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