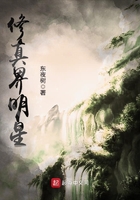安平郡主走到皇甫少华面前,立定,问话:“你家公子安排你在厢房里,是叫你偷听还是偷看?”
皇甫少华低头回话:“郡主说笑了。小的只是一个下人,方才在里面收拾东西,却闻说郡主到来,慌忙之间,不敢出来,却致郡主误会,小的自是该死。”
安平郡主绕着皇甫少华转了两圈,点头赞许:“不错不错,说话竟然滴水不漏。郦君玉的心腹,果然不同凡响。郦君玉叫你偷听的目的是什么?叫你给他做军师?他自己一肚子诡计了,还要什么军师?还是怕来客不善,要你出来帮忙?你懂得武艺?”
皇甫少华一噎。孟丽君拂袖而起:“郡主娘娘,我敬你是客,因此以礼相待。却原来是来我家欺负一个下人!郡主娘娘大驾光临,预先并无圣旨通传,学生一介草民,那里知道来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郡主娘娘?又如何预先安排人员,对付郡主娘娘?此话先休提。却不知郡主娘娘来此,是何公干?学生本非郡主家下人,亦非在职官员,应该无有接待郡主娘娘、受郡主娘娘欺负的职责吧?既然如此,请郡主娘娘离开此处,学生自有事情,无暇接待,请郡主娘娘见谅。”
安平郡主见郦君玉脸色已经气白了,也知道自己方才说话,已经将这个臭书生要气疯了。想起铁穆吩咐,不免也心下忐忑。但是又不愿就此道歉,便直僵僵站着,说不出话来。却不知此时那个臭书生,心下也是忐忑不安,正是所谓色厉内荏。
孟丽君深知这个道理——越是心虚的时候,越是要表现地强硬。何况现在铁穆派安平千里迢迢来,必然有事寻找自己。自己作出一幅恼怒模样,这郡主娘娘,必然不敢轻易得罪自己。那反而安全了。
王长虹见此情景,知道该自己说话了,便急忙说道:“郡主先息怒,郦先生也先将心放舒缓些。末将说句实在话,我们此来,自不希望行踪落人眼目。这小厮人在厢房里,我们想要查问两句,也是分所应当。而郦先生事先并不知我等到来,未曾先安排好下人,才有这一场误会,先生不要生气可好?郡主您也不要生气可好?”转头呵斥皇甫少华:“还不下去!”
皇甫少华松了口气,急忙下去。
见王长虹如此软语央求,安平方把脸色松下来,说道:“郦先生自己做这等事情,还责怪起我来!”又坐了回去。郦君玉见安平并无从皇甫少华面目上看出破绽,也松了口气,目的已达,也无心再与这娇娇女结仇,赔笑道:“学生方才不曾细想。郡主查问,本是应当。但是郡主方才说话,却直指学生居心叵测,学生未免委屈,说话便急了,得罪了郡主。郡主大人大量,想来不会与学生这不懂礼仪的人计较。”
安平见郦君玉服软,这才心满意足。说道:“我们说事情吧。”眼睛转向王长虹。
王长虹说道:“殿下派我等寻找郦先生,时日已久。今年四月,先生不告而别。想起先生曾经说过,老家在明州,李玉飞便曾秘密到明州寻访。但是我们虽然找到姓郦人家,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先生。”
孟丽君知道那时自己还在湖广严妈妈家中养伤,不由心里好笑。却听王长虹继续说道:“想先生所说多半是谎言,只道先生是世外之人,自不愿纠缠于俗务当中,殿下无可奈何,也只好罢了。我等想起先生说话口音,似乎是云南之人,也曾到云南秘密访问,却也没有踪迹。直到今年九月,浙江省乡试发榜,先生竟然一举成名,高中解元,才知道先生的真正身份。殿下当即没有迟疑,立即派李玉飞去明州寻找先生。没有想到,追到明州,竟然扑了个空,先生竟然回到湖广祭祖。李玉飞赶回临安,与殿下说知此事。殿下事情紧急,不能多加耽搁,于是便派郡主男装出来传信给我,要我千万要找到先生。郡主自临安出发赶到这里,早起晚歇,日夜兼程,也不过只花了七日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