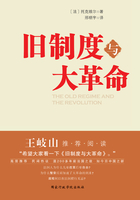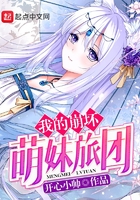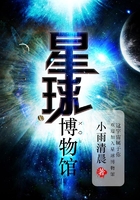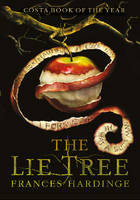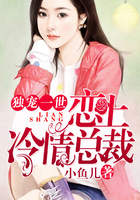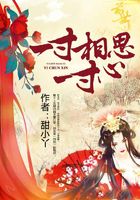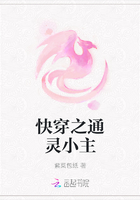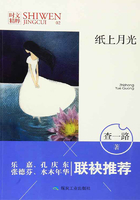《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回忆
哈雷特·阿班 著 杨植峰 译
哈雷特·阿班1926年来中国,从事新闻采访与报纸编辑,1929年起任《纽约时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后调往上海,任中国首席记者,凡十二年,于1941年离任回国。1944年出版《民国采访战》一书,回忆了自己在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者生涯。该书的中译本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刊出的是该书的节选,文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接掌《英文导报》
8月(1926年——译者)底,我终于迎来了转机。我收到北京《英文导报》东主葛洛甫·克拉克的信,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北京,替他担任报纸的总编。他提出的薪水是每月六百大洋。
我到处打听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大家却避而不谈,甚为奇怪。有人说,报纸“还可以”——但又说,克拉克曾经是个教授,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东应该都是传教组织,有些还是中国人。克拉克本人常被称为“空头激进派”。
我们之间有了书信往返后,克拉克先生写道,他要找的人,要在北京《英文导报》“至少呆到1927年中”。我最后回信谨慎地说,我会在9月中旬自费北上,先开始工作。六周之内,给他个明确说法,看能不能呆到1927年中。我指出,这么做的话,即使我决定不在北京呆那么久,他也有足够时间在年底前另觅人替代。
大家白纸黑字同意这些条件后,我终于在四十二岁生日那天,乘船从上海赴天津。几个月后,我离开的地方成了全球的新闻中心,也成了紧张态势的发源地。但是,我跑到北京来,看似避重就轻,却在后来几年,多方证明我的这一选择有无上价值。
我与北京《英文导报》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6月。在我的整个新闻从业史上,这段工作是最不寻常的。期间,我对远东政治生活的认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我至今仍在庆幸,与该报分手,居然没闹到严重损害我的职业声誉和人品的地步,实在难得。
该报的主持人葛洛甫·克拉克是个友善的人。他体格肥壮,一只眼略有斜视,态度有时客气得过了头。但不知怎的,他总让人觉得不自在,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
我抵达那天,他请我去他家共进晚餐,我也有幸认识了克拉克太太和两个孩子。席间,克拉克侃侃而谈,讲到外国人在北京要找到理想住所殊属不易,接着,便提出要把他的房子分出一部分租给我。给我的部分包括客厅、餐厅、浴室、储藏室和一间大卧室,自带一进院子,与克拉克的那部分住所是隔开的。他还提议,可以让他的几个仆人专门过来替我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他要求的租金相当便宜,我就当场答应了下来。我说,我现在只答应先住六个星期,然后才决定是否替报社干下去。
克拉克的寓所在城墙内,位于京城的最东边,胡同的名字大概是“翰林”的意思。北京《英文导报》的印刷厂则靠近市中心,在煤渣胡同的一个小小四合院里,房间和院子都用青石板铺地。排版是靠中国排字工手工完成的,而除了工头外,工人们对英文都是一字不识,令我称奇。
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两百份。印厂的工资开销可以靠接外活来负担。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已经晚了一个月。头版一般是合众社的电讯,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或日本或俄国的各种组织资助的。我查看了档案,发现除了从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几乎没有社论。本地新闻也极少,因为报纸没有自己的记者。
见这种经营方式实在有违常规,我便萌生了退意,决定六个星期一到,就知会克拉克,不准备住满半年,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直到他找到我的继任人。后来,我又发现,克拉克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大洋,但欠薪已有半年了。这一发现,更坚定了我离去的决心。
我履新三个星期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英文导报》的广告经理斯坦立·佛雷耳一头冲进我的办公室,样子极度的惊惶。佛雷耳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克拉克下星期三要回美国了,你知道吗?”
我愣住了。
“那谁来坐我的位置?”我问。
“你不知道这事?”
“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你是怎么知道的?”
“出去拉广告时发现的,”佛雷耳道,“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发现他给自己、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买了去芝加哥的船票。在一家裁缝店,我又发现他下了紧急订单,要做五套西装和一件大衣。在我们报纸登广告的鞋匠也说,克拉克在他那儿定做了六双新鞋,最晚必须在星期二交货。从公司账簿上可以查到,克拉克已经把欠他的薪水全领了。”
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来接替我的位置。
由于星期一不出报,谈话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打到一半时,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大声对我说,有要事与我商讨,让我请客人离开。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很识相,各自告辞走了。我则做好了准备,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
他开门见山道:“告诉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
我没好气地回道:“一点都不意外,早就听说了,知道你买了船票、西装,还做了新鞋。”
“怎么会……”他刚要接口,我举手阻止了他。
“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
“怎么啦,当然是你了。”
“不是我,”我强调。“你全都搞错了。”
接下那半小时,我回想起来便打寒颤,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心里满是厌恶。克拉克先是说,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没有搞懂”,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必须即刻就启程。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才说,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开刀,才能保住她的视力。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
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缠硬磨,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呆到1927年春。作为交换,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伙食也自理。
出乎意料的是,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导报》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在他缺席期间,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就可辞职。
星期一,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知道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12点半时,克拉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祝我一切好运,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
五分钟后,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只包含新闻部分”,并通知我说,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撰写。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
阅毕,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跑过院子,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对他说,我一收拾完东西,马上就走。他一听,再次向我求起了情,而且哭开了。于是我一错再错,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让步前,与他重签了份协议,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协议说,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
初识顾维钧
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这段时间里,中国要事频仍,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报上出声,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
1926年秋的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而北京的政权,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各国外交官上任时,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却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1926年初,北京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我9月抵京时,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则向西退入了四川省。
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年初,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
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部长,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有围墙环绕,广场敞阔。我到时,见怒气冲冲的部长已经在等我。
“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尖声问,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导报》塞到我鼻子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
“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我反问,怒火绝不稍逊于他。
顾博士继续尖声道:“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还回美国去了,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
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
于是,我告诉顾,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而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他听了,才稍微平静,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但我们交谈良久后,反而变得友好了。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他在当时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我在《英文导报》任职的余下时间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下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要知道,他可是那个政权的顶梁柱之一。
与司徒雷登们的分歧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由于那时的国民党人强烈亲共,鼓动排外,对外国人,尤其是教会及传教士屡施暴行,终于刺痛了美国、英国和其他缔约国。各国开始仓促部署保护行动。开进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军队已超过了两万人,路上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来。
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在城里大肆劫掠,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掠和焚毁。最后,一群美国和欧洲难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驻地美孚山。在此,他们又遭到攻击。长江上的美英两国军舰于是赶来救援,舰炮齐射,形成一个半圆的火力保护圈,难民趁机从高大的城墙上顺绳而下,逃往江边,由登陆部队接应,用小汽艇送到军舰上。
那时,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两艘日本军舰,听到交火的声音后,火速赶来,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对中方的战斗,但抵达现场时,炮击已告结束。两名日本舰长因为来迟而懊悔不迭,居然为此哭开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因此,我自然要浓墨重彩处理这个故事,遂在北京《英文导报》头版使用了八栏的大标题,导语则用了双栏粗体字。
第二天,好戏上场了。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见里面赫然坐着北京《英文导报》的三位董事:教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半教会性质的北京语言学院校长W.B.彼得斯博士。
三个人由司徒雷登博士为发言人,所以他先开腔道:“我们来的目的,是抗议你把《英文导报》搞成一份不可饶恕的耸人听闻的报纸。你把南京事件的新闻放在了头版,还用了危言耸听的大标题,你难辞其咎。如果这件事非报道不可,那也应该把它放在内页里,只用单栏的标题就够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们又把抗议内容重复一遍后,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论,就好比试着与童子说理。我告诉他们,这条新闻是头等重要的。自二十六年前义和团叛乱以来,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向中国人开火,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要占据头版位置。我指出,美国及欧洲的所有报纸,肯定会把轰炸南京的新闻置于当天最显著的位置。
他们的依据则是,本次事件必将损害中国人对美欧人士的亲善之情,从而损害他们各自的事业,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因此,这类新闻必须封杀,或小而化之。
最后,双方搞得剑拔弩张,于是我拿出与克拉克的书面协议,上面言之凿凿,授权我全面掌控办报方针及新闻版面。我对访客们直言,如果不收回抗议,二十四小时一过,我就拂袖而去。而如果他们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议,那我就当场辞职。
事后,我与这三位先生便再未谋面。直到来年开春,我才因为一件急事,又找了他们三人一次。由于此事可能危及报纸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所以必须找他们面商。
这场危机与北京《英文导报》(及该报代理总编)是息息相关的。事情的缘起是1927年春对俄国大使馆的一次突袭。那时,张作霖大帅已从满洲移往北京,京津一带尽归他掌控。他的盟友是臭名昭著、苦力出身的张宗昌,张占据了人口三千万的山东省。
而蒋介石则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坐拥长江下游的人力与财源,正在同中国共产党闹分裂。这种背景下,北京使馆区内的苏联使馆开始招来列强及中国当局的怀疑,被认为窝藏着大量中共党员,并到处策划阴谋,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各缔约国。
按当时的规定,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人,乃至各类中国军警人员,一概不得进入使馆区的大门。中方政要来访时,保镖可以随行,但必须临时解除武装。因此,各缔约国的大使及公使们自然无法自己组织武装力量,对受到怀疑的苏联使馆实行突袭。于是,他们便默许张作霖手下的军人进入使馆区,突袭了苏联使馆。而照理,该使馆是享有不可侵犯的外交豁免权的。
突袭让苏联使馆人员及藏匿其中的中共党人措手不及。尽管苏联人试图销毁卷宗,当局依然查获了大量文件。苏联人在一幢使馆房屋外设置了障碍,将文件堆进壁炉里,浇上煤油点燃。但中方军警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后,从烟囱浇下,挫败了苏联人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