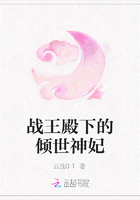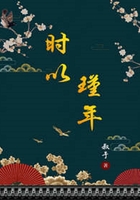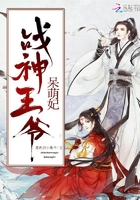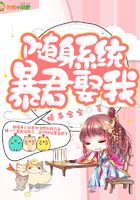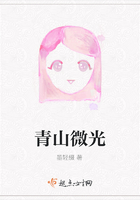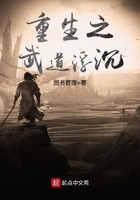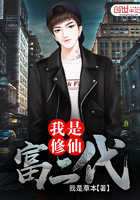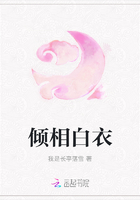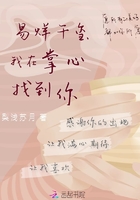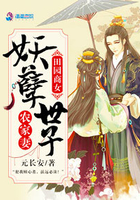难不成,祖父与祖母果真想将元娘许给何家?这何飞箭如此不定性,如何使得?
“阿兄!”此时李遐玉已经安然滑到岸边,笑吟吟地望着他,“前两日才接到阿兄的信,原以为过些日子再去驿道上接你也不迟,却不想你们行军竟这般迅疾。阿兄可是得了几日休沐?我同你一起回弘静县城罢。”
“也好。”谢琰回过神,淡淡笑了笑,“这些时日过得如何?家中可曾发生什么事?”
“家中安然无恙,你尽管放心就是。”李遐玉道,转念想起他曾在信中提起的谢璞,“阿兄过冬至、元日的时候,可曾去拜访谢家大兄?我仔细想了想,觉得眼下阿兄已经升任旅帅,军籍也记在河间府,便是告知家人应当亦无妨。”
“长安城内元日驱傩、上元观灯越是热闹,我们这些武侯便越发须得打起精神,四处巡防,以免出现各种意外。我哪有什么空闲去拜访大兄?”谢琰回道,“何况,我母亲性情固执,绝不会因我已经当了从八品上的武官而改变心意。除非我服朱服紫,否则她绝不会放弃让我贡举晋身的执念。”
“那待阿兄升任果毅都尉‘从五品下’之后,再衣锦还乡便是。”李遐玉道,“以阿兄如今的迁转速度,或许也不过是四五年的事罢了。说起来,谢家大兄省试可有望?”省试通常在一月末或二月初,如今大概已经张贴了榜文。不过,还须得等上几日,部曲才能将消息传回灵州。
“我看过他作的诗赋与策论。”谢琰拧起眉,喟叹道,“在陈州算是出挑,却并无令人眼前一亮的灵气。而且,大兄从未出过陈州境内,见识太狭窄,策论作得再花团锦簇也少了几分实用。便是有人引荐,恐怕也入不得考功员外郎的眼——何况那位范阳郡公,亦是出了名的公正之人。”他虽暂时放下了读书进学,但毕竟当年该学的样样不少,又时常读书,靠着扎实的功底倒也养出了几分鉴赏之力。在长安,历年进士的卷子都会印出来供人传看,他亦抽空读了许多,自是发现自家大兄离这些人才尚有几分差距。
“若非天才绝艳之辈,谁考进士不须得磨几年呢?”李遐玉安慰他,“若是谢家大兄留在长安,文气荟萃,或许比留在陈州更易长进些呢。如此说来,玉郎也该多读一读那些进士作的诗赋策论,才会懂得人外有人的道理。”
“我将那些省试实录册子都带了回来,另有些不错的文册文集,玉郎平时可多瞧一瞧。”
他们两人低声交谈、缓步离开,全然不曾注意到身后李遐龄欲言又止的模样。小家伙当初因恼怒谢琰“欺瞒”,在他前去长安之时仍不愿理会他。如今时过境迁,那些小心思早便烟消云散,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犹豫之间,他望向何飞箭,虚心请教:“何家二兄,若是你不慎与何家大兄争吵起来,又有几个月不曾见他,会如何与他相处?”
何飞箭望着谢琰与李遐玉的背影,有些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该如何相处就如何相处,权当作什么也不曾发生就是了。兄弟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你可别像小娘子那般扭扭捏捏,该做什么,尽管去做便是。”
“……”李遐龄忽地觉得,原来何二郎也能说出有道理的话,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你说得是。阿兄千里迢迢赶回来,无论如何我也该去问候他。冰嬉改日再顽,我随着阿兄阿姊家去了。”
“等等!你方才的神色很是奇怪,让我有些不舒服——你到底是何意?”
“何家二兄,你想得太多了。”
是夜,李家人再度齐聚一堂,在正院内堂中享用了丰盛的家宴。李和饮着谢琰与孙夏带回的长安阿婆清、郎官清,开怀大笑。柴氏亦笑看着底下已然长成的五个孩子,颇为欣慰。不过是数年罢了,几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便已经能够撑起家业,样样都思虑周全,委实是太不容易了。当初教养这些孩子的时候,她从未想过他们竟能成长到如斯地步。或许,老天到底仍是怜惜他们这两把老骨头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才将懂事的孩子们都送到了他们身边罢。待再过几年,他们或许也能过一过含饴弄孙的轻省日子了。
谢琰将带回的礼物分送出去,人人各不相同,样样都周全得很,得了家人连声夸赞。孙夏虽说也带了礼物,但到底粗疏一些,他也不甚在意。而李遐龄收到阿兄精心准备的法帖、省试实录册以及文卷、文册之后,便厚着脸皮像往常一样缠在了阿兄身边。李遐玉见两人依旧如故,亦是松了口气。
待到夜深时分,孩子们各自回了院子歇息。谢琰在院门前静立半晌,心中思虑纷纷,仍是忍不住回转,去见李和与柴氏。幸而两位长辈尚未歇息,将他唤了进去:“你先前在信中都报喜不报忧,难不成遇上了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