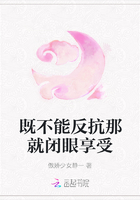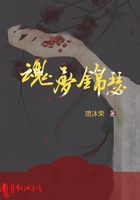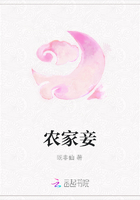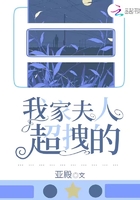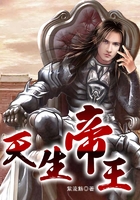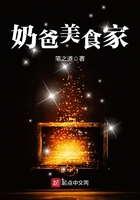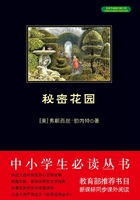重檐庑殿、鸱吻飞翘,华美而壮丽的太极殿中,诸臣在内侍的高唱声里,默默地朝着空空如也的御座行礼,而后又面向香风飘拂的垂帘,再度行礼。武皇后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重重脂粉掩盖着她略有几分苍白的面容,朱唇红艳如烈火。
作为木兰卫将军,李遐玉静静地立在她身侧,巡睃着丹陛底下正襟危坐的众臣。她瞧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容,尚书省左仆射崔子竟、右仆射刘仁轨、中书令李敬玄、侍中裴炎,凭着征吐蕃之功而晋封的凉国公契苾何力、甘国公慕容若、肃国公谢琰,以及六部尚书与九卿等,皆是服紫服绯的高官。
这些掌握大唐权势政务的儿郎,如今竟皆在脚下俯首。恍然间,她仿佛从内心深处升腾起了些许睥睨天下的雄心壮志。她倏然有些理解,为何武皇后向往着权力,为何她想坐在此处,紧紧地抓住权势不放手。原来,掌握天下众生的权力,令所有男儿都匍匐在脚底的威望,竟是如此诱人。
然而,作为坚持正统的重臣们,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后一直垂帘听政。接连数日,他们都在对武皇后施加压力,坚持要立英王李哲为太子。按理说,两位兄长去世,也确实该轮到英王了。但在场的人其实都很清楚,他禀性懦弱,既不聪慧亦无才华,并不适合为太子。只是,不少臣子宁可让这位太子监国,由他们把握朝政大事,也不愿见武皇后摄政。
“世间只有父子传承,断无兄死弟及的道理。”武皇后冷冷地望着他们,“当年让四郎‘李贤’继立太子,只是因三郎‘李弘’无后嗣罢了。如今四郎既有嫡子,立五郎便不合宗法。尔等逼着圣人与我再立太子,究竟意欲何为?!”
“殿下息怒!立太子本便在乎陛下之心,亦不必过分拘泥于宗法!如今安乐郡王尚幼,不能亲政监国,改立英王殿下为太子才合适啊!”中书令李敬玄手持笏板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陛下重病在身,理应由太子监国——”
“他有这个能力监国么?!”武皇后柳眉倒竖,怒喝道,“你们问一问崔爱卿!他是太子太傅,也教过英王!他可有理政监国之能?!若是他能有三郎或四郎的三分之才,圣人与我便不会这般犹豫了!将大唐交到他手中,我们便是死了也不可能放心!”
“……”众目睽睽之下,左仆射崔子竟很是冷静,“殿下所言,即为圣人之念?”因皇帝陛下重病卧床,他只能隔几天觐见一回,每次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头疾折磨而痛苦的神色,谈及太子之位时亦是犹豫不定。难不成这些时日,圣人已经被武皇后说服了?这倒也不无可能,英王的资质实在是太平庸了。有两位太子殿下珠玉在前,帝后又如何能看得上他呢?
“这是自然。”武皇后挑起眉,“圣人确实与我讨论过太子之事,但继立英王决计不可。”
有人抬起首,欲提殷王李旦,却被一旁安坐的三位国公瞪了回去。曾在沙场染血的武将,皆是杀得蛮狠无比的吐蕃人丢盔弃甲的猛士。他们的目光犹如利刃一般,将跃跃欲试的人们皆牢牢镇在原地,再也不敢妄动。众臣这才想起来,他们曾与“孝章皇帝”太子贤出征吐蕃,论立场定然是支持安乐郡王的。
崔子竟仿佛并未注意到旁边的暗潮汹涌,继续问:“那么,陛下的意思是,立安乐郡王为皇太孙?倘若如此,臣毫无异议。安乐郡王确实极类父祖,聪颖明慧,文武双全。且郡王今年已经十三岁,只需再过两三载,便可参与政务并监国。”
武皇后正要颔首,倏然有宫人跌跌撞撞地奔过来:“……安乐郡王……安乐郡王误食毒饼!已经昏迷不醒!!太子妃‘房氏’命奴前来禀告!请皇后殿下为郡王做主!!”
闻言,群臣大惊,武皇后更是震怒无比。她倏然立了起来,苍白的面容用脂粉也掩藏不住,几乎是声嘶力竭地怒喊:“太医可请来了?!还不赶紧将甘露殿的御医派去东宫!!立即封锁太极宫!谁也不准出入!给我仔细地查!!看看究竟是谁要对我的孙儿下手!!”
李遐玉立即行礼,低声道:“木兰卫领命。”
当她从垂帘后走出来的时候,许多臣子都怔了怔,这位定敏国夫人的封号,与其夫谢琰的封号并不一致,曾引来诸多议论。有人说,因“定敏”二字是先帝所赐,故而不得擅动;又有人说,若是女子能封国公,恐怕她已经凭着功劳封爵了,故而才特意不变。不过,不论如何,她都是武皇后的亲信,木兰卫的开创者与执掌者,在长安城内亦是威名赫赫。
谢琰将目光投向她,不着痕迹地表明他的忧虑。夺嫡之事,他们本该独善其身,不参与其中。但木兰卫地位特殊,遵从武皇后之令行事,如今却是不得不涉入了。
李遐玉脚步微微顿了顿,手紧紧地按在了横刀的刀柄之上,翩然离去。
因救治及时,安乐郡王只是被毒伤了脾胃,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昔日强健的少年郎,如今却只能满面苍白地躺在床榻上养病,瞧着着实可怜。武皇后陪伴了他一会儿,怜惜地替他盖好了衾被,又吩咐太子妃房氏好生守着,这才回到了甘露殿偏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