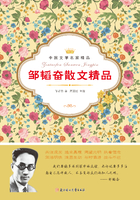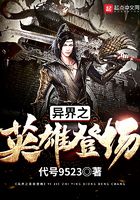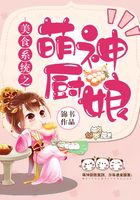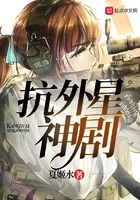我爱祖国的原野,
我是在这原野生长的。
迈着健壮的脚步,
我走着,踏着每一块土壤,
都触觉着温暖,
仿佛与我融合为一片。
我的祖先都已化为这原野的泥沙,
让树繁茂,让谷粒生芽又结实,
让野花装饰曲折小径的边缘,
让细草铺满松软的毡子,
让小溪唱着歌流过,
让菜圃展开浓绿的嫩叶,
让高下回环的田畦,
摇着金黄的香稻。
而我也将化为这原野的泥沙啊,
我将与这里的一切同在。
我爱这原野的一切,
我向原野激动的呼喊,
带着无尽的渴望,
仰卧在原野上,
望着蔚蓝的远天。
原野也拥抱我,
以温柔的发,温柔的肢体抚慰我,
我的身体永远是属于这原野的。
我爱听这原野的声音,
这村犬的吠、鸡的啼叫、
和牛的鸣声。
或是一只野鸟,
一头虫子都能引我神往。
而颜色又是这样美好啊,
在朴素中显出典雅与安闲。
我爱每一溪桥,
每一岩谷和村落,
甚至每一蜷卧的小丘,
都给我以可亲的容貌。
坐在山和山叠绕的,
田和田环曲的,
路和路区划的,
雾气蒙蒙的田野中,
我闻着而且喜爱着
那些不知名的干草香。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在青木关农村中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重庆《新蜀报》)
作者附记中提到的青木关,今属重庆市沙坪坝区,处在重庆歇马镇、青木关镇和凤凰镇的交界地带。抗战期间那一带统称江北,那里关隘险阻、森林密布,绿色绵延。
1938年春,常任侠到武汉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并应茅盾、廖沫沙之邀,为《抗战日报》编副刊。年底随三厅转移重庆,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艺术考古员,兼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
1939年到1941年间,常任侠曾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胡小石等共同主持了重庆江北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可能出于田野调查,诗人会经常到青木关访古探幽,那葱绿的山野代表了战时大后方片刻的宁静,农村田园风光抚慰着诗人敏感的心灵。
面对日寇侵略,诗人起笔直抒胸臆:“我爱祖国的原野。”第二段写的是自然和生命的循环,在诗人眼里,化为泥沙的祖先,都已变成茂密的树、结实的谷粒和“装饰曲折小径的边缘”的野花。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使读者与原野之间一下子亲近起来,并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虽然诗歌作于12月初,一方面源于山中的气候,另外一方面更源于诗人的美好想象,“菜圃展开浓绿的嫩叶”,“田畦摇着金黄的香稻”,恬静的农村景象、富足的农耕生活,依然在诗人笔下如画卷一般次第展开。紧接着,诗人以“音”配“画”,犬的叫声、鸟的啼音、牛的低鸣,都被诗人一一揽入到诗中。诗人写得很细腻,甚至“一头虫子都能引我神往”。
在远景、近景都作了色彩明快的勾勒之后,诗人给溪桥、村落、山丘等景物予以中景描写,层层揭示原野之美。
能在半壁焦土之外看到原野,并且因热爱而愿意化为这原野的泥沙,诗人以祖国山川自然之美,对抗战争的恶,讴歌炮火下顽强生长的绿色,这是诗人作为艺术家的别致所在。这是抗战诗篇中一朵带着原野露珠的花,以曲曲折折的抒情,坚定着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的信心。
1904年,诗人出生于洪灾多发的安徽颍上,家贫母慈。1922年,考入南京美专。1927年加入北伐学生军。1928年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5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研究东方艺术史和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1936年底返国,在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1949年应周恩来电召返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特级教授。
诗人以诗明志,抗战时期,与孙望编辑出版了《现代中国诗选》,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诗坛上全部诗人及其作品。诗人以言立身,长期从事东方艺术史、考古学的研究,并旁及中亚、东亚、东南亚诸国美术史以及音乐、舞蹈史的研究,对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96年10月在北京辞世,享年93岁。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著有《常任侠全集》(6卷)。
这位明朝大将常遇春的后人,一生以“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为座右铭。1949年,奉召从印度回国之际,常任侠口占七绝一首:“远离国土久飘零,雪压长松岁几更。初见红旗忽下泪,何人知我此时情。”爱国之情之意,铺满祖国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