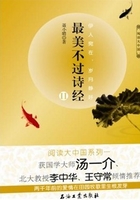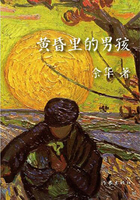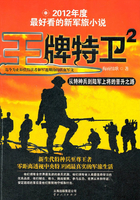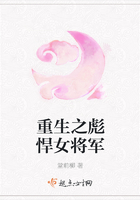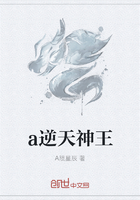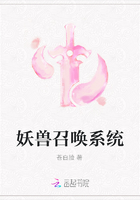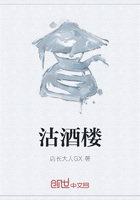乔伊斯的沉默并非那种妥协和屈服的沉默,听凭压迫力量为所欲为;乔伊斯的沉默是用沉默来与压迫力量保持距离,同时用心底的声音来与压迫性力量对抗,保持自己意志的清醒独立,等待有一天可以说出自己的声音。
斯蒂芬的沉默的反抗性在他面对穆利根、迪西校长这些强力人物时突出地表现出来。穆利根听了斯蒂芬关于爱尔兰艺术的比喻后,开始挽着斯蒂芬的胳膊称赞斯蒂芬,大谈他们两个结成同盟一起收拾海恩斯,建立新的异教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斯蒂芬一言未发,但是在穆利根的每句话中间都有一段或两段斯蒂芬的内心独白插进来,对穆利根的话做出无声的评判:当穆利根夸奖他“比别人更有灵魂”时,斯蒂芬的内心独白无声地回应到:“他惧怕我艺术的柳叶刀”[43];当穆利根说“只要你我携手,我们就能在这个岛上做点什么”[44]时,斯蒂芬的内心独白说“克兰利的胳膊。他的胳膊”[45]。克兰利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的朋友,曾和他挽着胳膊大谈艺术和人生,最后却背叛了他。因此斯蒂芬这里的意思是,穆利根的胳膊与克兰利的胳膊一样,都是虚假的友谊,都将背叛;当穆利根说像捉弄肯普索普那样捉弄海恩斯时,斯蒂芬的脑海里无声地出现了捉弄者的冷漠和肯普索普的可怜。因此穆利根接下来关于建立新异教中心的滔滔不绝的声音,只如风中的碎片,飘过斯蒂芬的耳朵,却不能对斯蒂芬的心灵施加任何影响。相反,斯蒂芬毫不犹豫地打断他,告诉他放过海恩斯。
在这里可以看到,斯蒂芬表面的沉默中其实包含着针锋相对的立场,他在沉默中反驳着穆利根的每句话,指出穆利根的虚伪、善变和冷酷的本质。斯蒂芬的灵魂并没有被外部的声音屈折,而是倔强地等待着自己发声的时机,然后或者小规模地简短有力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或者用自己的利器钢笔[46],向对手掷出更有力的投枪。
七
然而,很多时候,社会的规训力量并不允许异议者像漏网的鱼一样沉默但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规训力量用种种手法迫使被规训者按照它的指示行动,正如穆利根不会听凭身边有一个保持距离的旁观者或疏离的评判者。在《尤利西斯》中,穆利根强迫斯蒂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斯蒂芬用自己的格言向海恩斯要钱。
对斯蒂芬来说,这是一种屈辱的乞讨姿态,是他高傲的灵魂所不容许的。因此当穆利根第一次要斯蒂芬向海恩斯要钱时,斯蒂芬使用了沉默的手法,没有回答[47]。但是穆利根并不因此放过他,而是向海恩斯说了,并第二次敦促斯蒂芬这样做。斯蒂芬在无法沉默的情况下回答说“今天早晨我会拿到工资”[48],言下之意“我宁愿自己拿钱买我的自由”。但是穆利根不但立刻让斯蒂芬请客,将这笔钱据为己有,并且第三次当着海恩斯的面,让斯蒂芬要钱。规训的力量不会留给被规训力量任何躲避的空间,在这种步步紧逼的强制下,斯蒂芬拿起了他的第二个武器,“狡黠”。
狡黠原本是奥德修斯的武器。他用狡黠逃过了独眼巨人,用狡黠攻下了特洛伊,用狡黠与奥林匹斯山的神祇们斗智,他还想用狡黠(装疯)来逃过特洛伊战争的大征兵。这种狡黠之所以被称为“cunning”而不是“wise”(聪明),因为它更不带有价值判断,完全是自我生存策略,更接近一种市民的智慧。《列那狐传奇》中既捉弄当权者又欺负弱小者的列那狐是狡黠的,《亨利五世》中用出乖露丑赢得王子的青睐的福斯塔夫是狡黠的,《巨人传》中一心捉弄别人,把笑话他的羊贩子骗下海的巴汝奇是狡黠的。但是随着西方文学越来越道德化,随着智慧越来越被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这种自保的智慧也越来越被视为小聪明,退位成配角和丑角。乔伊斯则重向古希腊寻找摆脱现代权力规训的出路[49],把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智慧视为现代英雄的武器。面对穆利根的步步紧逼,斯蒂芬运用狡黠,让自己在不正面对抗规训力量的同时,却能保持自己的自由。乔伊斯在这件事上使用的狡黠武器是反讽。
反讽是用似是而非的手法,在一句话中包含相互矛盾的两种判断,从而使句子陷入一种暧昧两可的处境[50]。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使诗作和诗人同时取得自由”[51],由于相反判断在反讽中同时存在,孰是孰非不做明确说明,藉此诗人可以接受解读者的任何解释,而不必使自己陷入非此即彼的约束之中,因此是一种“消极自由”[52]。
斯蒂芬在穆利根的反复催促下,干脆直接问海恩斯“我能从中赚点儿钱吗?”[53]表面上遵循了穆利根的指示。但是从后面穆利根对他说这句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蒂芬说这句话时,带着“下流的斜睨和扫兴的耶稣会士的嘲讽”[54],也就是说,虽然斯蒂芬说出的话表达了要钱的意思,但是他说话的表情和语气,又把这句话变成一个玩笑,以肢体语言取消了所说的话。这样,斯蒂芬就处于一种反讽的暧昧两可的状态,既说了要钱,满足了穆利根的要求,又用语气和表情表示了不要钱,只是开玩笑,从而保留了自己的尊严。这样的暧昧两可的要求也使海恩斯不必正面回答,一笑而过,避免了可能产生的难堪。
德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反讽是文学现代性在话语上的标志[5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反讽赋予了现代社会的异议者一个含混空间,在这里异议者既可以表达自己的异议,又保留了自己的自由。
八
正是因为反讽这一可以在强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规训网络下保持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力量,从而成为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主要运用的手法。“第二十二条军规”象征的同样是无所不在的现代规训力量,它可以随时随地出现,无法反驳,从而也无法反击。
卡夫卡曾经尝试过让《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对那个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机器——法庭进行抵抗,置之不理,但是卡夫卡清醒地知道个人的抵抗在这种强大的规训力量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带给抵抗者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他让约瑟夫·K最后“像一条狗似的”[56]被法庭派来的人杀死。
约瑟夫·海勒也深知这一点,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他也让一名叫邓巴的中尉大声说出真相和不满,邓巴最终却被权力机构派来的人秘密处理掉了。主人公尤索林虽然力量强大到可以打败一个个暗杀者,但是因为个人的抵抗无法让社会性的规训力量停止,只要他不死,暗杀就不会结束,因此尤索林其实并没有真正摆脱被规训力量消灭的阴影。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同样使用过沉默和反讽,但是规训力量依然不放过他,因此最后,约瑟夫·海勒给了尤索林,也是所有现代人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逃亡。
不约而同的,乔伊斯同样把流亡作为现代人在社会规训力量面前最后的出路。沉默和狡黠可以摆脱暂时的危险,却无法使人从根本上,至少长久地摆脱规训的威胁。现代社会的规训力量是条如影随形的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永不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斯蒂芬选择了离开马特卢城堡,乔伊斯选择了离开爱尔兰,自我流亡,转身寻找一个自由的世界。最终,巴黎,或者更确切地说,艺术的世界,将成为乔伊斯的自由天堂[57]。正是在这个世界里,乔伊斯最终用艺术的柳叶刀做出了自己的回击,而他带给后人的对规训话语的反思,正是规训性社会网络出现裂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