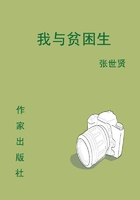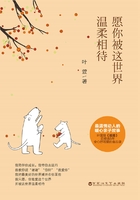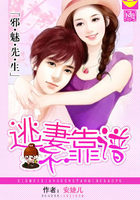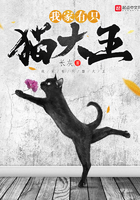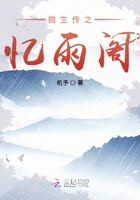乔伊斯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比《尤利西斯》更进了一步,彻底摆脱了斯蒂芬的个人主义,主人公壹耳微蚵完全融入了群体之中。壹耳微蚵的简写是HCE,按照乔伊斯的解释,HCE是“此即人人”(Here Comes Everybody)的缩写,意味着主人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人(everybody),总是看上去类似和等于他自己,并且特别符合任何和所有这样的世界普遍性(universalisation)”[75]。HCE这一“人人”形象表明,乔伊斯最终接受了人的社会性,把自我看作人类整体的一个分子。这一点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主题上也突出地体现出来,正如乔伊斯的研究者们公认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像其它小说那样写一个或几个人,也不是塑造某个社会集团的“群像”,而是从哲理高度阐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小说中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抽象的,都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
乔伊斯后期从斯蒂芬的个人主义向HCE的群体生命的这个转变过程,用歌德的概念说是一次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在本质上与浮士德从私人书斋走向群众集体劳动是一致的,都是艺术家从纯艺术的世界向民间文化的回归。
有趣的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选择了都柏林一个酒馆老板来做自己的“人人”,用他酒馆的景象和酒客来代表人类社会。很显然,乔伊斯的这个选择来自他对都柏林生活的理解。在他的心目中,都柏林酒馆的聚饮代表着爱尔兰乃至整个人类的民间文化。
乔伊斯后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乔伊斯自己性格中遗传自父亲的喜剧成分外,婚后的家庭生活和流亡欧洲大陆的经历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早年,乔伊斯虽然在青年人确立自我的欲望的驱使下表现得孤傲不逊,但他的性格中一直隐含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喜剧性或者说丑角的一面,并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来。据雅各斯·麦坎顿回忆,乔伊斯曾自称为“爱尔兰小丑”[76],直到成年,他还会跳一种四肢着地的“蜘蛛舞”来娱乐朋友。乔伊斯的妻子诺拉是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女性,写信连标点也不加,趣味完全谈不上高雅,但正如乔伊斯在分析《流亡者》的意象时写的,诺拉对乔伊斯来说正意味着淳朴浑厚的大地。在乔伊斯的后期作品中,妻子身份的女性总表现出大地所具有的深厚、包容和永恒这些特征。乔伊斯把《尤利西斯》定在他和诺拉相识的那一天不是没有深义的,这一天诺拉使乔伊斯找到了立足的大地,是诺拉式的女性把乔伊斯从早期纯粹的艺术世界带回到日常生活现实。
诺拉使乔伊斯获得现实感,流亡欧洲的生活则使乔伊斯重新审视和评价爱尔兰文化。许多年后乔伊斯写道:“有时想到爱尔兰,发现我过去似乎过于苛刻了。(至少在《都柏林人》中)我没有反映出这个城市具有的魅力,自从离开爱尔兰后,除了巴黎,我在其它任何城市都没感受到在都柏林时的那种自在。我没能反映出它的纯朴的偏狭和热情。后一种‘美德’我至今没在欧洲其它地方发现过。我从未公正地对待过它的美,在我的心目中它比我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或意大利所看到的都更具有自然的美。”[77]乔伊斯离开了爱尔兰,反而更亲近爱尔兰文化。他后来不仅完全接受了他父亲那种酒吧生活,而且开始对爱尔兰的诙谐文化发生了兴趣,“一些人在我的住处呆到深夜,谈论爱尔兰的智慧和幽默”[78],他们谈得如此之多,以至有一天对乔伊斯的创作从来不感兴趣的诺拉也向乔伊斯要关于爱尔兰智慧和幽默的书看。
当然,乔伊斯对爱尔兰诙谐文化的最高的礼赞莫过于他在作品中描写爱尔兰的酒吧狂欢,特别是表现出了这种文化的现实魅力,同时,反过来,爱尔兰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赋予了乔伊斯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浑厚感和生命力。
三
爱尔兰的民间诙谐文化除了改变了乔伊斯作品的价值取向,使他从早期的超人价值转向后期的群体价值外,随着作品重心的转变,乔伊斯后期作品的题材、结构和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相比,乔伊斯的后期作品越来越显得“什么也没说”[79],越来越缺少黑格尔认为一部作品应有的绝对理念,但同时,乔伊斯的作品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现实感和生命力,在形式上也越来越复杂多变。
美国学者克里斯特娃曾经谈到乔伊斯后期作品中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特征,她把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列为典型的“多声部小说”,认为正是这一语言特征赋予了《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不断延展的生命力[80]。不过她主要是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来分析乔伊斯作品的结构、叙述这些形式方面的问题的。笔者同意克里斯特娃的观点,不过同时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民间诙谐文化因素远远超出了形式这个范围。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斯蒂芬的自我的人与布卢姆的社会的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之相应的斯蒂芬的封闭性、排他性和布卢姆的开放性、包容性,而开放性是布卢姆的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独眼巨人”一章中,布卢姆与“市民”的冲突表面看是布卢姆的犹太人身份导致的,但从这一章的“市民”叙述模式与布卢姆本人的思维模式看,两个人的叙述和思维模式其实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上,一个是“市民”的狭隘专制的爱尔兰民族沙文主义文化,一个是开放兼容的民间诙谐文化,两人真正的冲突是文本叙述层面中封闭的文化与开放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一章中布卢姆的胜利也不是简单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开放的价值观念的胜利。罗伯特·舒勒认为,这种价值观念“把我们逐步引导到一种不同于早期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对人的认识之中”[81]。
与早期小说相比,乔伊斯的后期小说容纳了许多乔伊斯过去曾排斥的东西,特别是属于现实的物质—肉体层面的东西,这一点在作品使用的语言上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早在《都柏林人》阶段,《都柏林人》就曾经因为书中的“污言秽语”在出版时数次碰壁,不过乔伊斯此时的辩解是这些“污言秽语”是爱尔兰社会本身就有的,如果把这些话删去就会影响爱尔兰人看到自己的丑陋。显然,乔伊斯说这话的时候,对这些“污言秽语”持的是批判的态度,是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来揭示现实的“丑陋”。与后来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都柏林人》的语言其实可以说“干净”得多了,乔伊斯后期的作品不仅大量使用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粪便”[82]的语言,而且随着“粪便语言”的增多,乔伊斯在使用这些粪便语言时所持的否定态度却逐渐减少,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已明确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粪便学研究。“刻尔吉”和“潘奈洛佩”两章的语言应该说是《尤利西斯》中最污秽的,然而这两章带给读者的却不是《都柏林人》式的压抑沉闷,反而有着一种狂欢式的放纵和宣泄。
与“粪便”语言相应的是人物形象的物质化、肉体化和肉欲化。《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禁欲和思辩。他曾经被性诱惑过一次,但这次经历反而使他走上了极端的禁欲主义。他“不抽烟,不到市场上去,也从不和女孩子打情骂俏,他从不干这类事,或者说,他妈的什么也不干”[83]。斯蒂芬“艺术家”式地终日沉浸在纯粹的审美体验之中,他的思想里只有存在、美这样的理念化的东西。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的这一特征继续发展,“普洛冬”和“斯鸠利和卡吕布狄”两章体现了斯蒂芬抽象思辩的高峰。詹姆斯·马多克斯认为,正是斯蒂芬这种“排他的书卷气”造成了斯蒂芬这一形象的缺陷,他指出,斯蒂芬的头脑中只有“关于经验的抽象概念,而没有经验本身”[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