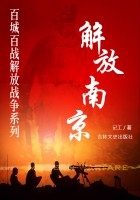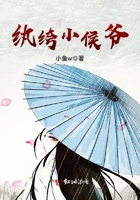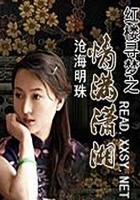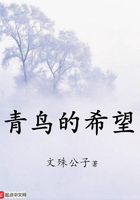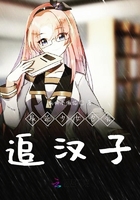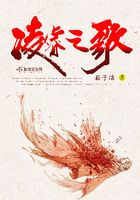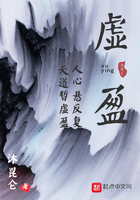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希望千禧之年能带来好运,带来生活的富裕,同时也有一丝的忧郁与不安:离“千年虫”发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人们害怕世纪交替时出现导弹乱飞、飞机迷航、计算机不听指令等情况。然而,就在这世纪交替的前两天,即1999年12月30日,我在厦门大学突然接到弟弟高丰国的电话:父亲病故了。虽然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接到电话后还是被这个噩耗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我的祖辈和父辈像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是从屈辱、贫穷中走过来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过上了小康的生活。父亲于1936年11月出生于原汉阳县永安镇高家畈,是一个有两个行政村、2000多人口而95%以上的家庭以高姓为主的大村落,高姓在汉阳县可以说是望族了。据高氏家谱记载,我们的祖先是明朝朱元璋时的吏部官员高大用,洪武六年(即公元1373年)朱元璋封其六子朱桢为楚昭王,选中文韬武略的高大用为随王护驾重臣,自此,宋元世居金陵的高氏就有一支留落在湖北了,高大用就是一世祖。高大用有三子,其二子高得二也有三子,长子高文通以武功授锦衣卫指挥,晚年解甲归田后,先后寓居汉阳城区桃花岭、洗马口、高公桥等处,均因城市喧闹,乃迁至高家畈居住,文通公就是高家畈的开山鼻祖了。这里东北面是奓山,东面是小奓山,山下是小奓湖。望山靠湖,自然风景优美,文通公选择到高家畈居住,大概是看中了这里的自然风景秀丽,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吧。文通公有四子,其长子琰有一鹏、一羽两子。高一鹏、高一羽兄弟俩先后是明丁丑年和丙戍年的进士,两人分别在四川中江和湖北安陆为官。此后,高一鹏任职期满回到了高家畈,而高一羽则迁居安陆。高一鹏生七子,除四子、五子远游未归外,长子、二子、三子、六子、七子子孙繁衍,连绵不断。以致现在人们还知道哪个小村落是几房的后代。我们是二房的后代,自然辈分很低。
说起我的父亲,在高家畈也是很低微的。我的高祖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膝下只有祖父一人。当年还没有分家,大家生活在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只能过上温饱的生活,祖父自然难以娶上媳妇。那时我的祖母在奓山左姓人家寡居,膝下有一个五岁的儿子。祖母是被强行抢亲的,那时高家人多势众,由于长年在外管湖,村民都有一股凶悍、霸道的气势,周围十里八乡的外姓人家都是退避三舍,左家人单力薄,自然不是高家的对手。我的祖父母成亲后生下了我父亲。
然而好景不长,在我父亲三岁时祖父就去世了,高家畈属于湖区,男人们长年在外下湖打草、捕鱼、挖藕,也长年从事农田劳动,当时血吸虫病很是流行,加之医疗很差,无法控制病疫,村里很多男人都是在壮年时失去生命的,很多家庭留下的是孤儿寡母。我的大奶奶(即祖父的兄嫂)也是在二十八岁时失去丈夫的,留下一个女儿。这样一来我的祖母和大奶奶分别守着父亲和大伯妈在这个大家庭里苦苦度日。
建国前,高家畈自办了一个正本中学,凡是高姓家族的子弟均可在这里就读,父亲自然不在话下,但他本人寡言少语,学习成绩很差,勉勉强强读到高小毕业。在汉阳县,由于地少人多,加之距武汉市只有四十公里路程,许多人家待小孩长到十多岁就让村里人带到武汉当学徒挣钱养家。父亲十三岁时正值武汉解放,他是由本村一位叔叔带到武汉当学徒的,开始是给师傅家带小孩,以后再逐渐学了一点木工手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举目无亲,生性老实,沉默寡言,自然难以讨得师傅、师娘的欢心,吃了不少苦头。1957年搞城市合作化运动,父亲进了解放市场,成为一名集体所有制工人。
我母亲的身世也是很不幸的。母亲五岁时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不知是失散了还是被遗弃,我的大奶奶始终未说,母亲至今也不知道。她五岁时就被我们高家的一位远亲收养,那家也是家大口阔,生活不富裕,添一张嘴巴吃饭自然成了包袱,少不了被打骂。后来我祖母看她实在是可怜,就收养了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祖母分得了一条船,就在小奓湖摆渡过活,母亲小小年纪就成为祖母的帮手,附近的人们习惯上称我祖母是“渡船婆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父亲在武汉上班,平时的联系就是每月十几号父亲汇一次款回家,逢年过节父亲才得以回家一次,大包小包带回一些吃的、用的东西。父亲平时生活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每月的工资除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和日常开销外,大部分寄回家了。我记忆中最清楚的是每年年底,生产队年终决算时,我们家肯定是超支户,这时父亲就从单位借支一些钱交上超支款,日后从工资中慢慢归还。这种贫穷的日子养成了他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能过得去就行。
父亲生性老实,沉默寡言,不善交际,除了自家的几个亲戚时常走动外,几乎没什么朋友。由于是“半边户”,集体单位福利差,没有分到一处住房,平时只是租住在硚口居仁门一个8平方米的木板房里,光线差,平时上楼都是小心谨慎,因为木板房长年失修,人走在上面,房子都在颤动。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87年,以后在我那里才住上了楼房。近几年他住在汉阳七里小区三弟爱国家里,总算了却不枉做一个城里人的心愿。
父亲在1986年提前退休,丰国顶职后从汉阳县来到武汉,那一年我祖母去世,母亲也来到武汉,一家人租住在硚口崇仁门一处私房里,全家总算团圆了。父亲的身体很好,干惯了体力活的人难得清闲,平时给人家干点木工活补贴家用。直到90年代初搬到我这里后才没有外出做活。90年代中后期父亲的身体明显差多了,脸也消瘦了,真是老了许多,其间还有两次轻度中风,父亲只是简单地去医院看看病,却从未做过彻底的检查,只知道肾功能不好,自己买些补药吃,既花了钱又不见得对身体有利,如果早点检查出是糖尿病,其病情是可以控制的,不至于到病入膏肓时才知病因,此时已为时晚矣。去年11月下旬我曾从厦门赶回武汉,看望病中的父亲,哪知不到两个月他便去世,这竟是最后的一别。
如今父亲安葬在他出身的地方——蔡甸区永安镇高家畈的小奓湖畔,这里长眠着高家的祖祖辈辈,包括我的祖母、大奶奶,愿他们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从此安息,我们也将永远地怀念他们。
二〇〇〇年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