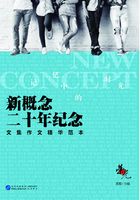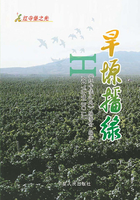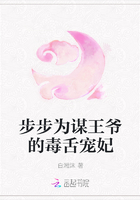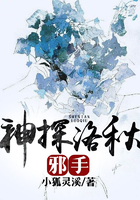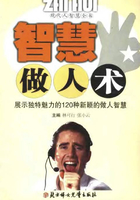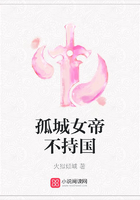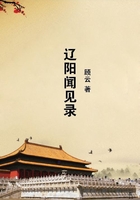提笔写这篇序言时,莫名地想到我的一些酒事。
首先声明,我不会喝酒,这不免有点地无银之嫌。我想说我没酒瘾,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想到酒的,而饮酒时,酒意动辄又写在脸上,如胭染两腮,饰演关公是无须化妆的,我喝酒须酒肴,这又距酒趣甚远,真会饮酒的人,即便是喝醉了,脚下发飘亦面不改色,有无酒肴也无关紧要。我曾有一邻,是位小学校长,好酒,每日路过小店,酒三两,一饮而尽,随手在柜台边捏一粒盐,放于口中,然后,双手捂住嘴,生怕酒味跑了。每日一喝,天天如是,一时被传为谈资。
追溯在下的喝酒史,最早还是我记事之前的事,听父母亲说的,父亲好酒,看着父亲饮酒好奇,端起酒盅就喝,辣得大哭。不知因何,总觉那不是我,可以是任何无知孩童。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喝酒,应是十多岁的时候。那时,村里有个酒厂,烧制老白干,我常去酒厂玩耍,印象中有大锅炉、大水泥池子。年节,酒厂发酒,父亲鼓励我喝,儿时,逞能又逞强,便想试试自己能喝多少,父亲给我倒酒,我一气喝了十二小酒盅,还没醉意,记得酒入口火炭一般热辣。一盅可盛酒三钱,父亲大体给我算了一下酒量,很赞赏。第一次畅快开饮的记录便留在了记忆里。
成年后,饮酒就不计其数了,目前为止,总共醉了两次半,不妨今天都和盘托出。
第一次醉酒,是中秋之前的一次聚餐,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个临时工,酒馆不大,位置在四岔路口,酒馆的名字很有趣,叫“好再来”。因为是新人,跟领导同事初次喝酒,又要敬酒,又要陪酒,喝得猛,不觉喝高了。不知怎么走出酒馆、又是如何骑上的自相车、上公路、入土堰,当我醒来时,只见我躺在土堰边,月已挂中天,自行车在土堰半腰陪着我。竟然没吐酒。每忆起,都会发出人生难得几回醉的感叹。
第二次,是同窗小聚,在小城的一家酒店,酒店还算气派,包间也大,红毡铺地,却记不起酒店的名称,只记得酒喝得痛快,菜肴倒在其次,主要是有往事可下酒,同学间的那些糗事,是特级大厨所烹调不出来的,酒的度数,亦远没有寒夜给被子压件大衣那般的情谊高,不觉就喝过了。第一次醉酒是不知道留量,此次醉酒是不想让自己留量。
从酒店出来,又去K歌,随歌乱舞,不亦乐乎!歌唱得荒腔走板,声嘶力竭,直把酒气喊得差不多了,又到大排档去补充,从大排档起身,一人手里还拎着一只啤酒瓶子,砸好几家旅馆,见一群醉汉,都说没床铺了,只得折回头,再去大排档喝酒。
第三次,是文友小聚,在南方,奇山异水,酒店开在水上,酒是自家酿制的,都说南方人不能喝酒,估计那是平均数,有的人是被不能喝的。酒是原液,绿蚁新醅酒,晶莹透亮。我仗着自己是北方人,有心里优势,到底是南方人,以柔克刚,嘴上说不能喝酒,实际酒量挺大,事后想想,能陪酒的,酒量当然可以,推杯问盏,喝得尽兴,自觉酒要喝高了,这可是出门在外,不能喝得太难看,赶忙离席,溜之大吉,悄悄地跑到栈桥上去吹吹风。否则,非醉不可。这次算是半醉。
写序宜短不宜长。本书讲述的是古代文人饮酒的故事,一不留神,把自己的那点酒事给解密了,不想听我啰嗦的,赶紧翻开正文,去品评书中文人与酒的故事,集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体,别有一番风味。再说,文人与酒相加,那就是文化。别不赘言,就此打住,是为序。
马浩
2015年1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