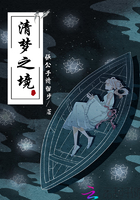海恩斯停下脚步,掏出一只光滑的银质烟盒,上面闪烁着一颗绿宝石。他用拇指把它按开,递了过去。
——谢谢,斯蒂芬说着,拿了一支香烟。
海恩斯自己也取了一支,啪的一声又把盒子关上,放回侧兜里,并从背心兜里掏出一只翻打火匣,也把它按开,自己先点着了烟,随即双手像两扇贝壳似的拢着燃起的火绒,伸向斯蒂芬。
——是啊,当然喽,他们重新向前走着,他说。要么信,要么信,你说对不?就我个人来说,我就容忍不了人格神这种概念。你也不赞成,对吧?
——你在我身上看到的,斯蒂芬闷闷不乐地说,是一个可怕的自由思想的典型。
他继续走着,等待对方开口,身边拖着那根梣木手杖。手杖上的金属包头沿着小径轻快地跟随着他,在他的脚后跟吱吱作响。我的好搭档跟着我,叫着斯蒂依依依依依芬。一条波状道道,沿着小径。今晚他们摸着黑儿来到这里,就会踏着它了。他想要这把钥匙。那是我的。房租是我交的。而今我吃着他那苦涩的面包[116]。把钥匙也给他拉倒。一股脑儿。他会向我讨的。从他的眼神里也看得出来。
——总之,海恩斯开口说……
斯蒂芬回过头去,只见那冷冷地打量着他的眼色并非完全缺乏善意。
——总之,我认为你是能够在思想上挣脱羁绊的。依我看,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我是两个主人的奴仆,斯蒂芬说,一个英国的和一个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海恩斯说。
一个疯狂的女王[117],年迈而且爱妒忌。给朕下跪。
——还有第三个[118],斯蒂芬说,他要我给他打杂。
——意大利的?海恩斯又说。你是什么意思?
——大英帝国,斯蒂芬回答说,他的脸涨红了,还有神圣罗马使徒公教会[119]。
海恩斯把沾在下唇上的一些烟叶屑抹掉后才说话。
——我很能理解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一个爱尔兰人一定会这么想的。我们英国人觉得我们对待你们不怎么公平。看来这要怪历史[120]。
堂堂皇皇而威风凛凛的称号勾起了斯蒂芬对其铜钟那胜利的铿锵声的记忆:信奉独一至圣使公教会:礼拜仪式与教义像他本人那稀有的思想一般缓慢地发展,并起着变化,命星的神秘变化。《马尔塞鲁斯教皇[121]弥撒曲》[122]中的使徒象征[123],大家的歌声汇在一起,嘹亮地唱着坚信之歌;在他们的颂歌后面,富于战斗性的教会那位时刻警惕着的使者[124]缴了异教祖师的械。并加以威胁异教徒们成群结队地逃窜,主教冠歪歪斜斜;他们是佛提乌[125]以及包括穆利根在内的一群嘲弄者;还有为了证实基督圣父并非一体而毕生展开漫长斗争的阿里乌[126],以及否认基督具有凡人肉身的瓦伦廷[127];再有就是深奥莫测的非洲异教始祖撒伯里乌[128],他主张圣父本人就是他自己的圣子。刚才穆利根就曾用此话来嘲弄这位陌生人[129]。无谓的嘲弄。一切织风者最终必落得一场空[130]。他们受到威胁,被缴械,被击败;在冲突中,来自教会的那些摆好阵势的使者们,米迦勒的万军,用长矛和盾牌永远保卫教会。
听哪,听哪。经久不息的喝彩。该死!以天主的名[131]!
——当然喽,我是个英国人,海恩斯的嗓音说,因此我在感觉上是个英国人。我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落入德国犹太人的手里[132]。我认为当前,这恐怕是我们全国性的问题。
有两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眺望着:一个是商人,另一个是船老大。
——船正向阄牛港[133]开呢。
船老大略带轻蔑神情朝海湾北部点了点头。
——那一带有五深,他说,一点钟左右涨潮,它就会朝那边浮去了。今儿个已经是第九天[134]啦。
淹死的人。一只帆船在空荡荡的海湾里顺风改变着航向,等待一团泡肿的玩意儿突然浮上来,一张肿胀的脸,盐白色的,翻转向太阳。我在这儿哪。
他们沿着弯曲的小道下到了湾汊。勃克·穆利根站在岩石上,他只穿了件衬衫,没有夹住的领带在肩上飘动。一个年轻人抓住他附近一块岩石的尖角,在颜色深得像果冻般的水里,宛若青蛙似的缓缓踹动着两条绿腿。
——弟弟跟你在一起吗,玛拉基?
——他在韦斯特米思。跟班农[135]一家人在一起。
——还在那儿吗?班农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在那儿遇见了一个可爱的小妞儿。他管她叫照相姑娘[136]。
——是快照吧,呃?一拍就成。
勃克·穆利根坐下来解他那高腰靴子的带子。离岩角不远处,抽冷子冒出一张上岁数的人那涨得通红的脸,喷着水。他攀住石头爬上来。水在他的脑袋以及花环般的一圈灰发[137]上闪烁着,沿着他的胸脯和肚子流淌下来,从他那松垂着的黑色缠腰布里往外冒。
勃克·穆利根闪过身子,让他爬过去,瞥了海恩斯和斯蒂芬一眼,用大拇指甲虔诚地在额头、嘴唇和胸骨上画了十字[138]。
——西摩回城里来啦,年轻人重新抓住岩角说,他想弃医从军呢。
——啊,随他去吧!勃克·穆利根说。
——下周就该受熬煎了。你认识卡莱尔家那个红毛丫头莉莉吗?
——认得。
——昨天晚上跟他在码头上调情来着。她爸爸阔得流油。
——她够劲儿吗?
——这,你最好去问西摩。
——西摩,一个嗜血的军官,勃克·穆利根说。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脱下长裤站起来,说了句老生常谈:
——红毛女人浪起来赛过山羊。
他惊愕地住了口,并摸了摸随风呼扇着的衬衫里面的肋部。
——我的第十二根肋骨没有啦,他大声说。我是超人[139]。没有牙齿的金赤和我。是超人。
他扭着身子脱下衬衫,把它甩在背后那堆衣服上。
——玛拉基,你在这儿下来吗?
——嗯。给我在床上让开点儿地方吧。
年轻人在水里猛地向后退去,伸长胳膊利利索索地划了两下,就游到湾汊中部。海恩斯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着烟。
——你不下水吗?勃克·穆利根问道。
——待会儿再说,海恩斯说,刚吃完早饭可不行。
斯蒂芬掉过身去。
——穆利根,我要走啦,他说。
——金赤,给咱那把钥匙,勃克·穆利根说,好把我的内衣压平。
斯蒂芬递给了他钥匙。勃克·穆利根将它撂在自己那堆衣服上。
——还要两便士,他说,好喝上一品脱。就丢在那儿吧。
斯蒂芬又在那软塌塌的堆儿上丢下两个便士。不是穿,就是脱。勃克·穆利根直直地站着,将双手在胸前握在一起,庄严地说:
——偷自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140]。琐罗亚斯德如是说[141]。
他那肥胖的身躯跳进水去。
——回头见,海恩斯回头望着攀登小径的斯蒂芬说,爱尔兰人的粗犷使他露出笑容。
公牛的角,马的蹄子,撒克逊人的微笑[142]。
——在“船记”酒馆,勃克·穆利根嚷道。十二点半。
——好吧,斯蒂芬说。
他沿着那蜿蜒的坡道走去。
饰以百合的光明的
司铎群来伴尔,
极乐圣童贞之群[143]……
壁龛里是神父的一圈灰色光晕,他正在那儿细心地穿上衣服[144]。今晚我不在这儿过夜。家也归不得。
拖得长长的、甜甜的声音从海上呼唤着他。拐弯的时候,他摆了摆手,又呼唤了。一个柔滑、褐色的头,海豹的,远远地在水面上,滚圆的。
篡夺者[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