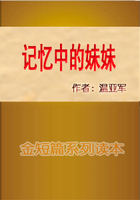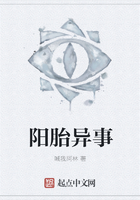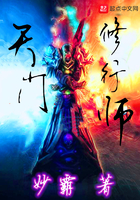这是一部自选集,在学术上说不上有多大的价值,但这却是我的人生记录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曾担任过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杂志社主编,2004年被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这些工作经历使得我与新时期红学发展的许多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的一些文章、讲话以及接受的采访等,对了解新时期红学的发展,或许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7月冯其庸先生把我从文化部办公厅调到了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1980年经国务院编办的批准,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2012年6月退休,我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艺术研究院。我整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了33年。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33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在那次宣布我退休的大会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感激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我的培养,正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把我从一个无知小子培养成一个学者。”的确,我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有着深深的感情和感激。记得我曾多次对年轻的同事们说过当初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时的心情,那时能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无疑是感到极大的幸运,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我们的心中是最高的艺术研究学府,有那么多的大师,如张庚、王朝闻、杨荫浏、吴晓邦、郭汉城、缪天瑞、葛一虹、陆梅林、郑雪莱、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李少白……在这样一个大师和著名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能参与其中就已经是荣幸之至了,那里还会想到以后能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那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才真正是全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能成为全国最权威的艺术研究机构,正是由这些大师们为我们奠基和建设起来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是冯其庸先生一手创建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有红楼梦研究所让人感到很特别,但它无疑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张“名片”。“红学”的独特性与魅力是毋庸置疑的,而红楼梦研究所在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本身就是红学新时期的重要产物。当时的红楼梦研究所在冯其庸先生的带领下,集中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他们是吕启祥、胡文彬、林冠夫、陶建基、徐贻庭、顾平旦、邓庆佑、丁伟忠、杜景华、王湜华等等。红楼梦研究所创办了中国大陆红学史上第一个《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历时七年完成了《红楼梦》新的校注本、出版了《红楼梦大辞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促进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
我生之也晚,没有参加上197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红楼梦学刊创刊的编委会,也没有参加1980年7月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宣布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这成为我人生极大的遗憾。红楼梦学刊创刊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无疑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里程碑与重要标志,而这些都离不开冯其庸先生和红楼梦研究所。虽然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两次在新时期红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但我还是幸运的,在冯其庸和胡文彬等先生的关照和提携下,我几乎参加1981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所有的重要的红学活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经历了红学新时期的全过程。记得1981年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那次大会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大会的主题是《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今天的人们似乎对这样的主题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可在当年,一次《红楼梦》的学术研讨会,以研究《红楼梦》的艺术为主题,则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说起来更有趣的是,那次大会筹备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的组成,也是颇有些“历史意义”的,主要工作人员有四个人:袁世硕、刘世德、胡文彬、张庆善。现在袁老师、刘老师都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胡先生也过了古稀之年,他们如今都是享誉海内外的红学大家,我也过了耳顺之年,想起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冯其庸、李希凡两位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关照和提携,两位先生即是德高望重的师长,又是我多年的老领导,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教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1979年冯老把我调到红楼梦研究所时,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三十多年来我得到他的许多教诲,这是很大的幸运。冯老是第一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我是第二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老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第二任会长(吴组缃先生是第一任会长),我则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第三任会长。而实际上,当时接替冯老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的人选有好几位,他们比我更有资历、更有能力、更有学问,更适合担任会长,但由于年龄的原因,更由于冯老等前辈学者出于对年轻人的培养考虑,而选择了我。虽然当时我也并不年轻了,但还是诚惶诚恐,对冯老等前辈学者的提携和厚爱心存感念感恩之心。我也深知前辈们的期待和心愿,虽然限于能力和水平,我这个会长干的不怎么样,但我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努力着。我是把推动红学事业发展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来做的。
影响我走上红学之路的还有林冠夫先生、吕启祥先生、胡文彬先生和我大学的老师应必诚先生。说起来惭愧,我是上大学以后才开始读《红楼梦》的,指导老师就是应必诚先生。巧的是应老师后来也来北京到红楼梦校注组了。我能从事《红楼梦》研究、能调到红楼梦研究所,都是因为有了这些机缘,这真是命运使然。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感谢的人很多,与人为善一直是我做人的准则。我的父母没有文化,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们一辈子都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与教育,还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为人要善良,要本分、要懂得感恩。父母之恩,我们是永远无法报答的了,尤其是自己的年纪也很大了以后,更是怀念父母,感念不已。就是对帮助我有恩于我的师长朋友,我们的报答感谢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心里有感恩之心,这是最重要的。
这本小书取名《惠新集》,没有多少的讲究,也没有谐音“会心”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最近十几年我一直住在“惠新北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宿舍楼,而对更多的人来讲,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就是“惠新里”。说起来十分惭愧,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竟不知道“惠新里”这个名字的来历。据我所知,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叫“惠新里”。编这本集子的时候,偶然查了查“惠新里”名称的由来,感到很有意思。原来我们这里早年间是元大都北墙外的一片荒地,人烟稀少,清代时形成村落,因附近曾有过一座慧忠庵(早已废弃),故称为“慧忠庵村”。后来建新区的时候,想到古时“慧”与“惠”通用,又因是新建小区,故称“惠新里”。这个名字起的真好,是很有文化意蕴的。
我1975年到北京工作,至今整整40年,前二十多年住在和平里,后十几年住在惠新里,这两个地方都很好,名字也都很好听,巧的是都有一个“里”。而惠新里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不仅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在这里写出的,而我人生中的大喜大悲,也都离不开“惠新里”。取名《惠新集》,仅是为了纪念这段生活经历,为人生留下一点痕迹。
是为序!
2015年9月22日于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