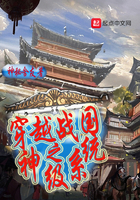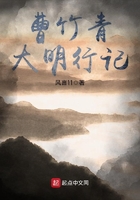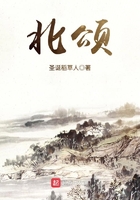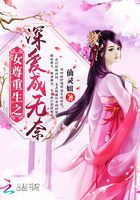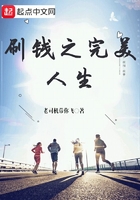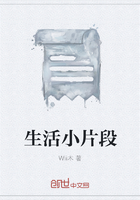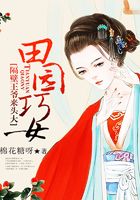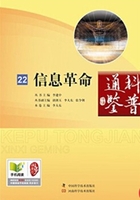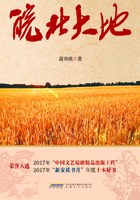——甲寅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及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今刘议调各上司马步兵丁通计二万有奇,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然其中有不得不裁者,如……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参将吴文杰等分统之,星夜兼程赴辽,一切安家行粮,或借支本处堪动银两,或那给解京钱粮庶于危镇有济。”(《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
这是兵部尚书黄嘉善给万历皇帝上的一份奏疏,主要是在萨尔浒大战前明、金双方实力的对比,其中对明兵力的集结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努尔哈赤的过激行为让百病缠身的万历怎么也坐不住了。
在万历看来,辽东丧师失地,明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他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摧毁后金军事实力。他在朝堂上发话说:“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万历郑重交代兵部、户部等大臣:“内帑空虚,尔部便将马价等银照数给发,户部应发饷银亦着尽力措处,文武官务殚心协谋,共图捍圉,恢复事完,分别赏罚,如有疏虞,必罪不宥,其大举征剿事还着九卿科道会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九卿科道会议的结果是:荐举杨镐为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
杨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大家推举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军事人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好理解,但为什么要求他是文人呢?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实行以文制武的制度,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的确,相对武将而言,文臣对帝王的统治所构成的威胁比较小。明承宋制,为了加强君权,就重用文臣,通过财权、人事权、兵马调拨权等等打压武将势力,控制军权,从而更稳定自身的权力。
明朝初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大都督,鉴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后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统兵作战,与掌管军事行政事务的兵部形成相互制约的作用。兵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发令调兵,统兵权则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多为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随之取消。
到了明朝后期,五军都督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地区发生了重大战事,就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军集结组成征讨大军。由于每路总兵率领的本辖区兵力有限(一般在数千到一万人之间),且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又各有不同,就需要兵部官员出马,担任大军统帅——明末的经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准确地说,明朝经略一职就出自万历援朝之役,由兵部侍郎之类的文官出外担任。而既为文官出身,真正通晓兵事的人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
杨镐的确是个人才。比如说,他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
著名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先生赞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足见杨镐在抗日援朝战争中居功至伟。朝鲜人也因此将杨镐视为民族大救星。
继稷山大捷之后,杨镐乘胜再战,拟将日军主力围歼于蔚山。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接连的十数日暴雨使日军躲过了一劫,明军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功败垂成,未能使战果进一步扩大,反被日军所败。
按理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可是,杨镐却因此遭到了朝内大臣的激烈弹劾,指责他“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明神宗实录》),最后落了个革职撤回的下场。这事儿发生在言官大行其事的明朝并不奇怪,试想想,以李成梁纵横辽东二十年的赫赫声威,尚且不免被弹劾回朝,杨镐被弹,就见怪不怪了。
杨镐回国之日,朝鲜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牵衣拦道,一送再送,直出郊外,大臣纷纷赠诗为别。(详见《再造藩邦志》卷五)
这还不算,朝鲜国王此后还多次上疏万历为杨镐鸣不平,并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悬于祠内,供奉杨镐画像。(见《李朝实录》)
杨镐在朝鲜既如此深得人心,朝廷此番启用他出征辽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想借他的影响力得到朝鲜方面的策应。
万历还专门给朝鲜国王下了一道敕谕,要朝鲜“奉大帅之檄文,集陪臣之谋议;借兵一万以上,赋马七百有奇;遣间谍以侦虏情,购焰焇以饬火器”。(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
而此时大明驻守辽东的守军,总计约有两万余人。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明朝廷必须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
除了由杨镐全面负责辽东外,万历还任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原总兵杜松负责驻守山海关,原四川总兵刘、蓟镇总兵王国栋、副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随时候命。
万历明确要求各级官兵亟图战守长策,各处城堡要用心防守,遇到敌人,并力截杀,务挫狂锋,等援兵一到,即合谋大张挞伐,以振国威。事情平息后一起升赏,贻误军机,决不宽贷。
杨镐到了辽东,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
杨镐虽是书生出身,可通晓军事,深谙兵凶战危,并未草率采取行动,而是聚积粮草,集结军队,收集难民,振作士气。
为了打好这一仗,他还派人到建州找努尔哈赤和谈,迷惑对手。
他要努尔哈赤交还所掳走的辽东人口,主动向朝廷认错,称若如此或许朝廷可既往不咎。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努尔哈赤既已气势汹汹地宣布了“七大恨”,撕破脸皮和明朝廷对着干,认错肯定是不可能了,但你要说他是要入关灭了明自己做皇帝,那又未免太抬举他了。他的兵力不过六七万人,所据不过一隅之地,要灭了大明,连梦都没做过。那么,他要的是什么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态度,同时也是为了赢取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二十二日,率军由鸦鹘关进兵,攻陷由明军镇守的清河堡(今辽宁本溪清河城乡),将清河万余军民屠了个精光。九月初四,又派兵将抚顺东北的会安堡屠戮洗劫得鸡犬不留。
他将三百名平民押到抚顺关,斩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一个人,割了他的双耳,让他给杨镐带话:挑起战争的责任全在明政府,如果不服气,可以约定日期决战;如果想息事宁人,就必须封我为王,将原来我的抚顺敕书五百道、开原敕书一千道,全部分给我的兵将。还有,给我绸缎三千匹,白银三千两,黄金三百两。“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
看,这才是努尔哈赤真正想要的。
看来,不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酋长是不行了。万历诏赐杨镐尚方宝剑,责令他抓紧时间和努尔哈赤对练,犁庭扫穴,让努尔哈赤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
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已经完成了集结。
其中,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则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而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全部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
此外,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包括后勤、运输等等,号称四十七万。
由于四方调兵,辽东军饷随即骤增三百万两,于是循当年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劳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催促杨镐抓紧行动。
杨镐通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玉庭等人商议,定于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
杨镐大会诸将,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分进合击。
杨镐这个做法,也许会有人存在疑问,觉得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两万五千人,而努尔哈赤有六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怎么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算,还指挥官呢,狗屁!
事实上,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明军调自四面八方,除了九边重镇(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个军镇,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中的辽东、延绥、宁夏等镇以及四川和浙江外,其他各地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他们来自不同军区,互不隶属,无法将他们在短时间内磨合在一起,权衡之下,分头并进当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分进”并不等于分散兵力,而是一个兵力集结的过程,“合击”才是关键,各路明军分头前进,努尔哈赤无法判断哪支部队是主力,就不敢轻举妄动,如若其贸然出击,就会置后方于不顾,随时有被端掉的危险,可谓防不胜防。这样,“分进”的风险就相对降低,而各“分进”的部队一旦到达指定地点,仍然在“合击”敌人时持有兵力上的优势。
相对而言,集中兵力以一路人马开进,则努尔哈赤可以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对明军进行伏击和骚扰,本来,明军在林海雪原中与占据地利的敌人展开野战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明军从辽沈发兵攻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需要纵深两百多里进入后金腹地作战,沿路又多是山川峡谷,河流林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合兵后的军需辎重过于庞大不说,地形又不熟悉,一旦陷于险地,缺少了前后左右的呼应,搞不好会全军覆没。
所以,明军的口号是:“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七册)
这四路军分别是:
左翼北路军由开原总兵官马林率领,共一万五千人,会同叶赫部的一万三千人出三岔口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左翼中路军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从沈阳渡浑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击赫图阿拉。右翼中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从清河城出鸦鹘关,从南面袭击赫图阿拉。右翼南路军由辽阳总兵刘率领,会合朝鲜兵,共二万三千人,出宽甸,从东南攻向赫图阿拉。
另外,杨镐还派出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与阻击和努尔哈赤关系密切的蒙古军队;又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率兵驻辽阳,为机动兵力;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自己坐镇沈阳,直接指挥四路大军。
二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雪,行军困难。杨镐不得不将出发时间改为二十五日。二十五日,雪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
要不要再等等呢?
山海关总兵杜松就提出,现在大雪迷路,不如延期发兵。辽阳总兵刘也表示,我军对地形还不熟悉,还是缓一缓再发兵为好。
可是,不能再等了。
大军已齐集于辽东,且不说朝内一催再催,而一旦延期,军饷粮食接济不上,就会影响士气,对战事不利。而且,现在是三月初春,经过漫长冬季的空耗,物资向来匮乏的东北女真部落也承受着巨大的后勤压力。再者,因为下雪,出兵的日子已经推了又推,现在还在下雪,敌人疏于防守,突然发兵,正好攻其不备,一举破城。
兵者,诡道也。
用兵之术,在于虚实变幻,神鬼莫测。更何况,为了麻痹对方,杨镐原先还遣后金逃卒赍书努尔哈赤,佯称:“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四十七万大军,当是泰山压顶之势,先从心理上给努尔哈赤以强大震慑力,让其心生畏惧,不敢出击,一味坚守赫图阿拉。这样就更利于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形成合围赫图阿拉的局面。故意将发兵日期说成十几日之后,是为了迷惑对方,让其在信与不信之间犹豫,摸不着头脑。而现在,如果把出兵的日期再往后推,真成了三月十五日出兵,到时不免弄巧成拙,反被敌军所制。
于是,杨镐宣布:“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把皇上钦赐的尚方剑挂于军门,以警告还想劝阻延期出兵者。
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兵。
杨镐再请尚方剑,宣读十四款“罚约”,将抚顺临阵逃将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附十四条“罚约”:
——各路信地,距奴贼(指努尔哈赤)城寨计道途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本路虽杀贼收兵,见别路为贼所乘,不即救援者,明系观望,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
——主将与将领、千把总及军士,或有私仇于阵中,乘机陷害者,审实处斩。
——官军临阵退缩不前者,登时立斩。
——马步兵前队以冲锋陷阵破敌为功,不许割级,俟贼败走之后,方许后队割级,验功之时,前后三七分赏。如贼未败,而争先割级、来抢级者皆斩。
——临阵私逃及诈称病规免者斩。
——营中蓄藏妇女者斩。
——营中不加紧严防,致失火延烧火药粮草者斩。
——杀中国(指明朝)被掳人民报功者斩。
——滥杀投降夷人及老幼妇女充功者斩。
——争夺高丽(指朝鲜)及北关(叶赫)所获首级者斩。
——攻克贼寨争抢财物致有失机者斩,仍罪及本路将领。
——俘获贼属子女及被掳汉人妇女隐匿不报者斩。
——督运及护粮草官违误军兴者斩。(《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