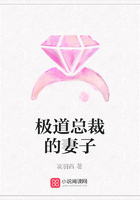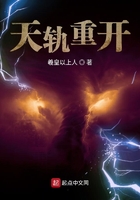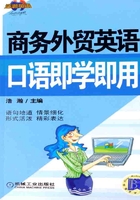据《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的记载可知,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周扬曾经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到毛泽东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应该说,周扬此时的检讨起码在表面上还是非常虔诚的,但一些主要的原因他却不能说出,比如他对江青在文艺界的指手画脚十分反感,自己对她的“假传圣旨”也必须进行抵制等等,他只能用“没有警觉”等理由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扬这次与江青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但出于种种考虑自然也不便点破。在听了周扬的检讨之后,毛泽东针对他的辩解,上纲上线并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出自毛泽东之口,周扬自然诚惶诚恐无地自容。但毛泽东犹不放过,又严厉地批评周扬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想起当日周扬强调的“小人物的文章”这条理由,毛泽东明确告诫说:“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再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一直没有受到批判:“如果不批判,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的。”
周扬作了深刻而又彻底的检讨之后,学习古代贤哲使用攻心战术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亲解其缚”,而是继续冷落了周扬一段时间。直到11月下旬,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后,才允许周扬掉转了他的命运之舟。
此时,大批判的熊熊烈火已然燃遍了神州大地,新闻媒体在行动上也取得了空前一致的大好局面。
然而,虽然此时毛泽东原谅并依然重用了周扬,但最可怕的却是江青对他的仇视态度仍然一如既往。她要彻底地整垮这位“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以便使自己成为“文艺界的旗手”或登上“文艺女皇”的宝座。12年后,当周扬被批倒批臭且被关进秦城监狱之时,他与江青的这次冲突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大罪状。197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仍然抓住周扬当年反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大批特批,可见江青在与周扬的这次冲突中对他结下了多么大的仇怨!只不过在此时的批判文章中,却又在周扬的前面拉上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更大的“大人物”——刘少奇。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随意性以及御用文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
三、引发批判运动的第三偶然性因素:“替罪羊”冯雪峰也是“罪有应得”
本来,如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能够顺利地在《人民日报》转载,这场批判运动也就不会与冯雪峰及《文艺报》发生任何关系。岂料周扬却要“多事”,阻止了江青的意图并大搞折中在《文艺报》转载,这便给冯雪峰及《文艺报》种下了一颗要结苦果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雪峰与《文艺报》都是地地道道的“替罪羊”,但由于冯雪峰本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又在惹恼了江青的同时也激怒了毛泽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罪有应得”的。
毛泽东与冯雪峰,本来曾有过深厚的交情和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后来对冯雪峰产生了反感呢?近年来,学术界许多人都在试图探讨其中的奥秘,但却都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实际上,只要我们将他们之间的交往史略微缕述一下,就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冯雪峰自己回忆说:“还在国内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工作的毛泽东曾向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我的同乡(同学)打听我的下落,说他很喜欢《湖畔》诗,认为写得很好,要我去南方与他一起工作。以诗会友,可见他的诗人气质。”[8]激赏白话文运动但却并不喜欢白话诗的毛泽东,居然破例地说自己“很喜欢《湖畔》诗”,可见相对于形式而言毛泽东更注重诗的内容和情感,更注重充溢于诗文中的人的个性和品质;由此亦可看出,冯雪峰的“湖畔诗”具有多么强的感染力。然而,此时的毛泽东与冯雪峰,也只是一种所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神交,自然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他们彼此谋面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是在冯雪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以后,尤其是在瑞金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和副校长期间,冯雪峰居然有了经常与毛泽东在一起秉烛夜谈的机会,二人甚至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9]后来,在同甘苦共患难的长征途中,冯雪峰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友谊也日渐加深。随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冯雪峰在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敬仰之情的同时,毛泽东自然也加深了对冯雪峰的信任和倚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便很快对冯雪峰委以重任——让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当然,这项使命之所以落到冯雪峰头上,并不仅仅考虑到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冯雪峰当年曾在上海工作过,熟悉上海的情况且与鲁迅关系密切,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冯雪峰离开陕北前往上海,本来是代表中共中央行使神圣的使命,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南行,却对他晚年的悲剧人生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当然,倘若仅仅与周扬等人闹矛盾,也不至于对他的未来造成多大影响。最致命的是他在此期间,因与博古闹翻而赌气跑回家乡隐居。对冯雪峰的这一举动,毛泽东有何看法因缺乏史料不得而知,但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却对冯雪峰此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了?不干共产党吗?”[10]这虽然是潘汉年的个人意见,却很能代表中共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对冯雪峰此举的看法。如果从大局出发来说,无论上面的决定是对是错,冯雪峰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撂挑子不干的行为却是万万要不得的。在这次事件中,他那典型的“浙东人的脾气”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冯雪峰的人生悲剧,既有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的性格的因素。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安排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对文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国家第一个大型文学出版社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问题上,是否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不得而知。周恩来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也许已经同毛泽东商量过了。即使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毛泽东此时反感冯雪峰,那么在周恩来做出这一安排之后,毛泽东也许会表示自己的看法。后来,冯雪峰又兼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文艺报》主编等职,毛泽东依然默认了这种安排。然而,就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爆发前不久,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及《人民日报》曾以“李准事件”为由,对《文艺报》发动了一次围攻式的批评,致使《文艺报》不得不做公开的检讨。此事的背景究竟如何,因无确凿的史料,不敢妄加揣测,但对冯雪峰来说,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平心而论,此时的毛泽东对冯雪峰冷漠也好不满也罢,却还说不上有什么反感,后来发展到必欲将之批倒批臭的程度,却与那位喜欢多管闲事的“第一夫人”江青息息相关。
江青第一次到人民日报社要求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究竟对邓拓说了些什么冯雪峰可能不太清楚,但当她的意图遭到周扬抵制并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进行交涉时,冯雪峰就已经明白了江青要“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这个讨论的实质”。“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这是江青一再强调的主要理由。而此时的周扬,却已经拿定主意在《文艺报》转载这篇“并不成熟的文章”,所以他在请来林默涵、何其芳等盟友为自己助战的同时,还特意请来了冯雪峰。在这次特殊的谈判会上,当然还是由周扬来唱主角,邓拓、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则附和着周扬打帮腔,而冯雪峰却没有直接表态。然而,他说不说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江青说了些什么、周扬说了些什么,冯雪峰又该按照谁的意见办!在江青与周扬之间这次面对面的冲突中,争强好胜的江青强忍怒气做了让步,结果最终同意由《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这一折中方案的达成,看似化解了双方的矛盾,实际上二人之间最主要的矛盾焦点尚未解决:周扬之所以坚持要在《文艺报》转载,是因为他觉得这一问题“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好”;而江青则仍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的转载引起争论,从而“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因为当时守着周扬等人,也许江青没有再对冯雪峰强调自己的意见,但事后她不可能不再来过问此事。而在交涉会上没有表态的冯雪峰究竟服从周扬的安排还是认同江青的意见,在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了他自己的命运。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江青找冯雪峰过问此事的直接证据,但从史索、万家骥的《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条史料: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恂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文艺报》,对他指手划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我们无法核实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以理度之,当是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爆发之前。不然的话,已然陷入困境的冯雪峰,即使“浙东人的脾气”再大,也绝对不敢再这样跟江青说话。那么,此事是否发生在1954年9月下旬呢?愚以为这是极有可能的。江青之所以“过问《文艺报》”,应该还是为了那篇令她青眼有加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转载问题。她对冯雪峰“指手划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当然除了版面安排方面的“这样”“那样”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编者按”应该如何写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冯雪峰居然“那样”“毫不客气地”对江青说出“你不懂的事,别多管”“这样”的话来,又按照自己及周扬的意见写出“那样”一个“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的“编者按”来,他的这种做法,若不激怒江青,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周扬与江青的这次冲突中,冯雪峰显然倒向了周扬一边。当然,冯雪峰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之所以倾向于周扬,乃是因为他也觉得这一问题“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好”,他在“编者按”中只说“科学的观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而不说“马克思主义观点”或“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便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将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尽管他陪了十二分的小心,既征求过李希凡、蓝翎的意见,又特意报请中宣部审批。但在批判运动爆发之后,他们这些人,却都无力使冯雪峰摆脱风暴的袭击。
退一步说,即使江青“过问《文艺报》”不是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转载问题,那么,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爆发之前,冯雪峰对江青采取这样的态度,也必然会让江青窝火,待到他写的那个“编者按”公开发表之后,江青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必然将埋在心头的积怨随同新仇一并发出,让冯雪峰饱尝“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实际是不听从她江青指示的苦头。因此,1954年10月下旬,“《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甫一爆发,冯雪峰便即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表面看来他是在为周扬“替罪”,但在毛泽东和江青眼里,他却也是“罪有应得”的。
在此需要申明一点,毛泽东与江青对待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太相同的。江青可能只是在野心难以实现的前提下,纯粹从私人间的恩怨着想假公济私以泄私愤;而毛泽东则更多的是从大局着眼。通过这次周扬、邓拓、冯雪峰等人的表现,他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文艺界的不听指挥及思想混乱,并由此勾起了他对文艺界尤其是文艺界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们的不满情绪,因而他要借助这次运动的开展,用马列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在运动展开之先,不集中力量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却首先冲着《文艺报》大动干戈,便可证明毛泽东就是要借批判《文艺报》之举,对新闻媒体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而其最终目的,当然还是要为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开展铺平道路。
弄清楚了以上事实,也就明白了“《红楼梦》事件”爆发的另一个真正原因,同时也找到了毛泽东为何会对冯雪峰产生反感的具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