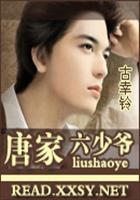确定了没有人跟踪我以后,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单独走下铁楼梯到地下库里去。走几步就用哄人的口气向前轻喊一声:“玛丽·凯塞琳,是我瓦尔特,是瓦尔特来了。”
我的脚上穿什么?我穿着一双黑漆皮鞋,鞋面上还有一只小小的蝴蝶结。这是阿尔巴德·李恩的十岁儿子小德克斯特给我的,正好是我的尺寸。德克斯特原来在舞蹈学校学舞蹈必须买这种鞋子,如今没有用处了。他第一次向他的父母提交最后通牒获得成功,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他进舞蹈学校他就自杀。他居然这么嫌恶舞蹈学校。
他真是个好孩子——在客厅游泳池里游过泳后穿着一套睡衣裤,外罩浴袍。他对我很关心,很同情,这个小老头儿的小脚上竟没有鞋子穿。我仿佛是童话里的一个小矮子,他是个小王子,把一双魔术的舞鞋送给了小矮子。
他长得真漂亮,棕色眼睛大大的,一头卷卷的黑色浓发。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儿子我什么都舍得。可是我想,我自己的儿子会给阿尔巴德·李恩那样的父亲带来不少痛苦。
天公地道。
“我是瓦尔特,玛丽·凯塞琳,”我又喊道,“瓦尔特来了。”到阶梯底下,我看到了头一个迹象,说明事情可能不妙。一只布鲁明代尔大百货公司的购货袋横躺在那里,袋子里乱七八糟的破布、一只洋娃娃的脑袋、一本《时装》杂志(那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出版物)都被倒了出来。
我把购货袋扶直了,把东西塞进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地板上有一摊血,那是我无法放回去的东西。越向前,血越多。
我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目的地故作惊人之笔,要读者震颤一下,以为我接着就发现玛丽·凯塞琳双手给砍掉了,举着血淋淋的断臂向我求救。实际上是她在范德皮尔特大道被“柴克”出租汽车撞了一下,她不愿进医院治疗,说她一切很好。
但是她一点也不好。
这很可能是一件有讽刺意义的事,但我无法证实——很有可能玛丽·凯塞琳是被她自己旗下的某辆出租汽车撞的。
她的鼻子撞破了,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还有更糟糕的事,我无法一一列举。玛丽·凯塞琳身上还撞破什么,撞断什么,都还没有检查统计。
她躲在一间厕所里,是一滴滴血迹把我引到那里的。谁在里面,毫无疑问,因为门下可以看见她的篮球鞋。
至少里面不是一具尸体。我轻轻报上自己的名字,表明和善的来意以后,她拉开了门闩,把门打开。她没有用马桶,只是坐在上面。她的样子就像在用马桶一样,十分狼狈,生活给她的羞辱已达到了顶点。她的鼻血已止住了,留下了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的一撇小胡子。
“唉!可怜的女人!”我叫道。
她对自己的状况一点都不在意。“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说,“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母亲是死于镭锭中毒的。
“你发生什么意外啦?”我问。
她告诉我被出租汽车撞了的事。她刚刚发了一封信给阿尔巴德·李恩,在电话上确认了她给他的一切指示。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我说。
“不,不,”她说,“待在这里,待在这里。”
“可是你需要帮助!”我说。
“我已不需要了。”她说。
“你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我说。
“我快要死了,瓦尔特,”她说,“知道这个就够了。”
“只要有一口气,就有希望。”我说,准备跑上楼去。
“你千万别把我再丢下不顾!”她说。
“我是要救你的命!”我说。
“你得先听我说了要说的话!”她说。“我一直坐在这里想:‘我的上帝,我经过这许多磨难,做了这许多工作,却没有一个人来听一听我要说的最后几句话。’你去叫一辆救护车,就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听到我的话了。”
“我可以让你舒服一些吗?”我说。
“我很舒服。”她说。这话有些道理,她那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可以为她保暖。她小小的脑袋靠在厕所一角的墙上,用一只破布枕头垫在铁架上。
其间我们头顶上的岩石不时发出隆隆声。上面如果有什么别的东西快要死了,那就是美国的铁路系统。残破的机车拉着残破的客车进出着车站。
“我知道了你的秘密。”我说。
“哪一个秘密?”她说,“我现在有不少秘密。”
我原来以为,在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拉姆杰克集团的大股东老板的时候,会出现戏剧性场面。结果当然是一场空。她早已告诉了我,我自己没有好好听。
“你的耳朵聋了吗,瓦尔特?”她说。
“我现在听得很好。”我说。
“难道你要我把最后的话大声嚷嚷给你听吗?”
“不,”我说,“但是我不要你再说什么最后的话这种话了。你有钱,玛丽·凯塞琳!你如果愿意,可以把整个医院都拿过来,叫他们把你治好!”
“这种生活我恨死了,”她说,“我已尽了我的努力,让大家过得好一些,也许谁都没有太大的办法。我已试够了,我现在要长眠了。”
“但是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生活!”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我会保护你的,玛丽·凯塞琳。我们可以雇用能够绝对信任的人。霍华德·休斯雇用了摩门教徒——因为他们讲道德,我们也可以雇用摩门教徒。”
“唉,上帝,瓦尔特,”她说,“你以为我没有用过摩门教徒?”
“你用过?”我问。
“我有一阵子用的全是摩门教徒。”她说,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恐怖故事。
那是她还生活得很奢侈的时候,她仍想要小小地享受一下她巨额的财富。她是个许多人要拍照,绑架,想方设法折磨或者杀死的对象。有人想杀死她,要她的手或她的钱,也是为了要报复。拉姆杰克集团侵占了或者毁掉了许多企业,甚至在推翻一些弱小国家的政府上也插了一手。
因此除了对那些忠实的摩门教徒以外,她对谁都不能泄露她的真实身份,而且她不得不停地以移动。有一次她住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1]一家拉姆杰克集团旗下酒店的顶层。这一层有二十套豪华房间,她都租了下来。从下面一层上来的两个楼梯口都用砖块给砌死了,就像阿拉巴霍酒店门厅里的拱门一样。只有一部电梯可以开到顶层,那部电梯由摩门教徒掌管。
甚至连旅馆经理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是肯定可以说,马纳瓜人人都推测到了她是谁。
尽管这样,有一天她还是轻率地决定要独自一个人到城里去逛逛,不论时间多短,也要尝尝她多年没有尝到的在世界上做一个普通人的滋味。因此她就戴了假发和墨镜出去了。
她看见一个中年的美国妇女坐在公园里的板凳上哭泣,就同她攀谈起来。那个妇女是从圣路易斯来的,她的丈夫是拉姆杰克集团安豪塞-布什啤酒[2]分部的酿酒师。她们听了一家旅游公司的建议到尼加拉瓜来度蜜月,但她的丈夫不幸在那天早上患恶性痢疾死了。
因此玛丽·凯塞琳把她带回旅馆,让她住在无人住的一间套房里,叫手下的摩门教徒设法用一架拉姆杰克集团的飞机把尸体和寡妇送回圣路易市。
玛丽·凯塞琳吩咐完了以后到那个妇女那里去把一切安排告诉她时,发现那个妇女已被窗帘绳子勒死了。不过真正可怕的是凶手,不论是谁,显然认为这个妇女就是玛丽·凯塞琳。因为她的手给砍去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这事情发生以后,玛丽·凯塞琳马上回了纽约。她开始从华道夫大酒店塔楼上的套房中,用望远镜观察提购货袋的叫花婆。附带说一句,三军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住在她上面一层。
她从此不出门,不见客,不找人。酒店的人也不让进,由摩门教徒从楼下送吃的来,给她铺床,收拾房间。可是有一天她还是接到了一封恐吓信,一只粉红色的洒过香水的信封放在她的内衣上。信中说,写信的人知道她是谁,要她对危地马拉合法政府被推翻负责。他要把整个旅馆炸掉。
玛丽·凯塞琳吃不消了,她丢下摩门教徒出走了,他们毫无疑问是忠实的,但也无法保护她。她开始用垃圾筒里找来的衣服一层又一层地包起身子来保护自己。
“要是你的钱使你这样不快活,”我说,“你为什么不捐掉?”
“我是要捐掉的!”她说,“我死后,你看一看我的左脚鞋子,瓦尔特。你会发现我的遗嘱在里面。我把拉姆杰克集团还给合法的主人,美国人民。”她笑了。看到这样幸福的微笑用只剩下一二老牙的牙龈展露出来,我心里感觉非常凄惨。
我以为她已死了,她还没有死。
“玛丽·凯塞琳?”我说。
“我还没有死呢。”她说。
“我现在得去找人了。”我说。
“你去的话,我就会死的。”她说,“这一点我现在是敢说的,我现在要死就能死,我可以自己选择时间。”
“这是谁都做不到的。”我说。
“叫花婆能做到,”她说,“这是我们的特殊功能。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死,我们说不好,但是一旦开始死,瓦尔特,我们就能选择确切的时间。你是不是愿意我马上就死,从一数到十?”
“别马上就死,千万可别死。”我说。
“那么就待在这里。”她说。
我就待在那里。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要谢谢你搂了我。”她说。
“什么时候都可以。”我说。
“一天一次足够了,”她说,“今天已搂过了。”
“你是我第一个真正做过爱的女人,”我说,“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拥抱,”她说,“我记得你说你爱我。在那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话。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很多这样的话——那是她死之前。”
我又开始哭了起来。
“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的。”她说。
“我是真心的,真心的,”我争辩说,“唉,上帝呀,我是真心的。”
“那没有关系,”她说,“你生来没有良心,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至少你想办法相信过有良心的人相信的东西——因此你也是一个好人。”
她停止了呼吸。她闭上了眼睛。她死了。
注释:
[1]马纳瓜(Managua):现译作马那瓜。
[2]安豪塞-布什啤酒(Anheuser-Busch):现译作安海斯-布希。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酿造商之一,拥有全美48.8%的啤酒市场份额,旗下品牌百威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