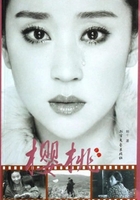场面一时尴尬,菜刀老板笑道:“算我多事,我自罚一杯。”常好给他斟满,结果他连干了三杯。
菜刀老板姓卢,说话算话,第二天真来摆了五桌酒席,请了四五十个出席交流会的客商,还定做了一条红绸横幅,喜气洋洋地拉在店招的上边:“快刀卢——诚谢天下客!”
〇一〇
好妹仔的生意好起来,有时候吃客满座,晚来的人还得靠在泡桐下边等。他们起初是来看成都酷哥的,后来成了回头客,都因为刘建设的鲫鱼可口,辣子鸡喷香。
周末,午后无事,常好就和刘建设商议添几张饭桌,一边感慨,“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郝彪那一刀,你也算没白挨。”
刘建设笑道:“恶事再八卦,也得有人传。你晓得是哪个传的吗?”
“不晓得。未必还是你?”
“说对了,就是我。我要不传,这一刀才真的白挨了。”
常好愣了愣,叹口气:“我应该早些高看一点你。”
刘建设笑道:“还来得及。有人就说过,刘建设是一座富矿,你要是愿意,每天都能挖出新财富。”
常好说:“谁说的?”
刘建设笑道:“我自己啊。”
“你要是废话再少些,你也够酷的。”
“你是要我学郝彪?”
常好却不再答理他,拿眼睛找郝彪。老印趴在桌上睡着了,而门外的泡桐下,孙三正和大妹说得热闹。就郝彪没影子。
郝彪在店后的小院晒太阳。院里有两口倒扣的瓦坛,他坐在一口瓦坛上嗑瓜子,把大搪瓷缸放在另一口瓦坛上。从这儿望出去,一排灰蒙蒙的房屋后,是一块块明黄色的油菜地。阳光下,油菜地就像飞毯正在飞。常好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头。
常好问他:“对这儿习惯不习惯?”
他点头,说:“习惯。”
常好又问:“你真的是杀了人,关进去劳改,又放了出来的?”
他又点头,说:“嗯。”
常好就要他具体讲一讲。
他说:“你都讲完了,没啥好讲的。”
常好哼了一声,说:“你在玩酷?”
他摇头,说:“我不玩酷。”
常好突然发作起来,说:“你打了包走人吧,哪个想看你一张冷脸!”
他依然摇头,说:“我还要赔你的桌子、椅子呢。”
常好说:“赔个屁,你以为真是黄花梨的啊?”
他说:“你们说是,那就是了。”
常好说:“啥子‘你们’,刘建设说的,跟我啥子关系?”
他说:“你们是一拨的。”
常好又气又好笑,把手伸到他眼皮下:“好嘛,我跟他一拨的,你也砍我一刀嘛。”
她的五指犹如刚刮过的竹筷,青青亮亮,指甲上浅浅地涂了粉红油脂,中指还戴了只铂金戒指。郝彪愣愣地看了半晌,抠着头皮嘿嘿地笑:“我不敢。”
常好将手收回去,把额前那一络燕翅似的头发抹了抹。郝彪看见她右眼角果然有个疤,小半个指甲大,嫩红色的,凸起来,有点倔犟和调皮。常好说:“你在看我的伤疤?小时候被我的初恋情敌给咬的。”
郝彪一脸发愣:“咬的?”
常好说:“不是咬,是扎的。”
郝彪说:“持械斗殴啊,还能是刀子?”
常好说:“比刀子狠,是斧子。阿弥陀佛,我命还在。”
郝彪呵呵地笑了:“阿弥陀佛。”又想起那个塑泥塑的人,心里嘀咕,“日怪。”
〇一一
常好让郝彪没事出去转转,看到漂亮妹仔,也可以打个望,别窝得发霉了。
镇上人很少,郝彪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孤单单的。他在干杂店买了一包炒瓜子,嗑着走出镇。下了公路,迎面就是油菜地。油菜地远看还像飞毯,走近发现它们高过人头,茂如密林,藏得下千军万马,微风一过,花瓣就跟金箔一样地飘。香气让郝彪有点头晕。他踩着田埂,向着油菜地的深处走。
起初还能听到几声喇叭,后来就连鸟叫也没了,只有蜂群飞过,抛下嗡——的一团响。四下静得不得了。再走一程,忽然听到有一个小孩在说话,清脆、悦耳,隔了油菜花远远传过来,如在空山幽谷,十分好听,却听不清楚。郝彪听了一会儿,不自觉向那声音靠过去。似乎靠得很近了,但始终隔着一垄油菜花。他躬下身子,犹豫着,是不是要从油菜花中穿过去?就在这时,声音消失了。他竖起耳朵听,只听见流水在寂寂地冲刷着水渠。他发了会儿蒙,突然听见那声音就在身后响起来。
其实已不是说话声,是那孩子在开怀地大笑,就像一只鸽子在扑棱棱地飞!郝彪吃了一惊,赶紧转身,只看见一架自行车载着两个人,呼地从他身前掠了过去,只给他留了个背影。
但郝彪已经看清楚,是一辆老式的、加重的邮车,保留着黯淡的绿漆,横杠下还挂着褪色的邮包。骑车的是一个长发女人,后座上坐了个戴红色棒球帽的小孩,背着书包,手里抱着一口小瓦坛。眨眼间,邮车辗过一段田埂,绕过一垄油菜花,倏地不见了,只有笑声还在花梢上,一跳一跳。
郝彪愣了一愣,寻着田埂走回去。走到岔路口,看见地上落着那小孩的棒球帽。他把帽子捡起来,拍去灰尘,把几根小草拈去,抬起头,正看见那邮车在反身骑回来。车到跟前停下,小孩下了车,女人扶住车。刚才开怀大笑的小孩,这会儿格外地娴静,就像那笑声是另一个人发出的。郝彪做了个递帽的动作——小孩大概七八岁,头发卷卷的、细软的,眉毛也是细细的,眼缝也是细细的,朝郝彪挪了两小步,犹豫着。狭路相逢,这个拿帽子的男人魁梧得让人不安。小孩回头望了一望母亲,母亲温软地一笑,意思说:
“去吧。”
郝彪这才细看了那母亲一眼。这一看,让他心口咚地一敲:他一定在哪儿见过她,如果不是她披着长发,也许差点叫出她的名字了。
她的头发是长长的,浓密但又蓬松,梳向脑后,又乱乱地搭在肩头,再披了些在胸前。她跟常好很不同,胸脯起伏大,肩膀宽,脸颊微黑、丰满,丰满得能见出好看的双下巴。虽然丰满,五官却又像精工细刻的石像,然而,她的微笑、发着微光的汗毛,又把石的坚硬抹去了,只留下了圆熟和细腻。她不看郝彪,头微低着,眼帘微耷着,嘴角漾出些淡淡的笑,似乎在鼓励小孩子:“去吧,谢谢叔叔。”
小孩子又走了一小步。郝彪也走了一步。
“小妹妹。”郝彪友好地招招手。
小孩脸上飞起两块红,但声音却是轻轻脆脆的:“是小弟弟。”
郝彪愣了愣,嘿嘿笑起来。小孩手上捧着小瓦坛,郝彪就亲手把帽子给他戴到了头上,还替他正了正。
“谢谢叔叔。”他又瞟了眼母亲,脸上有欢喜的笑。
邮车又载着这母子俩,在油菜花盛开的田埂上,风一般地骑走了。田埂在浅丘上起伏,那母亲的头偶尔会从油菜花上冒出来,长发飘拂,脸上闪烁着金色的汗粒。郝彪呆呆地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
郝彪走回镇子,感觉少有的疲累,喉咙发干,就在干杂店买了瓶农夫山泉,靠着柜台喝起来。喝完一瓶,又喝了一瓶,肚子微微鼓起来,心里却莫名怅怅的、空空的。卖干杂的老太婆问他:“你就是那个成都人?”他说:“嗯。”老太婆又问:“就是那个拿菜刀砍手背的成都人?”他苦笑了一声,把手伸起来向着阳光晃了晃,感觉自己像个黑手党。他说:“我哪舍得砍。”他又要了一瓶,边喝边走回鲫鱼馆。
走到街巷交叉的丁字口,向里一拐,他一下子收住了脚——
店门外的两棵泡桐下,正停着那辆绿色的旧邮车。
郝彪踌躇了起来,莫名生出些忸怩,不好意思去见这母子俩,似乎他们之间已存了一点儿秘密。可有什么秘密呢?!他在心里呸了自己一口,就大踏了步子向前走,不看那辆邮车,径直走回鲫鱼馆。
刚走到店门口,常好恰好正陪着这母子俩走出来。小男孩叫了声“叔叔”,惊喜得脸都通红了。郝彪略有些不自然,嘿嘿了两声,抹了一把脸,他怕自己的脸也红了。常好有些惊讶:“你们认识的?”郝彪不说话,看了看那母亲。但这母亲也不说话,她看了看郝彪,又看了看常好,嘴角漾起笑意来。笑意使她厚敦敦的双唇弯了一弯,郝彪莫名地觉得被扯痛了一下。
邮车载着这一对母子,又走远了。郝彪发了发愣,端过自己的大搪瓷缸,一口一口地喝茶。
常好再次问他:“你们认识吗?”
郝彪摇头:“不认识。”想了想,他又说,“不认识,可……就像是认识的。”
常好哈哈笑起来:“你晓得她是谁?”
郝彪自然不晓得。
“我说她是我嫂子,你信不信?”
“……我不信。”
“不信就算了。她是缅忆君,她来给我送冬菜。”
“小男孩是你侄儿?”
“是梯梯,梯坎的‘梯’,是她儿子。”
梯梯抱着的那口小瓦坛,现在就放在刘建设的灶台上。郝彪晓得了,这口瓦坛,还有路边无数的瓦坛,就是腌制冬菜的。他不晓得的是,冬菜有多金贵呢,还弄得跟茅台酒似的。
〇一二
打烊后,刘建设用一只木槌,谨慎地在小瓦坛封口上敲了三下。封口是用泥和石灰抹好的,一敲不应,二敲现出裂纹,三敲之后,泥头纷纷地落到桌面上。随后,他把蒙在坛口的最后一层布揭开了。郝彪听到店里所有人都深吸了一口气。他想,日怪,这是做啥呢?这时候,一股馥郁的香气跟虫子似的,钻进他的鼻孔里。他差点要打喷嚏,然而,这香气把他的喷嚏镇住了。无论是小观音带挑衅的香水味,还是油菜花让他发晕的气息,都没冬菜开坛的味道让他觉得这么的安逸。
他问常好:“老板,到底是啥味道呢?”
常好笑道:“就是冬菜的味道嘛。”
刘建设烧鲫鱼时,撒了一把切碎的冬菜。这顿晚饭已经很晚了,后门外传来农家的狗吠。然而,大家都吃得特别有精神。常好拿筷子在郝彪的碗边一敲。郝彪一惊,差点让鱼刺卡了喉咙。她说:“你已经超过我两倍了,十二条。”他不好意思,放了筷子,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常好又问:“晓得冬菜为啥这么香?”郝彪摇头,自然是不晓得。
常好就说:“四川、重庆两地的人都吃冬菜,拿它下饭,跟泡菜、咸菜的意思差不多。只有大足人哈脑壳,做笨活,腌制冬菜下的工夫,比孕妇怀胎儿还要耐得烦。寒露播种,立春收割,拿清水把一张张菜叶洗干净,在花花太阳下晾够十五天,然后抹一层盐,揉一遍,又晾,又抹盐,又揉,又晾……反反复复起码又是十五天,然后卷起来,放进瓦坛,封了口,就放在路边、树下、山坡顶子上,任风吹雨打,1月落雪,7月暴晒,经过整整3年,才‘啵’地一声用槌槌儿敲开。你说啷个不香呢?”
大妹咽口唾沫,像用牙签剔肉一样剔了丁点鱼放到嘴里去。她说:“三年!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也莫过如此嘛。”
常好把刘建设的酒杯拿来咂了一口,笑道:“世上万物,时间越长越金贵,除了女人。”
刘建设说:“道理是对的,可有的女人还是明知故犯的。”
大家一片发笑,孙三说刘建设“替古人担忧”,大妹就骂孙三“啷个敢把好姐姐比古人”。
常好十分委屈,拿指头指着自家鼻子:“那古人是我?”
郝彪弄不懂他们演的什么戏,等他们笑完了,问常好:“你嫂子,是邮递员?”
“我哥哥是邮递员。”
“那她是以腌冬菜为生了?”
“如果她是冬菜国际联营公司的董事长,她是可以冬菜为生的。可惜,她不是。”
“那她是什么?”
“我说她是我嫂子,你又不信……”
郝彪不问了,嗑了几颗瓜子,端起大搪瓷缸喝茶。他如今喝的是老重庆人习惯的沱茶,硬如坚饼,敲一块泡在缸中,一缸水黑洞洞,苦药一般,苦得倒是过瘾,让人心静。
第五节 香会
〇一三
泡桐的花谢了,阔叶刷刷地长出来,几天就盖满了枝头,恍若两棵树都挂满了绿色的大象耳朵。有一天,郝彪惊讶地发现,从早到晚,尘埃飞扬,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停地涌入大足。他们开车来,搭车来,也走着来,有的还扶老携幼,背着背包,提着雨伞和油桶,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路上行程,可见非止一日。旅馆间间客满,“好妹仔”虽新添了几张桌子,但有几十个人在吃,就还有几十个人站着在等。郝彪端盘子、洗碗忙晕了头。累倒不怕,他个子太高,只恨腰杆弯得发酸。
抽个空,横手揩把汗,他问刘建设:“是不是要打仗?”
刘建设替老板高兴,脸都笑烂了:“是打仗的反义词,我们祈祷和平。”
郝彪难得骂了他一声“嘴巴劲”,转脸看着常好。
常好说:“大厨师没乱说,今天是阴历二月十八,观音菩萨明天过生日,周围团转的香客,还有云贵川的施主们,都来宝顶朝山、烧香了。”
郝彪嘿嘿笑起来:“现在就是节多,没节找节,哄人花钱,商场打折。”
常好连呸三口!“说菩萨的怪话,当心烂嘴。上朝峨嵋,下朝宝顶,千年不变的规矩了,偏偏就你一个人不晓得。”
郝彪摇头,喃喃说:“宝顶能跟峨嵋比?宝顶有几个菩萨啊?”
常好看他摇头,一副呆相,也笑起来。“宝顶的菩萨,多得数不清。”
郝彪心口咚地一响,这才想起什么来。“宝顶是不是满山都刻了菩萨像?”
“满山嘛,倒还不至于。宝顶有个大佛湾,马蹄形,三面山崖密密麻麻都是菩萨、佛陀、金刚、护法、太子、孔雀、神仙、阎王……有一万多尊吧,乱七八糟,啥都有。阿弥陀佛!”
郝彪哈了哈腰。“老板,那你今晚不回宝顶烧香啊?”
“当然要烧啊。过了十点,就关店门,统统跟我上宝顶,正好赶上烧子时香。不求发财,但求平安。”
刘建设插话:“我还要多求一点点。”
“多什么?”
“明知故问,我不说。”
郝彪搓着自己的手,踌躇一会儿,木木地问:“观音过生,我去烧香,合适不合适?”
刘建设说:“当然合适啊!你不是杀过人……我是说,你不是砍过我手背吗?更应该去了。放下菜刀,立地成佛,除了宝顶,到哪儿寻这种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