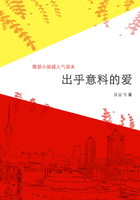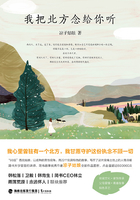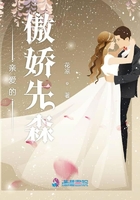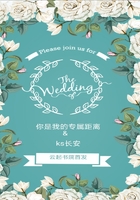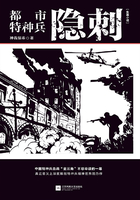这是一部新儒林外史,描写了上世纪末期一群底层小文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社会的抗争。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困难重重。
上部 实话难说
【1、大学毕业了】
这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不再由国家分配工作。农家子弟郑喜成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大槐树村。他不敢白天回家,而是借助夜色的掩护,回到那个位于老黄河故道腹地的小村。那是一个静谧的夜晚,他路过村头那棵大槐树,不由停下了脚步。朦朦月光下,当年村民为他捐助学费的一幕像电影似的展现在他面前,老支书那番充满鼓励和期望的话仍在他心头震响——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东方天际被朝霞涂抹得一片火红。村头那口大钟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像惊雷炸起,像山洪爆发,震响在村庄上空。村民们一个个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向村头大槐树下涌去。
这是一棵百年巨槐,枝叶交柯,郁郁葱葱,像一把巨伞高擎在村头。树上有一口铁钟,锈迹斑斑,上面落满了灰尘和鸟粪,掩没在青枝绿叶间。树下有一块青石板,高出地面半米多。这口铁钟和这块青石板是合作化时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文物,多年来再没人使用。
大槐树下聚集起全村几百口人。老支书站在那块青石板上,向村民们发话说,老少爷们,今天我打扰你们了。这个会本来应该由村支书和村委主任召集的,可他们俩都不在家,一个到南方打工去了,一个到外边跑生意去了。可有件急事儿,不得不把大伙召集来商量一下。
老支书这几句话一下把大伙感动了。有人说,看看,还是人家老支书,说话多中听啊,哪像现在的干部,动不动就发命令!有人催促,啥事儿,老支书?你还是咱村的当家人,你旗往哪里摆,俺就往哪里跟啊!
老支书轻咳一声,说,大伙可能知道了,喜娃子考上了大学,这可是咱村的光荣啊!咱村三十年没出过一个正牌的大学生了,今年喜娃子给咱村的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今年出了一个大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明年后年就可能出现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大学生来。咱大槐树村也许从今之后就能兴旺起来了。所以我说,这是咱村的大喜事,你们说是不是呀?
村民们欢呼起来,把喜娃子推到老支书面前,也把喜娃子爹推到树下那块大石板上,乱纷纷地说,叫他爷俩介绍介绍咋考上大学的,大伙也向他爷俩学学啊!
老支书向村民们摆摆手,大伙又安静下来。老支书说,喜娃子只是考上了大学,还没去上大学,现在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大学生。为啥呢?因为现在上学跟往年不一样,那时学生困难学校还给助学金哩,现在不同了,上大学要交钱,多少?不算在校吃花,一入学就得交四千块啊!喜娃子家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大伙说说,这事该咋办哩?难道咱村三十年出了个大学生就这样不吭不哈地黄了吗?
老支书说到这儿,也激动起来。他挺了挺胸脯,提高声音,倾注出全部热情和气力大声向村民发话说,老少爷们,大伙还没忘记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句话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咱村党的负责人不在家,就由我这个老党员出面吧!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咱全村要是每人拿五块钱,喜娃子就能上大学了。现在五块钱算个啥?不过七八斤小麦罢了!咱不搞摊派,一切都是自愿,你拿一百不算多,你拿两块不算少,你不拿一分也不算你落后!大伙说说这样中不中啊?
老支书的话顿时把村民们激发起来,鼓动起来。他们说,老支书说得好,咱就照老支书的话办,尽尽自己的心意吧!
这时只见老支书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卷钱,在空中摇了摇说,托邓小平的福,这几年我腰包里也有几个钱了,但不多,全年积蓄只不过五百块,我全拿出来给喜娃子作学费,能亲眼看到咱村的年轻人上了大学,我打心眼里高兴啊!
王志民老师也赶了来,他举着一沓钱说,元月份的工资我现在才领回来。这二百块钱我全给喜娃子吧!我教了二十多年学,今年才送出一个大学生!要是我的工资能全部兑现,我把钱全拿出来也乐意啊!
村民们也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当场掏钱,有的急忙回家拿钱,有拿三十五十的,也有拿十块八块的。爹接过这沾着庄稼人的汗水和体温的钱币,对喜娃子说,孩子,还不快跪下?给乡亲们磕头,快给乡亲们磕头啊!
爹说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抱拳,眼含热泪,向乡亲们连连拱手说,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了!
郑喜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合,他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看看老支书,看看乡亲们,这些普通的面孔普通的身躯多像这大槐树啊!表面看来很平凡,其实,在中国真正称得上伟大的才是他们!于是,他深深弯下了腰身,双手着地,跪拜在乡亲们面前。
……
现在,郑喜成大学毕业了,如何回报乡亲们对他的希望和厚爱?他眼望着那巨钟,心头是一片茫然。他不但没有衣锦还乡的激动,反而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悄悄从一条小道溜到那座土墙环护的小院来。
爹还没有睡,只是坐在门槛上一个劲吸烟。娘也没吭声儿,只把一碗面条放在他面前。郑喜成吃不下饭,他安慰爹娘说,我去人才中心了,人家记下我的名字,叫我在家等着。爹抬起头,只说了一句,吃饭吧,身子骨要紧哩!
第一个来到喜娃子家的是王志民老师,他问,工作找到没有?
郑喜成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虽然没有找不到工作,以后还有机会的!
王老师说,听说乡中学要人哩,你去活动活动嘛!
爹猛地站起来,要找工作就到党政机关!老师连工资都发不上,到那里去喝西北风?
王老师叹息一声说,那党政机关能是咱庄稼人进得去的?他闲坐一会,便独自走了。
爹又重复说,球,在家种地也不去学校!爹说这话时很激动,他在小院里来回走动着,那腰杆似乎比平时挺高了好多。现在我是看透了,这职业那职业,都没有干部这个职业吃香!现在真正当家做主的是干部,是领导!
郑喜成对爹说出如此真切而深刻的话,感到大为吃惊。爹不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爹是一位当代农民的典型。爹在作物种植上很有一手,至今他那句名言还在乡间广为传播。他针对农村的瞎指挥,编了一句顺口溜:乡干部的话不能听,他叫你上西你向东,他叫你种蒜你种葱!爹为此受到乡长的多次训斥,但他却依然固我。几年来爹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颇受四邻乡亲的尊敬。
郑喜成佩服爹的精明和深谋远虑,但又从心灵深处感到这一愿望难以实现。那干部能是好当的吗?那机关能是好进的吗?现在各单位都超编,都在喊着要裁员,想到党政机关里去真比登天还难。
月光将杂乱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投射到小院里,土墙根响起了蛐蛐的叫声,让人感到有几分寒意了。
爹说,睡吧!
娘也说,该睡了!
郑喜成也说,天不早了,该睡了!
可爹仍坐在那里吸烟。娘也坐在那里不动身。郑喜成不知是去睡觉,还是陪着爹娘再坐会儿好。
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原以为考上大学就端上了铁饭碗,一切不用咱再操心了。谁知毕了业还要自己找门子,娘的,早知这样,费那么大劲儿上大学干啥呀!
爹在小院里一直坐了很久很久,那叹息也一声连着一声。郑喜成只能再次安慰爹说,我的档案已输进人才中心的微机里了,有看中我的单位,人家会通知我的。
爹说,那就听天由命,在家等吧!
爹说这话时显得无可奈何。郑喜成感到心里很苦,很疼……
【2、翻出个文学梦】
等待的日子是最无奈的。郑喜成吃不香,睡不甜,就是到地里帮爹干活,心里也恍恍惚惚的,像做梦一般。他去给棉花整枝,把花杈当成杂枝给掐掉了。他去锄玉米,竟把玉米当成杂草给斩杀了。爹没有责怪他,爹说,你歇歇去吧,这点活我就干了。
郑喜成担心会弄出个神经病来,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便找了几本书看。乡下没什么好书,翻来找去,他从破纸箱里找出来早几年读过的几本小说和诗歌。虽然是随便翻一翻,却翻出他一个文学梦!
郑喜成上中学时,王老师教他班的语文。王老师一直是民办老师,为了表明自己的教学质量高,他特意将喜娃子的一篇作文推荐给老河报“新芽”专栏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能变成铅字,郑喜成自然乐得什么似的。然而,有人却讥笑他说,那“新芽”是发中小学生作文的,你郑喜成已是堂堂的高中生了,还跟小学生扎堆儿,不嫌丢人吗?这小辫子一下被抓了个准儿,连郑喜成也知道这“新芽”里标示的“中”字是指初中生的。但他不气馁,他要拿出更好的作品来证明他的水平。他丢下最难啃的数理化,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写作上。半年后他果然成功了,有首小诗竟发在老河报“精美文学”版上,跟本市著名作家平起平坐。他乐滋滋地去找王老师,并客客气气地说,请多指教!王老师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看你小子是发疯了!你赶快迷途知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简单几句话就把郑喜成的文学梦击碎了。现在每每回想起来,郑喜成对王老师都充满感激。别看王老师平时窝窝囊囊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竟如此有眼光。
现在郑喜成大学毕业了,他闲在家里,只能用写作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他像一只勤奋下蛋的母鸡,一天就有几首小诗问世。他向大报小报大刊物小刊物投稿,每次寄稿都得花好多钱。老娘喂的那几只老母鸡虽然同他比赛似的争着下蛋,但那卖鸡蛋的钱仍难以抵挡他与日俱增的邮费钱。他不得不向爹频频求助了。
爹问,你那稿子能挣多少钱?
他不屑地说,钱是小意思,我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爹说,价值不就是钱吗?
他说,价值不等于钱,它比钱更珍贵!
爹疑疑惑惑的,知道儿子比自己学问深,也就不再多问,从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几块钱,递给儿子说,只要有价值,爹就舍得!
爹对写作一直充满敬意,他认为能在报上发表文章都是了不起的,可后来看到儿子投的稿子没个响声儿,便悄悄问儿子,那作家能是好当的吗?当上作家是不是就有饭吃了?
郑喜成以冷冷的一笑而置之,因为这问题太不值得回答了。
爹没有生气,只站在一旁看儿子笔走龙蛇。是呀,古代一篇文章能考取头名状元,如今不是也有一篇稿子在报上发表就被提到上边去吃皇粮的吗?爹高兴地说,孩子,写吧,写吧,能写篇好文章混个好差使也不赖!爹把自己腰包里仅有的几块钱全掏出来,放到郑喜成桌头上,轻轻退出那间小书房。
寄出一篇稿子也同时寄出去一片希望,郑喜成自信会有慧眼识珠的好编辑把他的大作发表在显著位置上,让县里和市里的官员知道大槐树村有个笔杆子,能写一手好文章。可惜现在报刊既不退稿,也不回信,是发表了还是枪毙了,也不知道。那每一句诗行那凝聚着自己心血!既怀着希望又怀着失望的苦苦等待是最最难以忍受的。他坐卧不安,心急如焚,忧思中忽然想到,作品发表是要寄来稿费的,有了汇款单便可知作品发在哪家报纸哪家刊物了!
郑喜成跑到邮电所,目光越过高高的柜台,他看到一个女子低头看书的倩影。她全神贯注,目不旁视,如处无人之境。这天不逢集日,这小小的邮电所更显得冷落。郑喜成喊了两声,居然没有得到回应。郑喜成大为恼火,他愤怒地敲了敲柜台,请问,我的汇款单来了没有?!
这一声吼马上得到女营业员的迅速回应。在农村能收到汇款单的人家不多,因此那女营业员的反应便格外灵敏,也格外热情。她没看清对方的脸面,便投过来一个甜蜜的笑。姑娘的脸蛋黑粲粲的,而她投来的那个笑更使这黑粲粲的脸蛋儿变得亮丽多了。以写诗写出几分形象思维来的郑喜成顿时在脑瓜里闪现出来一个十分生动而妥贴的比喻来——黑牡丹!
黑牡丹看了一眼郑喜成,眼里顿时放射出惊喜的光彩。呀,这不是我们的大作家郑喜成同学吗?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郑喜成一时没有认出这黑牡丹是谁,这种不被认可的冷淡最令人尴尬,黑牡丹气得哼了一声,把脸扭到一边说,你还记不记得,有人曾在你的语文课本里夹个小纸条儿?那纸条儿可不是一般的纸条儿,那是从一本挂历上裁下来的,背面是刘晓庆火红鲜艳的嘴唇儿!
郑喜成忽然想起来了!那是他的作品在市报发表时,有人在他语文课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儿,那上面的话也真够刺激的——我爱你,未来的作家!当时他费好大猜疑也没猜出给他写信的是谁。现在经这黑牡丹一提示,才忽然想起来。啊,火红的嘴唇,不就是蕴含郝虹的寓意吗?对,黑牡丹就叫郝虹,她把自己的名字巧妙地隐含到刘晓庆的嘴唇上,从而表达出一种很性感又很生动的内容!
对不起,对不起!郑喜成连声道歉。
黑牡丹说,这也不怪你,我高中没读完,就来接爹的班了,咱班那么多女生,你哪能认得完哩!
二人趴在高高的柜台上,面对面地谈了个海阔天空。最后,黑牡丹问,是不是有海外关系,给你寄来一笔巨款?
郑喜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有几首小诗,可能发表了,我看看汇款单寄来没有。
话一出口,郑喜成顿时掉了价儿。黑牡丹用嘲弄中带有鄙夷的口气说,哎呀呀,你写那破玩艺儿干啥?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你还去凑什么热闹?
黑牡丹的嘴像刀子戳痛了郑喜成的心,二人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郑喜成转身要走,忽听街上人声喧闹,还有锣鼓声和叫骂声,使这个小集镇顿时陷入激动和不安之中。两人都跑出邮电所看热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