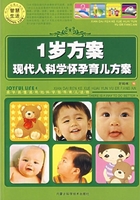三匹马行在浓黑的夜道上,出汉城经僻市抵白马门,一路走来星光如晦,扃户深闭。
自出齐香苑后,赵旭并蒙真,辛雷便添上了宵行的绒氅,骑马离开了。韩英则仍弛车回四方馆,掩人耳目。
北地的夜里,纵然无风,也冻的入骨。赵旭将毡帽向前拢了拢,狐皮手套触到两颊,只觉自己面如冰霜。他一面盘想着连日来的见闻经历,一面又要分心警戒着四周的动静,不敢稍怠。清憩之隙,倏沦惆怅,念中宵乍别,凝睇抟情,忽焉眼前,恍然云外。
感伤间,赵旭不自禁地就抬头望向了天上,只见那月仍在中天,交光晦幻着,侵寒无际。前瞻夜路茫茫,两无消息,更生寥落。
“大人若心仪黎姑娘,何不取金赎归。交由韩英去办,必定稳妥而秘密。”辛雷望赵旭形容似惨,故闲话道。
“莫要多话!”赵旭不加思索:“国事当前,何虑其他!”他心知韩英世故圆滑,营以自利,诸事愈勤愈至,愈应防范。然又不得不用他,一来为人际利害所缚,二来这人确实伶俐,最善相机应变,心思虽多舛,报国却无二心。
“辛雷!”赵旭又道:“银子可都备齐了?”这话原多余,脱口而出后,却生出些兴奋,溢于形容。
辛雷嘿然一笑,应道:“大人放心,一切皆已备妥。就是夜里天寒,大人恐要一直受冻了!”
“无妨!”赵旭顿下缰绳,心间沸然。面上即英气灼朗,笑意隐约。
原来宋辽两国,嫌隙日久,两国细作,穿游朝祚,非是鲜事。辽国左军中一中郎,名唤审密图南的,即是宋人潜隐多年,伪为装之。引进副使陶玦数使辽国,素悉此间风土人事。初入辽时,陶玦便以千金贻审密图南,图南初以两百金奉德王侧妃审密氏,又以三百金奉其正妃穆康氏。审密氏知之,怒责图南,图南以穆康氏能为己谋高位为由,回塞审密氏。审密氏性最轻浮,又蒙耶律宗训燕宠,愤之不过,遂言于图南:德王久觊帝位,日夜谋之。半月内便要功成,如图南以重金相赂,便述其计,不日效劳危时,与德王里应外合,勋国亦可望,何况一高位。图南踌躇再三,伪为不肯,翌日,方又献五百金。审密氏得意忘形,故将一己所知,和盘托出。德王一介武夫,其篡国之策,无非攘兵生乱,若只辽中内战,本无关宋使。但其意在勾结边匪,徉以荡寇之名,追迹边境,侵犯幽州。图南得信后,自速递于陶玦,陶玦与赵旭商议,此事干系重大,恐人心生变,故只达于亲信,勿言向众人。赵旭又与陶玦秘中拟信,简述此间情形,遣随行智勇之辈妆作往来商队,星夜送至幽州大营,濮王允让手中。前日朝上,果有人奏言,匪蔻经月集团,欲犯辽都,德王遂自请缨,领兵却贼。赵旭陶玦等更悉前报确然,一日之内,幸濮王回信亦至,濮王信中言——俱悉,自重。举事之日,当加兵城外,勿忧!赵旭与陶玦拆信得迅,虽未知将遣者何人,心间皆稍释怀安,相顾而喜。
“大人,郭将军,所向披靡,属下亲见过的!”蒙真策至赵旭身旁,压低了声音,欢欣道。这少年才十八岁,血性方刚且心思单纯,遇事辄易慷慨,难抑其情。
“你已知晓!”赵旭兴奋搴绳,眸亦采烁。
“嗯!”蒙真用力地点了点头,寒天冻地中,他晶白的面上绻着两团红晕,一双黑亮的眸子探顾炯炯,粗呵白气团团,毫不在意。
赵旭置下车帘,轻地一笑,心思这少年稚如幼虎,一腔未经世的豪迈,竟有些欣慰。
不一会儿,三人便转过一栋门楼,驶进了一条僻巷。这巷中阗寂,杳无人息。只有一声声敲钢锻铁的斫鸣,由远及近。
“大人,就要到了!”辛雷贴近赵旭侧旁,沉声道。他说着,一双眼仍聚视前方,语声愈发警觉。
“嗯!”赵旭应着,一只手旋翳向袖中,握紧了出使前赵祯密嘱于他的那枚虎螭铜青符。
忽然“嗖”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自赵旭耳边飞了过去。赵旭惕然而侧,惊舛定视间,方知是箭,险被辛雷横空捉住了。喘息甫定,只听得辛雷疾地一呼“大人小心!”,另一枚箭已飞了来。这次却是蒙真及时反应,半身跃转着,反手掇住了箭尾的雉羽。
正在三人全神警戒之际,只见空中飘下一影,越来越近。一面还悠然说道:“京中诸卫,真是愈发精进了!”
辛雷与蒙真悉紧紧地握着刀柄,辛雷已是不耐,一面豹视着四方,一面怒声诘道:“是谁!”
倏忽之间,那人已落到了地上。只见他款然数步,向赵旭俯身一揖,道:“少骑都尉凌锐思,见过引进使,赵大人!”
“图南!”赵旭勒停住那受惊之马,视向那人。
这是一个三十上下的男子,披一身玄革斗篷,斗篷内似是一身绒甲,腰间金带突狰,寒光晔晔。他身形魁伟,目光如隼,半张脸隐在斗篷下,不能得见。
“正是在下!”凌锐思亦视向赵旭,殊无卑亢。
“既是同僚,为何兵戈相见!”辛雷不肯依饶着,仍有些怒气。
凌锐思却未理会辛雷,只望着赵旭,意似猜度,又似打量,双眸倏地一深,洞邃如炬。
赵旭定然兀立着,目光稍有些俯仰,气岸桀骜又屏待凝静。
两人蓦地一松,相持顿解。赵旭敛然一沉,道:“事况紧急,不容多耽,凌大人,前面带路吧。”
“是。”凌锐思又是一揖,便转身向前去了。赵旭三人在后,只见他身形如常,行走却似生风,转瞬之间,已离开了数丈。
“走!”辛雷兀地一喊,便策马赶了上去。
赵旭与蒙真相顾一视,亦回马追上了前。三人跟着凌锐思,不大一会儿,便到了那铁声哐啷的地方。
那是一间破败的瓦舍,荒草被径,墙垣颓圮。马蹄漫踏过一地的枯槁,徐徐幽进着。蒙真展眼四望着,又好奇又紧张,气息也愈发促急,不知不觉间,离赵旭越来越近。辛雷此时却静了下来,信步悠然地,竟露出了平日里将官的威风。
“哗”地一动,霎时间火光扑聚而来,粲乱团团。火花星散后,众人凝睛细视,方见炉中烈火犹焚,人迹却已杳茫。
正在辛雷与蒙真惊疑之际,凌锐思已自屋后牵出了一匹骨骼劲健的骊马。他走上前来,将三把猂月纹首的鎏金弯刀递给了赵旭三人:“这是德王亲兵所佩的金刀,大人务必带好。”
“大人不会用刀!”蒙真随口道。
“呵。”凌锐思轻哂一笑,已跨上马出门去了。
“走吧!”赵旭按着凌锐思佩刀的地方将这把弯刀佩到了腰间的羊皮革带上,随即驰草而去,蒙真与辛雷自紧随在后。
众人方行出数武,只听得“轰隆”一阵巨响,身后霎热浪燎灼,火光滔天。一时间瓦砾灰飞,须眉立见。
蒙真侧目一瞥,不禁唏嘘:“真是好险,幸亏大人无恙!”
“若引进使客死辽境,濮王亦好举兵,师出有名了!”凌锐思淡淡道。
“你什么意思?”蒙真须臾思转,惊极交怒。
“兵分两计,计在一功!这道理,大人懂的吧!”凌锐思淡淡道。
“呵!这般道理,未免小视在下了。”
火光越升越高,渐渐地,与那天边夜昼连成了一片。熊熊吞咽过,哭声嘶喊,鼙鼓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