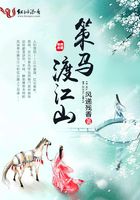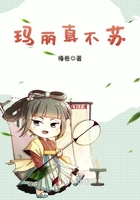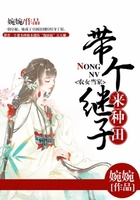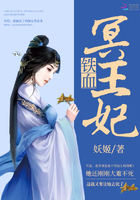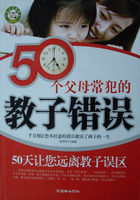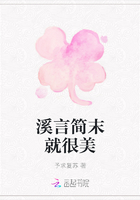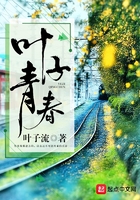“人生的一切都是苦禅参悟。”
这是允谚与适霁进到精舍中后听到明禅大师说的第一句话,当然是对商王说的,是时商王正掂着一粒黑子,面上愁眉紧锁,说不出的忧容深重。
“王爷已想了好一会儿,眼见得时候不多了,不如请小王爷或是徐小公主替王爷落了吧。”那明禅大师却是从容,不紧不慢地拈起一粒白子,又放了回去。他不过三十许的年纪,虽是年轻,已遍悟明经,参三藏,举凡经论讲演处,莲台浮屠之下,无不应答如流,见地不凡,显是大相国寺“明”字辈僧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生的很清俊,虽是盘坐着,也瞧得出身量修合,气宇轩宏。白净有棱的脸上一对破叶眉漆深而细,双眼明砺,那目光似乎无论落在哪儿都是严确而清晰的。这样严冬的天气,精舍中只生着一只红泥小炭炉,他也只叠披着三两件淡色丝绡的僧袍,念珠挂在执棋之外的另一只手上,捻动无声。
允谚与适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一时都没了言语。
“好了,你们二人有什么话,就说吧!”商王将棋子掷回棋笼中,他与子侄们说话一向声吻肃重,却也不大严厉骇人的。眼下不同,不仅严厉,似乎还有些懊恼冷淡在其中。
允谚的脸色也变的不大好了,他真觉得无聊透了,那幽暗的棚楼曲屏后,那样美丽而哀深的两个人,怎会与眼前这浊恼的情相勾连到了一处,甚至是很深的勾连,忧戚于命的那种。
“舅舅,是这样的,我们……”适霁见允谚脸色不变,又肃穆着不说话,恐两生嫌隙,不欢而散,自嬉笑着向前,替人说道。
适霁的话还未说完,已被允谚扯住袖子拉回了自己身后。允谚抬眼望着商王,似有些愤愤地,道:“允谊在潘楼中的一场事端,与小侄有些瓜葛。伯父不责,小侄深以为谢。此事尚有些余音,小侄既撞见看见了,便,便……”说着,他又思踌了起来,原本觉得理所当然,一时又迟疑了,甚不知那二人是否希望商王知晓他们的行踪,这数十载的年光变迁。他吞吞吐吐地,又怨愤自己。人世间的姻缘际会,是非恩怨啊,话到嘴边的谜底,就是不晓得怎样才算是好,算是妥当,兴许根本就没有吧,得尝所愿的圆满,甚至弥补都谈不上。
“怎么不接着说啦?方才不还气得很嘛。哼!”商王望了望二人,道。神情虽还是严肃,语声已比方才缓和了许多。
“我……”允谚沉了沉气,方重新抬头,望着商王,端正了语气,道:“伯父可听过玉楼笙这个名字?他如今是南瑾里望月棚内的一个男旦,是勾栏间很有声望的名伶。”
商王顿了一顿,仍波澜不惊地道:“未曾听过,一个勾栏中的优伶,本王何曾得知。”
“勾栏之中都是以假名姓示人的,这玉楼笙必定也是。那日在潘楼,煜兄,也就是宁海侯郭家的二公子为帮小侄脱身,解囊一千两买下了那秘釉青瓷的碎瓷片。还未出潘楼,那碎瓷片又被另一人用一柄做工极精巧的玉梳换去了。前几日小侄与煜兄在望月棚撞见那人,一时好奇跟了去看,才在棚楼内见到了玉楼笙。他与伯父年纪相仿,好像害了很重的病,听他们话中的意思,不久就要作别欢场了。”允谚缓缓地说道,一面不自觉地留意向商王的脸色。
商王一直沉着脸,眉峰待聚未聚的,有许多深藏的,忍耐的痛苦在其中。他默默地听着,一直未打断允谚的话。
“好了,时候差不多了,你们先回去吧。”过了一会儿,商王方沉肃道。
“是!小侄告退!”允谚俯身一揖,就要退出。适霁一脸懵怔,但知不该多话,便紧跟在允谚身后一道出去了。
方要出门,允谚又回身,想了想,仍道:“伯父,小侄只是事外之人,无意搅扰刺探。只是希望,希望伯父也看开些。人生百年,其实短得很呢。”说罢,便拂帘去了。
雪下的比方才更大了,飘在素黯的僧舍灯笼下,落在石砌竹槛间,一地的细碎晶莹。远处宝殿中灯火已漫,隐隐地随风雪递来沉沉的经声,这世界,夜里洞明,飘雪不语。
“大师,你说,那孩子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商王问着,仍执棋不定。
“便是要王爷宽心的意思啊!”明禅应道,仍云淡轻轻。
“就这样简单么?”
“简单么?那王爷可宽心了?”明禅玄莫地一笑,棋盘上白子一落,是最后一枚了。黑白经纬,到头究是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