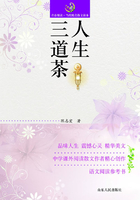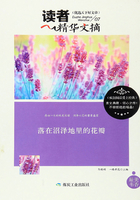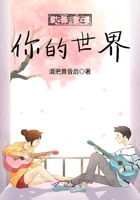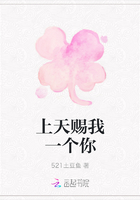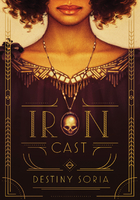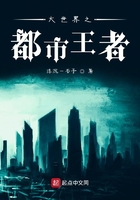白明德参与创办的学校,在1914年以后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扰。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上有报道曾提及,在1919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1923年3月,白明德的教会学校更名为明德小学,继承了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内的两幢楼房、三间平房和一个礼堂。到1951年3月时,明德小学有教职员工25人,学生1036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早春,人们对现实理想的狂热拥戴,很快就会淹没掉过往,包括来自荷兰小镇斯泰尔的圣言会和与其有关的所有痕迹。其实,在1875年艾诺德·杨生神父创立圣言会的那一年,沈钧儒、张作霖、秋瑾相继都来到了人世。远隔千山万水,将天主教圣言会和诞生在大清国的几个无神论者搅拌在一起叙述,似乎荒诞。但一一比较下来,却可以看清楚圣言会中国化的路径,看清楚变化着的圣言会生长的土壤。显然,除了向日葵和茉莉花的含糊隐喻之外,他们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持续存在的。这中间包括了民族主义和信仰的分合,也包括了西方宗教扩张背景下中国军事、法律、革命、文化的成长传奇。就这些要素而言,沈钧儒、张作霖、秋瑾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俗经验。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在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早在1907年,同盟会的鉴湖女侠秋瑾已死在了绍兴轩亭口,这个革命者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一个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先驱的预言,默默无闻来,轰轰烈烈走,用死亡占卜未来。沈钧儒活的时间最长,这位前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不仅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全盛期,还看着这个日趋专制的制度在大陆最终分崩离析。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时,沈钧儒和陈志皋等三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束之高阁。人们并不确定,为上帝工作的白明德,和争取人权的沈钧儒、护卫东北的张作霖、向往共和民主的秋瑾,是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但隐约觉得大致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这突然就让这些个没有发生过纠葛的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一种具有相同价值的连接。这种联想,令人沉迷并怅惘。
可以确定的是,古往今来,通向精神圣地的共同道路,一定有许多人在走。
从安治泰、福若瑟到白明德,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前后延续了30年。斯泰尔修会行走在青岛的那些年,大清帝国崩溃了,德意志帝国战败了,大日本帝国回家了。其间在青岛出生的第一代城里人,已经慢慢长大。
卫礼贤│不务正业的传教士
◎记忆地标:传教山魏玛传教会/克烈纳德住宅/大鲍岛
随着1898年3月6日《胶澳租借条约》尘埃落定,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新移民一起陆续进入殖民地青岛,使得世俗的青岛和上帝的青岛几乎无法分别。好在大家各有所求,身份识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安定下来后,人们却发现,也有身份确定的传教士,同时在进行着一些和传教不相干的事务。他们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埃·福柏,他的中文名字叫花之安;之后,卫礼贤在更人文化的学术方向上,继承了福柏的使命。
1898年4月5日福柏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刚支起铺盖的殖民地,并没有一杯热咖啡可以给他享用。一年以后,这种类似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传教士福柏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有没有一杯热咖啡,对他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他的热情,更多地倾注在当地原始植物品性的发现上,并且乐此不疲。
实质上,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道听途说发现青岛的地理价值,到植物学家福柏在这块土地上一点一点逐个调查物种,两个不同身份的德国人的行事背景,已经有了相当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执着的探索精神,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科学的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对东方自然与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纯粹的科学发现角度看,植物学家埃·福柏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没有争议地成为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同善会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一方面他需要完成同善会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独立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同善会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有着传教士身份的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冬天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一位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
对于埃·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政府墓地里。1901年9月,教会在武定路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是死者的夙愿。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安徽路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为纪念福柏,这所1907年开业的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的一个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继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等到人们在城市中心可以很容易喝到一杯纯正热咖啡的时候,福柏已经在植物实验场西部政府墓地里沉睡了有些年月。福柏栖息的地方后来被称为万国公墓,20世纪60年代被狂热的年轻人摧毁,大量的墓碑拿去做了铺路石。
福柏死前的4个月,卫礼贤这个同样具有符号意义的上帝使者,也抵达了青岛。
不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卫礼贤都是个容易让人产生兴趣的人。他的经历,他的作为,他身上承载的符号性特征,让他成为一个殖民地时代的特殊代表。而他的一系列写作活动,则同时使他作为一个历经者的见证意义,在后来的年代显现出非常的价值。
理查德·威廉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斯图加特,但也有资料显示他的出生时间实际在5个月后的10月10日。威廉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1882年父亲的过早去世,改变了威廉的生活轨道。面对陷入困境的家庭,母亲决定让他转入神学校接受教育。1895年11月,在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后,威廉被授予了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
1899年,威廉被魏玛传教会选派到中国协助福柏进行传教。5月12日,威廉抵达青岛,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生活历程。到青岛后的威廉,很快就显示出了融入中国社会的热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这就是卫礼贤。
开始的日子,卫礼贤是一边在简陋的房子里给德国孩子上课,一边在等待来自家乡的信件中度过的。1899年10月14日,卫礼贤在函告友人时曾说:“此间一切初创,万般简陋,但政府的工作很谨慎,且有魄力,主其事者并非总督叶世克,而为文官委员(单威廉)。单氏能干并富有远见,一切建树悉出自彼手。”在这个新的殖民地,雨季的瘟疫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头几年,传教士最经常进行的活动,就是主持葬礼。大致到了1900年的2月,随着魏玛传教会可以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投入了使用,卫礼贤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这时,他把他的未婚妻从家乡接了过来,并举行了婚礼。
接下来,卫礼贤开始了他的办学活动。他的学校1902年在今胶州路柏林传教会教堂旁边建立,定名为礼贤书院。1903年,书院在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第九中学)建成新的“中国式”布局的校舍。此后,书院是在继续吸引新生和不断扩建中逐步发展的。1905年,以卫礼贤夫人名字命名的美懿书院出现,成为青岛第一所女子学校。卫氏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基本依照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1906年,鉴于卫礼贤在兴办教育上的贡献,山东巡抚杨士襄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赐四品顶戴。
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实质上并没有广泛传布基督教义,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逐渐呈现出尊孔读经倾向。1903年开始,他即在《青岛最新消息》和另外一张在上海出版的影响力更大的德文报纸上,发表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北京方面的时事评论。后来,他还陆续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等译作。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和一些在此避难的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保持了持续的交往,尤其和改良活动家康有为、前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等过从甚密。在学习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过程中,劳乃宣曾给卫以很大帮助。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卫礼贤亦曾参加活动。从上海回青后,卫即筹划成立青岛尊孔文社,并聘请劳乃宣主持。1913年,卫氏在礼贤书院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填补了本地现代图书馆的空白。藏书楼匾额为恭亲王溥伟题写,劳乃宣则以《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赞之:“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时藏书楼藏书多至三万余册。
卫礼贤从1899年至1920年一直住在青岛。后来在几度进入中国后,他回到了德国。张君劢曾这样评价这个“世界公民”:“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在德国,卫礼贤继续了他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著。其中的《易经》,卫氏在青岛就开始翻译,毕十年之功,终于在1925年面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他的最后一部译著《吕氏春秋》,在他离世前两年出版。1930年,“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逝世。
1900年的9月29日,当威廉·舒勒从总督夫人海伦·沃琳的手中,接过由在青岛的德国妇女赠送的教堂台布装饰时,他后来一度租用的德县路3号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的房子,才刚刚开始建设。
人们对商人克烈纳的青岛行迹,始终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和这个进出口贸易商一起被时间淹没的,还有他的房子里面的许多匆匆来去的过客。根据马维立教授从波恩提供给青岛学者王栋的资料,克烈纳公司的办公室在大鲍岛,他自己也居住在大鲍岛。克烈纳在德县路买地建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在城市开发初期建成的这栋私人建筑,以一个敞开式外廊为标志,透露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猜测,在一些闲暇时间,这里的房客应该有机会松弛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透过二楼南边的窗户,眺望威廉皇帝岸外的前海。或者,在这些房间里面,还可以找到诸如阿·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和托马斯·曼的《去墓地的路》这些刚出版不久的德语读物。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输送到这里,所产生的精神慰藉作用大约相当于半个牧师。尽管,在克烈纳的房客名单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牧师。
其实,除了对克烈纳的行迹缺乏了解外,人们对魏玛传教会的威廉·舒勒牧师,也就是后来克烈纳的房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和传统的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特色。传教士被要求以迅速的、大量非基督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履行建立上帝之国的任务。而舒勒的到来,相信是为了减轻魏玛传教会同事卫礼贤进行“皈依基督教”工作的负担。有一段时间,卫礼贤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病得很重,幸亏后来及时去了上海治疗,才得到恢复。也许正是因为卫礼贤健康状况的糟糕,才使得魏玛传教会下决心再增派舒勒到青岛来。
从1900年5月起,舒勒成为青岛的新教牧师。他的薪水由总督府支付一半,另一半则由魏玛传教会支付。当年的秋天,舒勒在向魏玛传教会的报告中说:“迄今每星期日10点在总督府新教教堂举行弥撒。最近除了海军炮兵的蓝色外衣和水手的军服上装外,也出现了不常见的正规军尖顶头盔和制服。这些人以其家乡着装的方式,透露出他们是刚到亚洲的新人。去年夏天因为很多人被调到外围兵站和疾病,整队前来参加弥撒的连队数目常常锐减。”在舒勒看来,通过珍贵的圣台新台布的装饰,小教堂的外装饰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青岛夫人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在1900年的9月29日,由总督叶世克的夫人交给了舒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