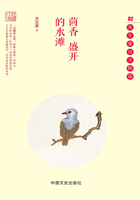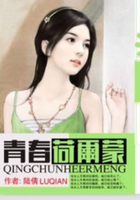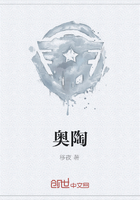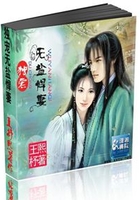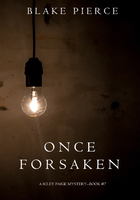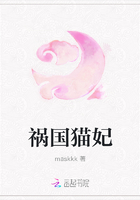邓仲纯的一生,可以拉拉杂杂牵扯出一堆文人故事,青岛7年,尽管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却也勾连起了胡适、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郁达夫、老舍、台静农等好些人物。邓仲纯原名邓初,与信奉“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同为安徽怀宁(安庆)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弟邓以蛰是清华教授。邓仲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老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就是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仲纯。邓仲纯与方愫悌结婚后,生有两女,分别是姐姐邓绎生、妹妹邓宛生。姐姐邓绎生后来随母姓,改名方瑞。1930年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请邓仲纯任校医,邓举家到青岛,和杨振声住楼上楼下。杨振声和比其小20岁的方瑞,发生了一段并不热闹也没有结果的桃色情事。据说曹禺后来创作《北京人》,剧中人物曾皓就有杨振声的影子。[42]这样的隐秘事情,各方当事人自然都不愿让人拿着放大镜窥视,时间稍长也就事过境迁了。如果后来方瑞没遇上曹禺,大概连个影子也不会留下。就这段隐情来说,《春秋谷梁传》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中的尊、贤、亲全齐了,张扬自属不义。其实,事情没扩大,除了杨振声的原因外,应该也和邓仲纯平素为人德厚、忠义有关。到青岛前的1929年,邓仲纯就曾在一个紧要关头帮助过郁达夫,使其幸免于难,这使得郁达夫一直心怀感动。1934年暑假郁达夫和邓仲纯在青岛重聚,郁曾赋诗“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得皖公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以范雎逃魏入秦的典故,比喻对当年邓救助其逃脱迫害的感激。
抗战爆发后,邓仲纯离开青岛回皖,随后全家避难入川,与当地乡绅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并在邓鹤年叔侄的资助下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应邓邀从重庆到江津,受到邓的持续帮助。台静农在《陈独秀先生》中记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九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七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邓以蛰的儿子邓仲先晚年回忆:“二伯父邓仲纯在江津开了一个延年医院。在江津看见了陈独秀先生,二伯父和他是至交,因陈独秀先生是我祖父的学生。”[43]后来一直到陈独秀逝世,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战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邓仲纯似也随赵太侔重返青岛,1947年9月5日老舍在美国纽约八十三西大街118号复信赵太侔,末了有“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一句。之后关于邓仲纯的公开资料甚少。国家制度变化翻天覆地,一个有一大把旧知识分子朋友的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又与脱党者陈独秀相濡以沫,晚境往好里想,也就是寂寞终了罢了。1959年,邓仲纯在北京撒手人寰,去见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了。他的青岛老邻居杨振声在此前3年也已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杨振声的最后日子,形单影只,门可罗雀。邓仲纯去世9年后,他的另外一位邻居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杀。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一个疯狂的季节,遥远的花香扑面,赶海的人发现了前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尸体。
丁麟年│光亮之外,一切陷入沉寂
◎记忆地标:少海书画社/水族馆/信义会医院
1930年的青岛和处在青春期的国民党一样,活泼地在上升轨道中有秩序运动,充满了新生、野心和欲望。似乎没有人关心衰老、迟暮和死亡,因为一切都是年轻的:制度、思想、学术、事物。然而,对上一代人,死亡却依然如期而至,像春夏秋冬的自然轮回。
1930年的死亡记录之一,是丁麟年的病逝。这个信奉“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的旧体制知识分子,一年前才移居青岛,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街道还没怎么熟悉,就戴着已经褪色的前清正五品帽子,回归了自然。丁麟年生于1870年,字绂臣,亦称绂宸,号幼石,山东日照涛雒人。生于进士世家,一门父子三进士,家有李鸿章所书“一门三进士”匾额。父丁守存(1812—1883),道光乙未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湖北督粮道等职,对天文、地理、测量、数学、物理、化学等均有研究,为近代较早的洋务派和军事科学家。丁麟年19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历任户部郎中、兴安府知府等职。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主张变法时,丁麟年正供职户部,对公车上书表示赞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出走,丁麟年曾施以资助。
1912年,丁麟年由陕西弃官回归故里,此后相继拒辞就任上海道、烟台道的邀约。1920年2月,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满足了其“笃嗜金石、热爱考古、精练书法”的夙愿。丁任内整顿、清理、编排馆内所藏图书文物,并搜集铜器、陶器、汉画石刻等文物,均分类鉴定考证,并搜集明刻精本等珍贵图书286种6875册。1929年,丁麟年因病辞职移居青岛,随后参与少海书画社。次年病逝于青岛,终年61岁。
丁麟年的死亡,差不多带走了自1912年开始在青岛积聚的旧知识精英们的最后文化招牌,剩余的老官僚文人,不是已经远走他乡,就是几近苟延残喘,发挥不了多少余热了。但就如同死亡的自然轮回并不能消纳掉逝者的所有文化信仰一样,新生的力量也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丁麟年的下一代中,同样不乏传统文化的认同者,并且身体力行。这其中包括了少海书画社的成员,也包括了另外的继承者。《淮南子·泛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必得和之精。”“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新时代的大河奔涌,新旧思想泥沙俱下,后来的时间,继续验证着一个一个不同经历者的不同选择,是是非非,任人评说。
在丁麟年逝世的1930年,丁参与的少海书画社,和其发生联系的年轻城市一样,继续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年中,26岁的赫保真和郭味蕖两位潍县老乡一起,在青岛举办了一个书画联展。赫保真,字聘卿,潍县南关人,早年为潍县画家丁东斋、刘秩东弟子。1924年来到青岛,任青岛模范小学美术教师,1926年加入少海书画社。郭味蕖原名忻,出身潍县书香世家,和赫保真一样,自幼随家乡画家丁东齐、刘秩东习画。早年入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画,毕业后任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教师。1937年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临摹古代原作,并随黄宾虹学画论及鉴赏。1951年受徐悲鸿之聘任职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1960年任中央美院中国画讲师,后任花鸟科主任。1970年以“战备疏散”为由被迁返潍坊,次年逝于故乡。
1930年的青岛,一边是新旧交替的嘈杂,一边是小桥流水的恬静,两幅画面交汇在一起,就如同冰火相融,打了个招呼,就各行其是去了。本地尚能发挥余热的老知识分子,寓居者吴郁生为其一。尽管年迈了许多,但这个前内阁学士却也不忘济世救人,以旧作数件捐赠给了苏州冬季书画济贫会和苏州书画赈灾会。那里是他的老家,乡土乡音,寄托着他的文化根脉。在1930年代这个花样翻新的年代,除了喜欢看电影之外,吴郁生继续保持了一个老派文人的习性,像一个老古董,外面裹了一层洒满了花露水的牛皮纸,里面却还是原汁原味,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就是不小心扑通一声跌碎了,也会马上找个工匠,严丝合缝地锔起来。于是,锔者不愁没饭吃。
有锔者风范的,狭可弄锅碗瓢盆混口饭吃,宽可修治举凡政治国是、军事战局、社会疾病、文化纠纷等等,无一不能。大概在那个年代,有板有眼的潍坊人张同信,就像一个学医的锔者,开始在青岛信义会诊所坐诊,锔连生死。这个叫张同信的医生又名张执符,生于189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同年入潍县乐道医院任医师,后任院长,1930年到青岛基督教信义会诊所任医师。根据零星资料的记载,张同信这一次的青岛执业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返回了原籍。抗战结束后重返青岛,参加接收日伪财产,并再度坐在了信义会医院的椅子上。这一回不同了,他被聘为青岛信义会医院董事会董事兼名誉院长,可谓名副其实的凯旋。1951年信义会医院改为青岛医院后,张同信任院长。1956年革新研制成手摇磨针头机,1967年逝世。这一年,青岛烈日当空,盛行文攻武卫。
在1930年的青岛,所有疯狂的举动,还未曾完成思想锔合。是年最盛大的文人聚合,是国立青岛大学汇集的“酒中八仙”宴饮。梁实秋记:“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熟,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的宽敞的巿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碗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44]
如是,青岛和新月文人,和酒,和寂寞,和风花雪月,成就了别样的193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的第19年。一任外面的世界眼花缭乱,港湾里的文人“举重若轻”,不及于乱——不论是酒场争雄,还是文化论战、政治逐鹿。
如是,1930年的文人和青岛或蜻蜓点水,或一往情深,纠缠得不分你我。若干年后,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和事,被视若精神矿藏,供人凭吊。可到了这时候,已经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光亮之外,一切都陷入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