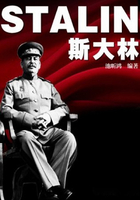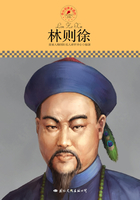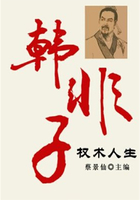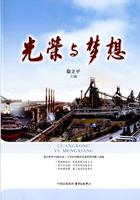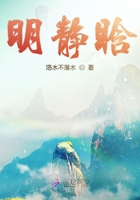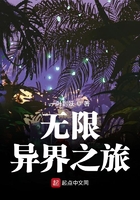在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一群操着砖头棍棒的男打手和挥舞着马桶刷把的女打手,在荷枪实弹的军警和身着灰布大褂的便衣侦缉的卫护下,狼奔豕突,冲进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雕花铁门。指挥者手持一根文明棍,他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的司长刘百昭。坚守在校园的二十多名女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紧挽手臂,拼死抵抗。男女打手蜂拥而上,拳脚交加,七八人或十多人挟持一个,将女生扭发倒拖出校门,捆塞进汽车,囚禁于报子街女师大补习科纸窗破烂、蛛网密布的空屋内。被殴拽的女生衣破发乱,遍体鳞伤。共产党员李桂生数次晕倒,后经抢救,方得复苏。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所谓“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一九二五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于同年十一月掀起了一场以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杨荫榆为直接目标的学潮——“驱羊运动”。一九二五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根据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开展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女师大学生组织起来,重新整顿学生自治会,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妾妇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女师大的地下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有些人还进入了领导核心。中共北京地委、北方区党委和市团委经常派人到女师大联系工作。在刘百昭率男女武将打入女师大的当天,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就受北京地委派遣,亲临现场,跟女师大学生并肩战斗。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是这次学潮的支持者。
一九二五年,是鲁迅前期战斗最为频繁、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一年。除处理教育部的日常公务和进行紧张繁忙的文学活动之外,鲁迅这一年还在七所大中学校兼课。青年们不仅通过鲁迅的作品得到精神的陶冶,而且在课堂上屏息静听着他的教诲。他幽默的谈吐,睿智的思想,乃至褪色的打着补丁的长袍,都给青年学生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青年们把鲁迅视为指点迷津的导师;正在找寻生力军的鲁迅,也把青年看成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当女师大进步学生吁请鲁迅给她们的斗争以声援时,鲁迅毫不犹豫,立即以同仇敌忾的精神跟她们同壕作战。
在北洋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两篇“呈教育部文”。他历举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他还同其他六名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被杨荫榆无理开除的六名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伸张正义。他公然违抗北洋政府教育部关于解散女师大的部令,毅然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因而教育总长章士钊于八月十二日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除了他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以示惩戒”。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跟进步学生在宗帽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不仅宣布义务授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由于女师大进步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北洋政府终于被迫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决定恢复女师大。八月二十二日鲁迅上诉平政院控诉章士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八月十三日,而章士钊呈请免职是在十二日,在前一天怎么可能知道后一天才发生的事情呢?鲁迅抓住章士钊的这个“倒填日期”的漏洞不放。这虽是一场硬仗,但由于鲁迅善于斗争,终于告倒了不但是教育部长,而且还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在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鲁迅撰写了大量杂文,痛斥“很想勒转马头”的封建复古派,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蟊贼。当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短暂避匿时,鲁迅基于对敌人不可改变的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鲁迅的这些作品,如闪电,划破了重叠的乌云;似惊雷,打破了窒闷的沉默。无辜受戮的学生读后“添了军火,加增气力”;势焰熏天的屠伯看了“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
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鲁迅还跟《现代评论》杂志《闲话》专栏的主持者陈源(西滢)等人进行了笔战。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甲寅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则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鏖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他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标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尚攻讦,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边。他们在文章中有时也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这场论争虽然常常围绕一些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
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鲁迅关于落水狗“一定仍要爬到岸上”的科学论断。一九二六年三月,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果然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的反扑。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三月十六日,又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忍无可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集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人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主持者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会后,两千多名群众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卫队公然枪杀徒手请愿的爱国民众,顿时弹丸横飞,血花四溅,酿成了死伤二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进步学生杨德群也在牺牲之列。诗人刘半农曾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悲吟: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天半黄尘翻血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
悲风带雪吹颬颬,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鲁迅是“三一八”当天下午听到这一噩耗的。当时他正在写一篇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杂文。青年受弹饮刃的消息传来,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抽刃而起,投入战斗。他迸发出火山岩浆般的炽热的感情,号召革命人民向屠杀者讨还血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血的事实使鲁迅认识到,旧中国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文学虽然是改良社会的一种力量,但单纯用文章“呐喊、叫苦、鸣不平”,并不会使“压迫、虐待、杀戮”革命人民的屠伯们立地成佛。
一九二六年八月,由于北方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京南下。他想利用这一机会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投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家庭生活集聚一点必需的钱,以免“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告别讲演。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