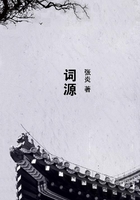“不知道,千百年后,小镇通史上会不会这样记载,敲响丧钟的人……苏良。”
少年躲在草药铺子里,苦涩一笑,面色因为这几日的接连不断的晦气事,愈发苍白了。
老酒鬼苏嵬是一个这场噩梦的开始,他只是小镇上首个意外失踪的人丁罢了,并不代表他也是最后一个。
而让小镇忧心忡忡、人心惶恐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随着东巷的猪肉铺子凌家父女的消失不见,然后便是龙须溪的钓叟,而后又是西巷的说书人,接着就是东巷整条大街的所有百姓……
先前的四场大病,带走了将近三成的百姓,已经让这个千年古镇气血两虚了,而紧接着的这场压轴戏,却是将这个数目提升到了五成之多,这个奄奄一息的小镇,已是有了日薄西山的趋势。
小镇百姓快被压的喘不过气了,走在四条小巷子上,看到的不再是往日的人海熙攘、摩拳擦掌,而是万人空巷、死气沉沉,他们都惧怕下一个莫名失踪的人是自己,但却忘了格物致知,探知本源。
少年在铺子里将那两条淡水鱼丢进锅里煎了,和肩上那不怕生的白猫,一同分了吃了。吃干抹净后,一人一猫,互相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都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不约而同地笑了。
少年填饱了肚子,戴上了那顶破草帽,出了草药铺子,沿着小巷上的青石,踏着劈啪作响的草鞋,便去了四巷交接处的夫子府。
到了眼前这间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高楼大厦门口时,苏良顿了下脚步,一路走来,草鞋的缝隙里夹杂上了不少泥石,磕着脚趾微疼,他皱眉的伸手摸了摸肩上盘卧着的白猫,大笑一声,踏门而入。
“还真是没创意啊。”
夫子府内,是如少年所料的场景,一人一壶,盘膝而坐,那人身材矮小,面色红润,显得精神抖擞,他似笑非笑的看着少年,丝毫没有因为后者的突兀闯入,而有一丝一毫的惊讶,脸上总是挂着招牌式的恬淡笑容,显得愈发高深莫测。
“当然没创意了,那些杂书闲传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矮小夫子微微一笑,拿起茶壶递到嘴边,轻抿了一小口,笑容更淡了。
“也是啊……”少年怔了一下,看向夫子的眼中多了些许莫名的情愫,良久良久,喟叹一句,默默的坐在了矮小老者的对面,也是粗鄙的学着夫子,依葫芦画瓢的盘坐下来。
夫子看着少年,似笑非笑,也不多言,只是淡淡的笑着,抿了一口又一口,壶里的茶水越来越少,偶得不经意间瞥见了那只白猫,只是淡然的看了一眼,那白猫便是立马缩起了身子,眼神恍惚。
对面正襟危坐的少年方才反应过来,怒发冲冠,面色愠怒,起身看着前者。夫子只是淡淡地回以微笑,河目海口,春风拂面,
“别动我的猫。”少年冷冷一哼,疾言厉色,吐气如冰。
“如你所愿。”矮小夫子丝毫不觉得半点窘迫,对着苏良轻轻点头,再次微笑。
“那些消失匿迹的人丁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心中自有答案,何须多问?”夫子叹了一口气,并没有选择回答少年问出的那个问题,而是反问一句,以进为退。他又伸手从怀中拿出一支木簪来,慢慢地递了过去,期间视线从未离开过苏良的身上。
少年始终抚摸着白猫柔顺毛发的那只手,忽然地止住了动作,不经意的将其毛发蛮横的扯掉了好几根,白猫痛苦的“喵呜”一声,伸出爪子报复性的蹭了蹭少年的脸庞,刹那留下了几道鲜红的抓痕。
苏良却是浑然不知,他只是傻傻的愣住了,良久,良久,良久,霍然皱眉,轻轻太息。
少年重重的闭上了双眼,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呼气吸气,吸气呼气,如此重复,少顷后,伸手接过矮小夫子递来的木簪,接过这木簪,他不由得发呆了。
他神情恍惚,一片朦胧,模糊之间,又是突兀想起了那双爱笑的眼睛,其倩影却是愈发模糊了,他目光如电,摇头晃脑,遂然愈发坚定了。
少年笑颜逐开,玩味的看了一眼那总挂着招牌式笑容的夫子,便是起了身,回敬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言语。
“那你呢?”
夫子缄默了。他没有回答。他闭上了眼睛。他吸了一口气。他吐了一口气。他仰起头又猛地抽了一口气。他睁开了眼睛。他看向远方。他满脸复杂的笑了。他坐了下来。
少年握紧了木簪,便提了提草鞋,转身离开了此处。
他并没有回到他该回到的那间草药铺子,也没有回到破旧的老宅,而是选择离开了这座千年古镇,离开生他养他的大青山,毅然决然地踏着坚定的步伐,迈向遥远的远方。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道路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
这个敲响了丧钟的少年,再一次地攀爬上了蜿蜒曲折的大青山,身姿矫健,健步如飞,他仿佛带上了所有的晦气事,悄然无息地离开了小镇。
站在大青山的绿林山间上,他回首萧瑟的遥看云里雾里的小镇,呼出一口浊气,豁然开朗,云消雾散。下意识提了提草鞋,目光如炬,无比认真,似要将这个平淡无奇的小镇永远的烙印在心中,不使其磨灭。
少年伸手打了个哈哈,对着青山绿水碎碎念叨个不停,戴上了破旧不堪的草帽,伸手摩挲着肩上白猫,双目淡若水,如脉脉春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一年,只身一人,背井离乡,他只有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