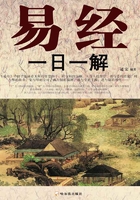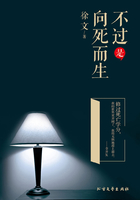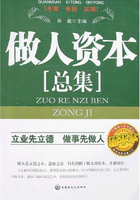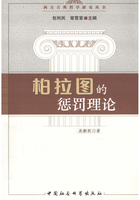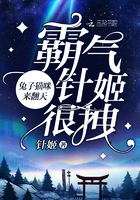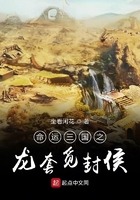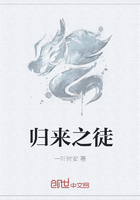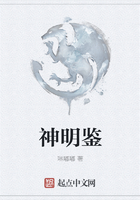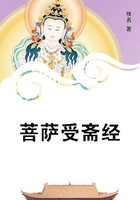道教宣扬神仙的存在,认为人通过修炼能长生不老,《西游记》、《聊斋故事》中也塑造了许多鬼神形象,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民间有神论的信仰倾向。儒家一般不相信存在鬼神,但对天命鬼神保持着某种敬畏心态,这种敬畏集中体现在儒家的道德生活以及丧祭之礼上。与民间有神论的信仰不同,儒家是从道德上、情感上来设定天命鬼神的存在,而不是从理智上肯定天命鬼神的存在。冯友兰认为,从理智上承认天命鬼神的存在,是宗教的一般特点,掺杂着迷信思想;而儒家从道德上情感上设定天命鬼神存在,则是一种诗与艺术的态度,不是宗教。儒家化宗教为诗、为艺术,这是儒家哲学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道德之天
从事天的观点,以看道德底行为,因此与道德底行为以超道德的意义。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冯友兰将中国古代关于“天”的意义归为五种:⑴“物质之天”,就是日常生活所看到的苍苍者,与地相对的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空;⑵“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也就是宗教所说的人格化的有意志的至上神;⑶“命运之天”,就是民间社会所说的运气;⑷“自然之天”,就是作为自然界整体意义上的天;⑸“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强调天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价值,人类道德生活的超越根据,道德律法都可以溯源于此。儒家对天的理解也是突出它的道德含义,没有将它视做人格化的有意志的至上神。在中国上古时期,这种观念是很普遍的。
远古先民对于雷雨闪电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就想象冥冥之中正襟危坐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是自然界的主宰,掌管着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以及各种各样事件的发生。远古先民称这个至上神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天”。从遗留下来的甲骨卜辞看来,这个“上帝”真是一手遮天的,天庭地府、六合内外、生物死物,都惟命是听。它有一个以日月风雨等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纯任个人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普通人哪里揣摩得透上帝的脾气,也听不懂上帝的“仙语”(如果能够有幸聆听的话),所以“天命从来高难问”。《书经·吕刑》记载:“乃命重黎,绝地通天”,“绝地通天”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重黎”就是普通百姓。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普通百姓被恶浊的人气包裹起来了,被断绝、阻碍了与清新的仙气亲近,无法与天神交流。按古人的说法,只有专门祀神的人即“巫”或“祝”,才能懂得天神的号令,与天神取得沟通。商朝的王公贵族还认为上帝是他们的祖先,因此他们经常受到上帝的庇护。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关于国家和王的行动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的方法,请求上帝明示,赐予福祉。
到了周朝,天的至上神意义的色彩渐渐淡化了,消褪了,道德意义逐渐浓厚起来。
《周书》上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说天是没有亲疏差等的,它执行惩恶扬善的统治功能,主要就看人的道德品格。《诗经·大雅·文王》载:“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只有那些敦行美德的人,才能与天命相匹配,以自己的善行求得更多的幸福。在这两段话中,天都具有人格化至上神的色彩,但是他的权威受到了限制,只是一个道德警察兼检察官。他也根据对人的审判,分配幸福的稀有资源,不过这位主管持心公正,有一杆公平秤,不会喜怒无常让人捉摸不定。大约上帝从商朝走到周朝,年纪大了,心态平和了。
《周书》与《诗经》中所讲的道德上的神,虽然没有把神看做统治一切的至上的主宰,但它仍然宣扬有神论。这种有神论与普通的有神论不同,它可以叫道德神学。普通的有神论则可以叫宇宙神论(把神看做宇宙的主宰)。当然,普通的有神论也包含有主宰人世间的道德行为的意义。然而后者只能叫神学的道德,这与前者道德的神学有着本质差别。西方哲学家康德曾就神学的道德与道德的神学做出区分,他说,神学的道德以神学为主,以道德为辅,道德只是神的众多的人格化的属性之一;而道德神学,则以道德为主,以神学为辅,神只不过是人的道德实践需要的一种设准。设准即假设,假设神的存在,因为有利于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于神是否真的存在,则存而不论。当然,周朝持道德神论的人们对于两者的区别,并没有如康德那样做出明确的说明。但是,他们着重于发挥天的道德意义,弃前朝的全能神于不顾,从这点来看,至少已经暗含了对于两者的区分。到了孔子的时代,“天”逐渐褪去了人格化的色彩,变成一种人无法预料的神秘力量,既不再是人类道德行为的主宰,更不是整个宇宙的至上神。《论语·阳货》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季自然更替,万物自然繁衍,不待上帝说话。这里所说的“天”被取消了话语权,已经没有人格化的意义了,但它还保留着人无从测度的神秘力量。《论语》记载,孔子“闻迅雷风烈必变”,即听见响雷,看见大风,孔子马上改了脸色。因为迅雷烈风这样剧烈的变化,是宇宙中某种神秘力量的骤然显现,也许在那暴怒的面容后面,上帝那颗温柔沉默的心正凝视着人间,所以孔子像见了国君似的,敛容致敬。孔子对宇宙中这种神秘的力量一直怀有敬畏之情,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即宇宙神秘的力量,孔子认为它与大人、圣人之言一样令人敬畏。宇宙中这种神秘力量是无关乎人的道德生活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作为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你诚心诚意邀请它附身,它一定会光临驾到的。为仁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苛责旁人,更不能祈望天命的恩赐。孔子认为,只要是依仁由义的事情,即使明知成功无望,还是要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地去做。当时的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就是说,道德行为不能由天命来决定,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它的动力来自于“道义”,而不是神。
宇宙的这种神秘力量,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日月起落,春秋更迭,沧海桑田,花落花开,潮奔浪涌,人事兴衰,无不体现着造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造力。因此宇宙的这种神秘力量,实在是自然界自身的内在动力。儒家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应该效法自然,在行为中再现宇宙的这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造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即健行不已,生生不息之意。天的本性是健行不已,生生不息,所以君子也应该像天那样,积极作为,奋斗不息。《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天命的本质是“于穆不已”(庄严肃穆,生生不息),即宇宙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以及生命力。所以天方成其为天,高于天下众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意思是说,天命之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以及生命力,何处不显示出来呢?周文王身上纯之又纯的道德品格,不就是宇宙生命力的光明照耀吗?
儒家将天命理解为宇宙生命力,却拒绝给予它一副人的面皮和人的心脏。同时,儒家也把道德行为的原动力追本到宇宙生命本体,这不仅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寻找到了超越于尘世的依据(如若单就尘世谈论道德原则,无论你抬出看起来多么无可置疑的“公理”,听众总可以质问你:你的“公理”之母又是什么呢?我不信你的公理,“公理”其如我何?你瞠目结舌,无可如何。要是你为道德信条找到超凡绝俗的靠山,震慑力可就大多了。),而且也将人类道德行为的意义上升到天地(宇宙)的境界。冯友兰讲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从天地(宇宙)的高度,从宇宙的大生命的高度,来看待人在尘世间的道德行为,从而使人的道德行为具有了超道德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下的“天命”,虽然仍是冥冥宇宙中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但已不是可以主宰世界的人格化的神灵,而是宇宙生命活力的象征,也是能提升人的精神层次的终极依据。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在这个之前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所谓“而立”,可不是指山东军阀韩复榘解说的“能站立起来”,没听说过孔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三十岁上给治愈了。“立”是指“立于礼”,能够按照儒家的礼法规则,循规蹈矩地去做事,但还未能从天命(宇宙生命本体)的高度去理解人类的道德生活,未能将儒家的礼法规则转化成自觉自愿的道德动力,依照冯友兰的说法,其境界只是达到了道德境界而未上升到天地境界。“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直到五十岁才理解天命的含义,知道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与天命遥相契合,从而深入体验到宇宙的大生命。宇宙的大生命充于体内,也就可以外化于规矩,将人类的道德生活美学化,进而获得一种宇宙的永恒的生命色彩。所以孔子叙述其五十岁以后的精神历程是“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天命是宇宙的大生命,生命本体,这一点后来宋儒谈的较多。在宋儒看来,宇宙万物并非死的物体,而都是活泼泼、光灿灿的生命。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何以故,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道:“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认为“天地”是有生命的,他从天地的生意中感受到精神的陶醉,从自身的有限的感性生命中挣脱出来,解放出来,体验到宇宙生命本体的无限和永恒,广漠无垠而又亲切感人,从而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也提升到天地的境界。因此,在宋儒那里,天命已没有了丝毫神性的色彩,它只是表达圣人所具有的天地境界和宇宙情怀的一个超越的标准。或者说,它表达的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种神性实体。境界高的人能够知天命、顺天命,体验宇宙的大生命;境界低的人则不能知天顺天,对宇宙生命活力的流动视而不见。儒家常说,人与宇宙万物本为一体,如宋儒张载说:“民吾同胞,物我与也。”程明道说:“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其实这是从天地境界上讲的一体,因为在天地境界上,人能看到宇宙的生命活力,体验到宇宙的生命本体,对于没有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只见得物我两隔,人心疏离,是谈不上人与万物为一体的。
虽然儒家讲的天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造力;天命为人洞达,为人顺从,可以使人提升到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但天命仍然是道德之天。按冯友兰的说法,孔子的知天命、顺天命,是对儒家外在礼法规则的超越,这位仁者的内在生命体验挥洒出来,就是顺乎人情、合乎理义的美言善举,天然的尽善尽美,绝无雕饰痕迹。这是一种美学化的天地境界,好比一位大书法家从描红起步,到后来臻于佳境,随意挥毫就妙到巅峰。在这里儒家把人类的道德价值投向天命(或者叫天道),使天具有道德的意义,其实是在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寻找一种超越的先天的根据,赋予人类的道德行为以永恒而普遍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儒家对天命的态度不同于宗教,它是一种高于宗教的哲学态度,在儒家那里,根本不存在人格化的、有意志的至上神。因此不可把儒家的天命观视做道德的神学,而应叫做道德的宇宙论(天地境界论)。在有些地方,冯友兰也把他的天地境界称做宗教的精神境界,这是从广义的宗教来说的。只要追求一种超越感性物质世界的境界,追寻一种终极至上的精神价值,不管是否崇拜神仙上帝,这样的信仰形式都可以叫做宗教。儒家的天命观符合广义的宗教的定义,只不过是无神论的,不同于有神论的终极追求。
丧祭之礼
儒家对于丧礼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以求情感之慰安。儒家所宣传之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
儒家把天看做是道德之天,否认天是人格化有意志的至上神。儒家是无神论,否认有神论。但是,儒家在关于对鬼神之说的讨论中,又似乎不是完全的无神论者。《论语》载: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他“问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说的意思是:人际关系你还摸不清门路,人鬼关系你怎能找着北?生存问题尚且糊里糊涂,死亡之事如何理清脉络?孔子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说明他敬畏鬼神,又要远离鬼神,这算是智,否则就是不智。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大概是模棱两可,不明确地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强调鬼神的存在。
为什么孔子不旗帜鲜明地打倒鬼神,或者爽爽快快尊奉鬼神,自己当个人间教主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引用刘向《说苑》的记载,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