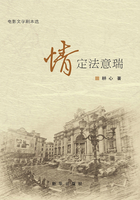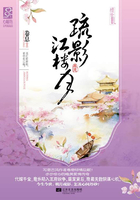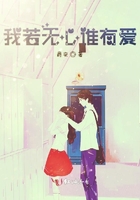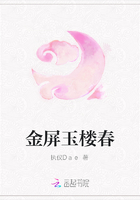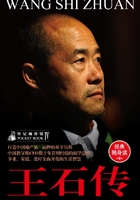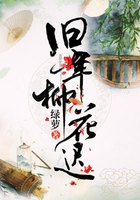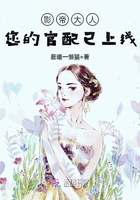在白马湖派散文家中,丰子恺先生是独操散文一体的。他的“写文”,自称“随笔”,而在我看来,多是理趣之文,即属于审智散文。散文除了抒情叙事,还有更重要的智性议论。也就是说,除了情趣,还有智趣。从理论上,强调抒情和叙事,也就是感性的审美价值;从趣味上讲,就是局限于情趣。然而,散文还有它更为深厚的智趣的传统,尤其在五四发轫期,与西方的随笔有了某种接近,而西方随笔多以智性思绪为主,这就助长了散文的智性深度。对于此,丰先生似传承得很好,又运用得很好。他的文体,既有传统笔记的风味,又亲炙西方随笔的格调,于中闪烁着智慧的辉光。当别人在晚明性灵小品的影响下,向着叙事抒情的纯文学方向走的时候,丰却直达智性,构建智趣,独守审智散文。他行文舒徐、自然,犹如那袅袅的“香篆”。据说,他写作或绘画时,伴以案头的炉香,熏闻香篆的烟息,这正是他那独特性格和审美趣味的表现。
散文要审智,也就是说散文要有很大的智慧的思想容量。1921年,周作人揭载于《晨报》上的《美文》,虽然很短,只有千把字,但却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经典。你能说它不是审智散文?显然是。丰子恺的散文除了生动的情趣与隽永的理趣外,还有一种新的趣味,即智趣,把诗情与智慧结合起来的趣味。“他谈高深的艺术理论问题,最喜欢举浅近的、人所共知的例子;若论深入浅出,趣味横生,恐怕只有朱光潜的《谈美》可与匹比。”此乃丰氏用《缘缘堂随笔》的笔调来写的。而朱光潜用的是散漫的说理文。两人皆用审智散文笔法写。丰子恺的《少年美术故事》,写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又可以和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相媲美。说到丰的行文,有人如此评论:“他只是平易地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这也是他们都是白马湖派散文家之故。
丰之散文创作始于1922年,其时正在白马湖畔与宁波的奉化江边。他在口舌之余,孜孜于笔耕,所成散文后来结集在《缘缘堂随笔》中,此书给他带来莫大的声誉,尤其是日译本的问世。日本学者谷崎润一郎读后曾表示:“他所取的题材,原本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这种“风韵”,即表现在取材于日常生活,追求弦外余音文外余味。所谓“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可解之佐证也。丰氏的那些文字,好像没什么“中心”“纲目”,说是一苇航船且行且泊,卧看云起,月下小窗,也差不多。倒是随笔的意思。自然也有的描绘自然物象,借物抒怀与阐述哲理;有的以自我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的表现,示出一片纯净高洁的心灵世界。此类文字一般被归入散文了。《山水间的生活》《杨柳》等篇皆可视为代表作。《杨柳》写得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曲径通幽”,是园林艺术中一种引人入胜的布局,披花拂柳,沿着曲折的小路向深处探寻,常常会引起人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叹;而每一曲折,又总是呈现一种新的境地,给人一种新的享受;特别是“曲径”最终所达到的“幽”处,更是令人神痴心醉,惊赞不已。这是一种“曲”的艺术。作者在外围做足文章,旨在修筑“曲径”,以便“通幽”,以便加强衬托,突出将要点赞的杨柳——“这种植物实在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现代散文咏赞树木花草借以寄寓哲理的,有郭沫若的《银杏》、茅盾的《白杨礼赞》、叶圣陶的《牵牛花》、苏雪林的《秃的梧桐》等,都为人们所传诵。《杨柳》显然也是一篇佳构。丰子恺对杨柳情有独钟,他在春晖时自有小屋坐落在白马湖畔,背山面水,因在它院内种了一株小柳,故称为“小杨柳屋”,说其小,客厅小得“像骰子似的”,“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正是在这间屋里,丏师、佩弦、朱光潜和二刘(薰宇、叔琴)等,相聚在一起,有时教研课务,更多的则是切磋文事。天气好时,他们便会坐在柳叶茂盛的树底下,大伙嬉笑着打开酒坛,掰开几颗落花生,然后,一直坐到月上中天,酣醉而归。“小杨柳屋”之聚,孕育了白马湖文派,也就有了白马湖散文佳作。我以为,这之中可以悟出丰子恺为何这般喜好柳树进而加以礼赞的原因。
写于1923年5月14日的《山水间的生活》,抒写出丰在春晖生活的独得的感兴。全文用对比的手法,道出山水间的生活的意义: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说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固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寞而邻人更亲。
这一段文字,亮出了一个创作者的人生的旨趣:他热爱白马湖的清风明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春晖,一切皆是纯洁、静雅的,以他为人生的态度找到了生存空间与处世方式,并以此为联结的精神纽带走到一起。“清静的热闹”的胜境,不就是中国新文学在浙东的一个沙龙吗?这是一个充满生活艺术化的文学沙龙,它以夏丏尊为轴心,团结一些志同道合者自然形成。参与的人虽不多,但它拥有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这是参与者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完美人格力量。认识此,就不难理解丰子恺为何觉得山水间的生活有意义了。
夏丏尊称赞丰子恺“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不为成见所束缚,每每通过自己的体察,从平凡中悟出自己的哲思:把日常生活艺术化。这是丰子恺散文之特长,亦是其散文智性的表现。至若他的关于审美教育(丰习惯于称之为“艺术教育”)的文章更属于审智散文。这些文字自白马湖时便开始写作,而且写了好几篇。如下所示:
丰子恺发表在《春晖》半月刊的文章
期数 时间 题目
一 1922年10月31日 艺术底慰安
三 1922年12月1日 青年与自然
六 1923年1月16日 美的世界与女性
八 存目,时间不详 本校的艺术教育(上)
九 存目,时间不详 本校的艺术教育(下)
十三 1923年6月1日 山水间的生活
十四 1923年6月16日 唱歌音域底测验
十五 1923年7月1日 唱歌音域底测验
十六 1923年10月1日 裴德文与其月光曲
十八 1923年11月1日 白马读书录
二十二 1924年1月1日 英语教授我观
二十四 1924年3月1日 白马读书录
二十五 1924年4月1日 白马读书录
二十八 1924年5月1日 白马读书录
三十一 1924年6月16日 艺术底创作与鉴赏
时间不详的:《远近法》《艺术》(五夜讲话)
其实,丰子恺在行将离开春晖中学的1924年岁寒,还写过一篇题为“由艺术到生活”的审智散文,文之结尾处,题“1924年12月24日在白马湖”。这篇散文,检阅丰子恺所有著述(包括《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丰子恺集外文选》殷琦编,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5月版)都未收录。佚文3000余字。其起笔之由头为“一位非常热心于提倡艺术教育的林黎叔先生”造访丰子恺,“热心地”与他“谈论育德女校学期艺术科的计划”而引起的“种种感想”。内文分两大段:(一)艺术是超现实的。(二)艺术活动是无我的。这篇佚文最初披露在我的“白马湖文化研究”博客上,时在2010年3月16日,后又在拙著《书味醰醰——从宁波到白马湖》(宁波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中予以传布,并注明发表处与发表日期——1925年1月1日《四明日报》(此系宁波早期的大型报纸,诞生于1910年,停刊于1927年)。
丰子恺的此类著作,皆是对青年学生而发的,可见他对青年美育教学的用心。丰先生说得好,“艺术教育是人生的很广泛的教育,不是局部分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诸如“画与唱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最后的目的,在乎养成像艺术制作(作画)与鉴赏(看画)的热情的爱的精神,把这样的精神应用于一切生活上”。丰子恺的这一思想,到了1926年,在《废止艺术科》中说得更直白:“图画科之主旨,原是要使学生赏识自然与艺术之美,应用其美以改善生活方式,感化其美而陶冶高尚的精神。”这就告诉我们,美育不仅仅是艺术技能培养这一“授业”层面上的外在呈现,更因其具备在潜移默化中直达心灵深处的特点,在“传道”层面能够传递真善美和向上向善的力量,引导青年学生激发高尚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这在当今似也有指导意义——加强对美育育德内容的顶层设计,让美育教化的方向植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其独特方式落实。值得一提的是,读这些美学知识普及性之文,感到的愉悦并不亚于读他的其他散文,这大抵是审智散文之故吧。
《美的世界与女性》亦是一篇美的教育的智趣散文,载于1923年1月16日《春晖》第6期。丰在文中表达了他的真善美合为一鼎,这个鼎是一种复合建构的观点:“向来的教育,偏重真善,忘却了美。就是重视知识道德,看轻美育”,所以要“提倡情育的艺术教育……叫人们从美的世界里得到神圣的爱,为了人们的幸福”。事实也是这样,知识、道德、艺术,三者共同参与人格的塑造,真、善、美的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完整的人格。因为该篇原为在宁波女子师范的讲演稿,其结语以气骋辞,亢奋有力:“我要对于现代的女性赞美且祈祷:‘一切女性皆优美。愿优美的女性,引导一切人们向美的世界去!’”
刊载于1923年10月1日《春晖》第16期上的《裴德文与其月光曲》也是一篇讲演稿,为春晖中学的“五夜讲话”(即每月5日、15日、25日晚上三次)所作。这种知识性的学术讲座,作为“对正课的帮助”,是春晖中学老师“很觉得可以自慰的一件事”。丰先生自然笔舌互用,乐意为之,丰演讲后,还在清风明月之夜,即兴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曲。“真是凉风习习,柳叶微飘,月光洒地,乐声悠扬。学生们都为美丽的白马湖景色和裴德文乐曲的优美旋律所陶醉。”“裴德文苦闷的生涯,听了使我感奋,月光曲的故事,尤使我引起怀古的幽情。半时间悠扬的琴声,使我初听钢琴和音乐没有感情的一个人也很动情!静寂中只有琴声和一个斗火虫的飞声,以外便没有了。”春晖早期的学生这样回忆着。从上述丰氏诸文似可看出,早期的春晖中学已经践行“智、德、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其中美育,诚是塑造完美人格过程中所必备的——“美是真与善的统一,美是真与善的完成,这三者相济,便完满了人格”,才成了人格完美的人。早期春晖的人格教育的成功,与丰子恺的为美的教育而鼓呼的这些审智散文是万难分割的。可喜的是,这些智性十足的文字于淡逸中透出,审智的抽象在审美的感性中传布,难怪乎其同道朱光潜云,“从纷纭世态中挑出人所亦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鳞半爪,经他的点染,便显出微妙隽永,令人一见不忘”。也如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般,“只是疏疏朗朗的几笔,然物类神态毕在壳中了”。智者哲思充溢其中。
散文似乎是一种“人书俱老”的体裁,“庾信文章老始成”。故有人说,丰子恺晚期随笔“超脱洪涛汹涌的尘世……将人间事提升为哲学思维奋力垦拓出的新亩,弥足珍贵”!而丰子恺先生长子丰华瞻则认为:“丰子恺最精彩的作品是在他年轻时写的……这些作品(指晚期作品)不能代表父亲的散文。”我赞同后者的说法,丰老先生精彩的作品似在白马湖时期,此时,他的为文之贯通智性和抒情审美的才气已初露端倪,故本文举证的多是丰氏的白马湖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