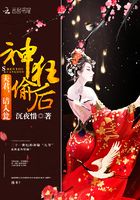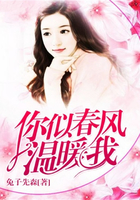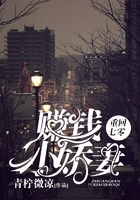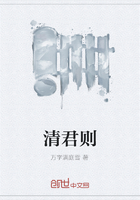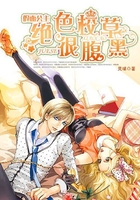船还在江上行,已不知是第几个春秋。这一次,我去普安,长江支流,磨刀溪边的一座古镇。因长江涨水,普安也被部分淹没。我问船上的人:普安为什么叫普安?没有人告诉我。
旁边一位老人说:“普安是农村一个乡,挨水边上,原来有土地,有房子,现在是水……我老家不在这里,在新津。”我再问什么,他都说不晓得,但回过身来又说:“这里是垮桥,五几年就垮了;那边是竹溪……”而随后话题一转,谈起他的生意经。
“这里山上有动物,我们来收一些动物。像白密子,很好吃的,价格贵;长得就像猫,灰颜色的,头上有一杠白的,尾巴那么长,那种肉是一级的,光是瘦肉,没有肥肉。还有一种叫土钻儿,矮脚、短尾巴,肉很多,是白膘,价格便宜些,像松鼠那个样式,大的有二十几斤。山上还有蛇,有一种毒蛇我们喊它钱串子,价格最高,一条五六斤,能卖好几百。有的人怕受毒,有的不怕,专门爱吃那种毒蛇。这种蛇只有在云阳,下川东这边才有,成都那边都没得,上一斤的我们就收,收了就和老板电话联系……”
我听得有趣,再看这个小老头长得精灵古怪,活像川剧中的丑角儿。
船还在前行,我又来到船尾。白塔出现在山上的时候,也在眼前漂移。一位退伍军人告诉我,这是清代顺治年间,为镇河妖而修建的文峰塔。而这里是新津生态保护区,原先的居民靠打鱼为生,现在大多作为生态移民,搬到了外地或云阳新县城去了。
这位退伍军人名叫李咏,这次回乡探亲,一路为我当向导。
前面是水磨乡、四方石、观塘口,岸边青草、红土间,现出一道道地基,房屋已经不见了,淹没了……
再前面就是三山嘴,李咏指着山上说:“我们家就在那座山上,树桩那里可以下去。原先这里河道很窄,枯水季节,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走过去,现在涨水了。”果然,绿水宽阔,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出处,只是缓缓流动,群山依旧安宁。普安普安,我一路念着你的名字,感觉像一种祝福祈祷。
“这里原先就是观塘湾观塘村,”李咏又说,“原先住着百十来号人,岸边种的都是柑橘,现在淹没了,移民迁到新疆、上海、陕西,还有重庆江津……”
船只向着山里缓缓行进——“再往前就是和平村一组、二组,原先水边是普通公路,再前面就是箭楼溪,从前岸边都是房子……”李咏说,而现在空空如也,只见青青草坡。
姚家坪到了,李咏在这里下船,下船之前还指给我看:“我们家就在第一个山头,那儿有一个红色标记,都是移民房子,从水边搬上去的,原先水边的房子没那么好。”
船继续前行,前面就是普安,普安再下面,就是小河沟和龙角。
我在普安下了船,之后走上一坡石梯,在梯坎上的第一座旧房屋里,看见两位妇女正埋头做针线。我上前问什么,她们都说:“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于是慢慢说。她们这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来意。
我问:“这里原先是什么样的?”
她们说:“河边上原先是个坝坝,有房子,也有地,都淹没了,居民都搬起走了,搬到了江西。这会儿街上人少,都在忙活路:插秧、割麦子、收豌豆……”
我又问普安的来历和从前的事情。她们说:“这要问六七十岁的老人才知道。”
“那你们认识的老人当中,有没有谁知道这些,懂得多的?”我问。
“有个叫李良之的老支书,他懂得最多,”她们说,“他家就在上头。”
谢过了她们,我起身就去找李良之。谁承想,刚走上几步石梯,一转弯,碰上一个瘦小的老汉,穿一件白衬衫,头戴一顶破草帽,正在干农活儿。
我说:“我找老支书李良之。”
他说:“我就是。”
我正欣喜,并询问普安旧事,没想到老支书瞪着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身份证拿来我看一下。”我顿时感觉浑身冰凉。
一时间难以接受,我说:“那算了吧。”转身就走,心想,历史给你一次机会,你不珍惜就算了。而回头想来,懊悔不已:明明是历史给我一次机会,我没有珍惜。
对外来的陌生人,老支书保持革命警惕,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对此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为什么不能再耐心一些,掏出身份证让他看一下,仔细审查一番又何妨?
毫无疑问,老支书必定了解普安历史,连同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而这一切就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被错过了。怎么办?已经转身走了,几乎刚走两步我就开始后悔,可又没有勇气回头,只能继续往前走,而心里还在恶意地想:让你不安,让你后悔去吧。可最终后悔不安的,是我自己。
就这样走进普安老街,一条深山古镇的青石板街道,两边是上世纪的房屋与生活,甚至更早;好熟悉的街道,很像是丰都旧城的鸦鹊街,老作坊、旧商店,一切都那么相似,只是鸦鹊街已经消失;同样是一位老人,坐在烟酒糖果店门前,像是在等我。我同样用心询问,然后就搬个小板凳坐下来,听老人讲述——
“我叫王茂德,己卯年(1939)出生,今年七十几了,老辈子都是做农活、种庄稼,在普安住了几百年,好多辈人了。我爷爷叫王齐斌,父亲叫王家方,我妈说,我的名字还是我爷爷起的……原先下面都是老街,我们是移民搬上来的。水没淹没之前,只是个溪沟,船到不了,要出远门,去云阳,都是打旱、赶车,现在水涨了才可以赶船。”
“普安为什么叫普安,也说不清楚,只知道这里有一个小地名叫马安山。原先高头还有些老房子,后来修公路拆了。解放前,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大地主叫李祖翁,后来也没有枪毙,自己上了岁数死了。我们小时候见过的一些老辈都过世了。”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去了双门铜厂挖铜矿,后来又去了共和铁厂、国营洪坪铁厂挖矿石、挑煤,之后又转到董家坝铁厂。我们在厂里没有吃到亏,在洪坪,一个月吃47斤,一顿半斤。在董家坝,一个月吃到53斤。直到1962年,我哥哥带口信来说:‘兄弟,你回来,把妈妈看一下。’听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就把铺盖背起,请个长假回来了,后来就把煤场工作丢了,洪坪铁厂补发的工资也没得到,到现在七十几了,也没有退休工资。回来搞农田基建,几个队扯伙,你到我这里插秧,我到你那里收割……”
“之前的灾荒年,我没在屋里,屋里很死了些人——我们队长保存粮食,关键他不拿出来吃。我们家有四兄弟、三姐妹,加上我父母总共九口人,我父亲,还有我两个兄弟王华德、王俊德都是饿死的。我幺兄弟死的时候才二十一岁。父亲死了没烧,就在老屋后头埋的,木头都是一垮一垮的,几个人挖个洞洞就埋了。两个兄弟更是,丢在后山就瓮在那里,当时没有劳力。”
“我们家成分不是很好,老的是个富农,人家就欺负他们,不准他们吃,不准他们穿,儿媳又打他们,两个老的在屋里吃了亏。年轻人铺盖都不给他们盖,他们一天到晚就在屋里睡起,屋里犁头、锄把、铺盖、衣服什么的,都给拿完了。当时我爸死了,我妈躺在床上说:‘你们东西莫拿,我后人回来还要种庄稼。’他们还是拿完了。当时是在兴隆,住的是哥哥盖的土房子。因为成分不好,家里一年到头大气都不敢出,被人欺负,那些人跟你说话腔调都不同。别人把红苕吃了,红苕皮抠下来丢在我们家门口,就说是我幺妹吃的。”
“有一回,我妹妹在山上割草,他又把红苕皮摔在我们家门口,又说是我妹妹又背了一背红苕回去。我那时年纪轻,性子有点儿刚,就把他收拾了一顿。我说你又来拿铺盖啊!”
“我妈妈给生产队喂牛卖牛粪,一天能得12分(牛粪可以撒在地里做肥料)。有一回,我妈累了,坐在那里歇凉,红宝队的看见,就叫她快起来干活儿。红宝队是那些积极分子组织的队伍,专门在那里监督,又不准你吃烟,又不准你歇凉,黑天还要你打夜工,这个队做了,又转到那个队去做。天啊,光是干活儿,你要站一下,棒棒身上打唉!那些积极分子,就坐在那里喝开水;你们那些莫想喝开水。我妈后来就是给他们整死的,在老君六队,以前叫兴隆六队,属于云阳普安乡,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
“我妈妈叫李良英,是李家湾的。当时也没个船,长阳洞有个医生叫王家瑞,我们走了十几里路去他那里诊病,中药一包一包抓回来吃,还是不行。王医生说:‘不行了,红宝队的把她整着了。这个病是心情引起的,治不好。’我妈妈是1963年死的,葬在老君六队。父母亲的坟没在一起。我们每年正月、清明都去飘红挂纸。”
“我妹妹王德英,原先也是种庄稼、喂牛,母亲去世后,妹妹出嫁,走之前把土地退还了。我们原先在老君六队,一个人有六丈多地。妹妹嫁的一个老公跟我们是一个村的,原先是兽医,后来也没有那个行业了……”
“我妻子也是己卯年出生,五十八岁得病死的,我跟她1962年生过一个女儿,生下来就死了。我现在这个儿是过(继)的,叫王季强,1964年出生,原先是五间(小地名)的,父亲死了,屋里有三个儿,他是老三,就过(继)给我了。我送他去学校读书,上的是这里的普安小学。普安小学原先是座观音庙,拆了建的小学,坡坡上还有一座张王庙也拆了。”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里分成两派:‘1127’和‘红云’,互相打,我们在厂里,那时乱得不得了。两派都是农民,整毛了就打一架。毛主席一下就收拢了,他老人家说:‘乱是乱的敌人,锻炼了群众。’”
“现在就靠儿子、儿媳开的这个杂货店求衣食,生意不好……我们在老君六队的两间老房子都卖了,土地给了别人,农转非之后,买的社保。”王茂德老人如是说。
坐在普安老街的杂货店门前,与王茂德老人聊天,感觉时间连着青山,一下午刚过了一半,已经历了沧桑岁月。
再往前走,只见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站在门前,正用一口大铁锅炒菜、做饭,旁边一群小孩儿跑来跑去,玩得正开心。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玩。老先生搬来一张凳子给我,我就坐下来和他聊天。老先生名叫陈真俊,壬午年(1942)年出生,今年七十二岁,原先在普安丰和滩,褚家梁老七组,来普安六七年了。
问及前尘往事,陈老先生说:“老辈子死了多年了。爷爷叫陈长顺,父亲叫陈敬武。我们苦了一辈子。父亲死的时候,我才十来岁。我十四五岁就去大办钢铁,到洞鹿挑焦煤、挖矿石、锯黑棒槌,后来又去红光铁厂。红光铁厂下马之后,再到故陵铁厂,然后又去南溪修路,到鱼泉铁矿打矿石,那里还有饭吃。灾荒年间,我妈妈和我一个兄弟,在屋里饿死了,还有一个兄弟给出去,给到狮子堡陈家屋里,也还是饿死了,死的时候只有十来岁……劳动力走完了,田地都荒了。”
“我1958年离开家,1961年回去。等我回家,瓦片都没得一块;大办钢铁的时候拆的,拆了炼钢铁;老房子变成了空地,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成了一个孤儿,生活慢慢来求。先是住在别人家,后来自己搭个草棚棚,在生产队挣工分,种芝麻、绿豆、苞谷……”
“我二十七岁才在龙角结的婚,妻子姓沈,我是上门女婿,结婚三四年她就跑了。她在妈屋里,随时跑唉。我跟她没有小孩儿。后来我又回老凼子里,找的第二个妻子叫丁放珍,是兴隆的,和她生的现在这个儿,在丰和滩褚家梁。原先那里房子、田地都有,现在淹没了。我们那个队一百多人,搬了没有几家了。现在褚家梁的房子都是要垮了的……”
“儿子、儿媳在浙江打工,我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带两个孙儿,他们在这边普安小学读书。我有那么多病,哪里带得了娃儿?拖起哼哼颠颠的……”陈真俊老人边说边喘,“我有肺气肿,主要是从前下力下重了。”而后他又说,“要是我妈还活着,现在有九十几了。”
我默默听着,并详细记录。我知道这些“细节”与“凡人琐事”的价值。是的,无需争论,只需用心记录。时间终将证明一切。尽管时间卷曲,脚步沉重,我庆幸自已依旧独自前行。
道路尽头出现一片田野,田野连着青山,山坡下一对老夫妻正在门前干农活儿,旁边的一间土屋被夕阳映红。在这座土屋前,我又遇见一位老人家,正和他聊天的时候,山坡上还站着一个老人,他让我上去,我让他等等。普安作证,江水作证。
而这会儿,我正坐在土屋门前,跟我说话的老人叫李从维,庚午(1930)年出生,老家在新津口。“老辈子都是挖泥培土,”他说,“解放前,新津口有一个大地主,叫王维诚,有一百五十多石[92]。他是个地下党员,死了不到两年就解放了,云阳来的干部都说可惜了。这个王维诚最恨棒老二,专门惩治他们,为老百姓办事。解放后,他家的土地、房子都分了,我们家也分到了,一个人分到两亩多地,还有砖房……土改的时候,嘴巴揸得那么大,你不揸大点儿不行。”老人笑道。
“后来大办钢铁,那最苦了!我们都去的,从新津口到流湾坨,走两天,流湾坨去了有一万多人,在那里挖矿炼铁,炼出了铁来。后来,我又去了磨子坪炼铁。男劳力都去炼铁了,女的在田里用牛耕地……天哪,饿死人多!家里穷,人又走不动。我们家就饿死了六个,爸爸、妈妈、我两个兄弟、两个侄儿,死在新津。我没在家吃集体伙食,十二岁就跑出去了,跑到湖北的利川、板桥当建筑工……那时候是各奔东西!人强的就活下来,不强的就亡了。”李从维老人如是说。
“我炼铁五年,逃出去十八年,回来收了亲,头年看起的,第二年结的婚,生了个女儿。我回来的地方,在新津口磨子坪,在那里做瓦,你给钱就挑去。我们那里也有几户烧瓦的,没有我的技术好。现在新津口的老房子都淹没了,我就搬到这儿来,帮女儿带娃儿……”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位“头年看起,第二年结的婚”的妻子一直在旁边干活儿,老太太用一个竹簸箕在抖着一大堆干豆子,灰尘扬起来,在夕阳里化成一阵阵烟雾。
抬头再看,坡上那位老人还在等我。而等我从旁边绕上去,那儿已经站了三四个老人了,还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小姑娘站在旁边听我们说——
提起往事,大家都说到王维诚,此人原名叫王圣金,小名叫润秋,是普安乡大地主,老家在回云村,但他本身是个地下党,和他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还有清水塘的刘茂行,云阳的赵伟、赵云,他们曾去刺杀云阳县国民党的马委员长。当时马委员长正在打麻将,王维诚带去的刽子手害怕了,怕得手抖,没有打中,他们都逃走了。我们听那些老人讲着。
王维诚是个厉害人,家里有几支枪,还有一支队伍,棒老二都怕他。当时共产党躲在他们家里,没有哪个敢去捉,也没有哪个敢找他的麻烦。但是后来,花名册上把他的名字搞没了,就没有他了。王维诚1948年就死了。
解放初,打了一些地主,在丰和坝坝,两边梁梁上都架的机枪;那时我们才十几岁,亲眼看到的,像丰和最大的地主倪二老爷,就是民兵用手枪打的。当时号称是“万人大会”,二十几个村的人,大河坝都站满了。枪毙的人都被扎起来,有严武承、罗治郡、向社阳、丁树忠、王学成,这些人当中有恶霸地主,还有乡长,王学成就是乡长。当时要去王学成家里搜枪,他拿人头担保,说他家没抢,结果搜出枪来,王学成就给枪毙了。他是好人唉。老人们说。
高峰村的王安竹老人(1932年出生)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从红狮去的洞鹿,走百把里,去‘万人铁厂’。上面说的是,云阳要搞个‘万人铁厂’,他们听到说是要搞一万个铁厂,在兴隆、双门、共和、石龙都是铁厂……我们去的是洞鹿铁厂,1958年10月去的,干了8个月,去山上砍树,树都砍光了,烧‘黑棒槌’,还是只炼出些块块铁、条条铁来的,我们都看见的。到1959年5月,洞鹿铁厂垮了,人都分散到故陵的红光铁厂,小地名叫红瓦屋,那是云阳县的总铁厂,真正是万人铁厂。我们共青团员就钻到炉膛里筑炭道,里头红彤彤的,钻进去五分钟就要出来,我又在那里干了一年多,1960年回到普安,那时候伙食团还没有下放,1961年伙食团才下放。”
“说起1959年,那我们就晓得了。”原共和六队生产队长吴智深说,“越是好地方的凼子,人死得越多。为什么?县委工作组,专门住的是好的凼子,像我们丰和的正坝、郎家的箭楼,我们晓得的。他一住,就管得紧些;山坡凼子,反而管得松些,你在山上偷点莫子[93]也得行;特别是平原凼子,死得多些。”
“他怎么管?比方说,你这个人饿得不得了,跑到坡上,捡个生红苕来吃,如果队长看到,就把你弄去开斗争会,不管你成分好坏,把你弄来一顿毒打。他干部自己在伙食团弄些吃的。还不准你开伙,你悄悄在坡上弄点莫子回来,还要等晚上,人都睡静了才来煮;那些当干部的,积极分子,他就在那儿看,看到哪儿冒烟,他就去喊你开门,开了就去收,就是那个情况……”
“灾荒年,就是1959年到1961年间,我父亲饿死了,哥哥也饿死了,姐姐去了铁厂。我那时十二岁,在学校读书,早上脚还不肿,下午也肿了。生产队种的萝卜埋在地里头,我偷偷拿起来,把泥一抹,咬两口,再埋进去;或者揣几个回来,等天黑了,找个罐罐,慢慢煮,管它熟不熟的,吃了就好。伙食团是定量的,我们学生娃儿后来每人每顿一两菜糊糊,只有半碗,怎么够?我妈妈四十岁生的我,她那时候就在生产队干活儿,掐点儿茶叶子,跟生产队换点儿菜……”
“我老头叫吴延亮,原先在煤窑上班,是按天算的,今天上班有钱,明天不上就没钱。他下班回来,又累又没吃的,加上咳嗽、身上长疮,又没药、没医疗,哪个能不死?父亲死的第二年,我就没再读书了。”
“我哥哥叫吴智可,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他白天做一天,晚上还要打夜工。见到劳力好的,就被用得很苦,劳力不好的,也没办法。我哥哥就属于劳力好的,一晚上要挑一个灶——每家的灶都要拆了,挑到堆肥料的那个凼子里,把泥巴和稀了用来做肥料(炉灶本身是烧过的泥巴,肥一些),种洋芋、种苞谷、红苕。我哥哥越做越饿,饿死了。”老队长吴智深如是说。
“后来我在共和六队当队长,队里一百多人干得有劲……在故陵开先进表彰大会,别人叫我‘棒老二’——我不怕事,喜欢打点儿架,不管你再歪的人,要得要不得,我是直来直去的。划土地,我先把政策跟你讲清楚,你们分完了,最后才是我的。但是不管你搞得再好,总有人反对。”老队长吴智深说。他说话掷地有声,四面都传来回音。
我们一直说到天黑。最后,我又问起李良之。吴智深告诉我,他是老干部,他的姐哥也是地下党……天黑了,还有许多话来不及说。老人们问我在哪里住宿,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找到地方。他们说不要紧,街上有旅社。
晚上,山坡上的人们一一散去了。我跟着吴队长来到街上,在他女儿开的餐馆吃了一碗面。夜晚在街上找到一家私人旅社,一幢新楼,好多空房间。儿女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两口在屋里。
夜深了,我躺在空空的大房间里,月亮挂在窗前。我在心里默念着:普安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