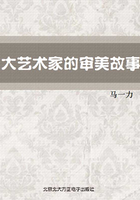“谁?什么输了?”
江采厉声质问。
不为其他,只为师文衣此时给她的感觉很不好。
说不上来的滋味,像喉咙里卡了刺,鼻子堵了一只,无伤大雅,却又让人浑身不舒服的感受。
师文衣胜利一般的笑容看的江采又是一阵刺眼,她皱起眉头,眼神里不含一丝温度。
“你今天最好把话说清楚。”
师文衣对她的警告充耳不闻,她脸上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癫狂,低声道:“师江采,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不喜欢你,不,我讨厌你,凭什么同样是师家的女儿,偏偏是你被当成天选之女送入宫中,成为人上人,凭什么同样是父亲的女儿,你就是师家女儿,而我,充其量只是个顶着师家女儿头衔,却毫无存在感的二小姐,甚至,我为了成为真正的师家人,学习了剑法,知道是什么剑法吗?死士!我跟着父亲,无数次死里逃生,这些你都不知道吧,可是为什么,让他骄傲的,还是百无一用的你!”
师文衣一口气将心中的不满与不甘倒了出来,而江采,也是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看似柔弱的妹妹,竟然暗中付出了这么也多努力。
她说的对,百无一用的师江采,怎么就能轻而易举的成为师放的骄傲了呢?
这个问题江采也曾想过无数次,后来,在一次无意中得知的一件事中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狠。
师江采这个人,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是丝毫不留情。
成为天选之女的路并不好走,她自幼入宫,一个孩童,就算身边高手如云又如何,如果有人想害她,在深宫里,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可是没有人想过这一点,师文衣以幼年之龄,是如何安然无恙生存到今天的。
如果江采不是听胧月提起往事,恐怕她也无法想象得出,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女孩,竟然眼睛不眨一下的,将一个冒失犯错的宫人处死。
自那之后,师江采对自己更加狠戾,她将宫中的规矩参了个透彻,将礼数做到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生活的更是滴水不漏,让人想钻空子都难。
这也是为何当年容湛与师江采两看相厌,却又奈何不了她半分的原因。
师江采太过缜密,百密而无一疏,这才让她的地位日益稳固。
另外,师江采的脑子也绝对够用。
宫中不缺聪明人,但缺的是聪明的不显山露水的人,而恰恰师江采就是那一类。
师放之所以将她当做骄傲,那是因为,比起师文衣,师江采更有野心,有欲 望。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和师放很相像,两人同样隶属于狠辣之人,故而,许多时候,不用言语交流,就能明白彼此要做什么。
但是在江采看来,师放不单单是将师江采当成女儿,他更多时候,是将她当成了合作伙伴。
这从父女的角度出发,其实还不如师文衣。
起码,他没有将这个女儿早早的扔进深宫那吃人的地方。
不过,师文衣不知道师放的良苦用心,到头来还在怪怨,不免让江采感到怅然。
筹谋一生,却连最直接的情感表达都没能传递出去,不可谓是不失败的。
“如果你父亲在地下听到这一番话,定然是要失望的。”
江采感慨一般的说了一句,师文衣却厉色道:“你懂什么!”
“他是不会在意我的,不管我心里如何想他,他都不会在乎,活着的时候如此,死了更是如此,师江采,我只恨自己当初手贱,如果任由你在湖里淹死多好。”
她说的那一次,正是五年前她穿越而来的时候。
其实她很想告诉她,她还是没能救出师江采,真正的师江采已经在湖里淹死了,后来的,都是她江采而已。
最终,她还是什么都没说,话已至此,师文衣依然执迷,她也无能为力。
“先跟你说清楚了,既然你从宫里出来了,那就与我再没有关系,我这次来山庄只是来避暑的,再者,容湛已经答应做你和秦桎的证婚人,你也别想太多,安心过以后的日子吧。”
江采安慰一番,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实在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带上小金鱼便要走。
师文衣又一次拦下她的去路,江采太阳穴突突直跳,竭力扼制着自己的怒火。
“还有什么事?”
“你和容……皇上在一起?”
大概还是习惯,师文衣说出‘容湛’两个字的时候,又改成‘皇上’。
江采不想去揣测她此时的想法,敷衍的应了一声。
“你当真是心大,他从前如此对你,你不怨恨他?”师文衣看怪物一般的眼神,但细看之下,眼底浅浅的藏着一丝探究。
江采没在意她的眼神,只是被缠的烦了,脱口而出:“是,我怨恨他,不管如何,我和他之间始终有着人命,说起来,师放也是死于他手,你就不怨恨?”
“父亲明明是……”
师文衣下意识接口,话说到一半,忽的意识到什么般,陡然停住。
她抿唇看着江采,似乎在观测她的表情真假。
片刻后,苍白的面上突然渐渐浮上笑意,笑的江采毛骨悚然。
“没错,父亲确实是容湛杀的,我恨他,所以,你可要记准了这一点。”
师文衣声音轻轻,带着上扬的尾音,不协调的感觉扑面而来。
江采实在呆不下去,不管她此时疯疯癫癫的模样,拉着小金鱼往回走。
走了一段距离,她神差鬼使的回头看了一眼。
远远的,师文衣就这么站在风口处,夜色朦胧下,不知为何,她的一双眼睛雪亮,即便离得这么远,也能清晰的看到那眼底的诡谲。
没来由的,江采心口处一阵发闷。
如她所说,如果早知道师文衣在这里,她是绝对不会来这儿的。
如今可好,白白闹了一身的不自在回去。
江采与小金鱼回到亭子里时,恰好见到园中行迹匆匆的下人们,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在找人。
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们要找的人就是师文衣,江采指了个方向,晚饭前,传来消息,师姑娘被找回来了。
彼时,江采与小金鱼正在屋里做数独游戏,容湛带来这个消息,她动作一顿。
细微的变化还是没能逃过容湛的眼睛,他问:“你见过她了?”
江采没什么好隐瞒的,点点头随口应了一声:“嗯。”
脑海中不由得想起师文衣的眼神,冷不丁,心中又闷的喘不过气来。
“她同你说什么了?”
容湛在两人身后站定,看着桌上正在犯难的小金鱼,随手画了个答案,小金鱼大喜,欢快的将空白处添上数字。
江采不动声色的将两人这明目张胆的作弊看了去,她抿了抿唇,不发一语。
“自后山回来,你的神色便一直不对劲,可是她对你说了什么?”
容湛问的坦然,江采依旧不言。
倒是一旁的小金鱼放下笔,回身替她回答:“她说了很多话,不过在我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重要,她说是父皇杀了外公,是这样吗?”
小孩子童言无忌,小金鱼年幼,不知道什么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更不知道,他的父亲杀了他母亲的父亲,这样的仇恨,又是罪加一等的。
小金鱼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将话摆在了台面上。
于是,一瞬间,屋内的空气变得尴尬无比。
准确的说,尴尬的只有江采一人,她面色不自在,垂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握起,随后再也绷不住一般,蹭的一下站起来:“我出去透透气。”
容湛也不拦着她,任由着她逃般的冲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父子俩,四目相对。
小金鱼眨巴着眼睛,不明所以:“娘亲怎么了?”
“她说她出去透气。”容湛官方说法。
小金鱼哦了一声,很爽快的跳过这个话题,他问:“所以父皇真的杀了外公?”
容湛眸光动了动,他抬手在他的脑门上不轻不重弹了下,摆出个嘘的姿势:“要保密,不能告诉你娘亲。”
小金鱼连连点头。
容湛满意的笑了笑,好看的唇瓣扇阖着:“外公不是父皇杀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娘亲?”小金鱼惊呼一声。
容湛笑意不减,却带了些不易察觉的苦涩:“她不信。”
小金鱼沉默了会儿,还想出谋划策,容湛先一步出声:“你先替父皇保密,时机成熟时,我自会告诉你娘亲。”
“嗯。”
似乎除了答应,也没其他法子了。
小金鱼看不懂两个大人之间的感情纠纷,以他的角度来看,有什么事情直接说明白不就好了?
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很多时候,真相早已经不那么重要。
如果能让江采心中好受的话,容湛宁愿一直背着这个黑锅。
只因为,他想象不到,有朝一日,江采得知真相,得知杀害师放的正是她从未怀疑过,并全身心信任的师洵的话,她会如何。
师洵这一招太狠,太绝。
他料准了他容湛不会为了和好铤而走险,更料准了,他绝不会以江采的安全做赌注。
所以这场赌局,他容湛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