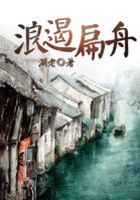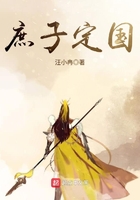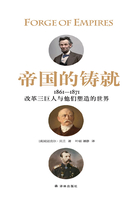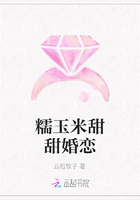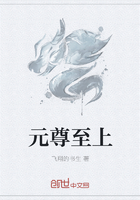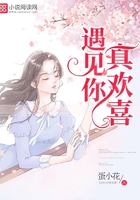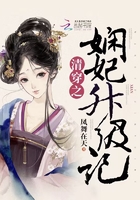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据考古发现,至少在180万年以前的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此时期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过后的一个时期。
1.人类的起源地应在非洲和亚洲
北京人,过去只知道是中国最早的人类,距今已经约50万年了。后来,又发现了蓝田人,距今应该已有约100万年了。北京人和蓝田人,都应属于更新世中期出现的人类。贾兰坡于1957年提出了应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去追寻最早的人类足迹。其结果,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果然陆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它们的年代距今已达170万—180万年了。经过对西侯度石器的观察,虽然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都比较古拙而原始,但是从其已注意了选料,并运用了不同的打击方法,以及制造出了不同类型的石器来看,应该是已经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光。因此,有的学者就提出了还应到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求,那里也应该发现我国最早的人类遗骸。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推测,应该抱有期望。
当今的非洲,已经发现了更多和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据今已达200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发现的石器历史则长达260万年以上。由此,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人类考古资料来看,人们则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是在非洲,或是亚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
2.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
今天的人类是由类人猿发展和进化而来的,但究竟是由哪种类人猿演化而来?又因什么机制使得类人猿向人类转化?又是在什么地方最具备从猿转化为人的客观条件,才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呢?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人类学课题,然而至今却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在所有古代类人猿中,旁遮普腊玛古猿是较接近于人类的。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大约生活在1500万—1000万年前的古代类人猿,应是最早人类的祖先。这种古代类人猿发现于印度旁遮普地区,而在我国云南的开远小龙潭及禄丰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不过由于最近在禄丰石灰坝大量古猿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已将其重新定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其所在地层属最晚中新世,距今约有700万—800万年了。
数量很多并形态完整的禄丰古猿化石,在同类古猿化石资料中是极少见的。禄丰古猿化石经整理和研究,已确定了的共有颅骨5个,下颌骨10个,颅骨和颌骨的碎片47块,上下齿列29组和牙齿650颗,还有肩胛骨和锁骨各1根,指骨2根;禄丰古猿的体征不但有雌雄之区别,也存在着许多个体的差异,呈现着相当复杂的一些情况。但从总体来说,有许多性状接近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状接近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亚洲现代大猿,从而这一切也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谱系,提供了新的十分重要的依据。
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绝不是由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该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然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过去的水平,但仍然不能完全搞得一清二楚。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探索人类的起源地,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应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应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陆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给这种提法以有力的支持。
西侯度文化,以西侯度地名而来,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黄河从它的西边和南边流过。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广泛分布的河湖相沙砾薄层和交错砂层,其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共计32件。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其打制的技术比较原始,已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都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的几种打制的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页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多为石片加工而成,并以单面加工为主。到目前为止,是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此外,还有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这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乃至砸开脑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随地抛弃,而长角则被加工为某种器具。当时共存的动物化石主要有鸵鸟、大河狸、刺猬、兔、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平额象、鬣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种类颇多,十分奇特。其中,绝属的占47%,绝种的占100%,并且有古老的种,如步氏羚羊等,因此被定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组。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组的年代,距今约为180万年。
西侯度只发现了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那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则有两者兼有的一处元谋人及其文化的遗址。这里说的上那蚌,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个棕褐色黏土的小山丘,四周冲沟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龙川江(金沙江的支流)。在那里发现过两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出土层位应在元谋阶第四段下部的第25层,属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70万年。在这一层的下部,更早的地层中也发现了文化遗物。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应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很深,形体相当粗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并呈现浅灰白色。这很可能是青年男性的个体。这两颗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而又具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因此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nesis)。
距离现在大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是我们所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原始人类。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两颗猿人的门齿化石。后来又发掘出旧石器、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和用火的灰烬。这里的猿人,就被称为元谋猿人。
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发现的石制品,主要是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主要用锤击制成,加工方法粗糙。在发现的化石中也有许多哺乳动物的肢骨碎片,有的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其他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看来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样都已懂得用火了。懂得用火,这对于人类来讲是一大极其重要的进步。另外,还发现云南马、爪蹄兽、野猪、水牛、纤细原始鹿、剑齿象、豪猪、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它们多以食草动物为主。经过对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属占33%,桤木属占13%,草本植物则占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由此看来,只有当时的气候温和适宜,才能见到森林、草原等诸多的美好景象。
在河北阳原小长梁地区发现了石器,这是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的遗留。石器的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它是用锤击或砸击制成的,不少的石片未经加工,便直接使用了,依旧看见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用来刮削、尖锋、砍砸等,但形体都比较小,个别的制造较有进步。小长梁发现的石器,所在地层较厚,跨越时间较长,其中还可能有年代较晚的石器。与小长梁石器伴生的有鬣狗、三门马、三趾马、腔齿犀、古菱齿象、羚羊、牛类和鹿类等动物,但多是已经绝灭了的动物,年代应是更新世早期。
继小长梁石器发现后,1981年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坨的西北侧又发现了一处面积极大、遗物十分丰富的石器地点。石器发现于距地表约40米深处的灰绿色砂质黏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靠下部的黏土层中,下与侏罗纪砾石不整合地接触。据测定,距今约100万年,可能属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期间。在那里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废弃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类型也很复杂,还有不少尖状器,砍砸器甚少。总体特征是体积较小,加工较精细,已经可以分出明确的类型,这很显然不是最早的石器。这石器与同时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显可见不同于西侯度和元谋上那蚌的石器,而与附近的小长梁石器十分相近。鉴于东谷坨石器最为丰富,故有人称之为东谷坨文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像,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3.中华民族的起源以及国内外之纷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曾有过多种说法,至今未能定论。不过,目前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已公认: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自20世纪60年代在云南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1975年又在云南禄丰陆续发现,不仅化石的数量多,并且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发现了腊玛古猿(雌性禄丰古猿)头骨的地点。
1987年,又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蝴蝶腊玛古猿。这些重要的发现,在地理上都与元谋直立人发现的地点相距甚近。近些年来,在湖北建始、巴东等处也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1990年5—6月,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更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经初步研究断定与1989年5月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类型,定名为郧县人。在郧西也发现过直立人化石;距郧县、郧西县均不甚远的陕西蓝田县也发现了蓝田直立人。这些从猿到人相衔接各个环节的发现,加上其他多处直立人的发现,证实了我国应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华民族决非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区域起源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综括先秦史料,叙述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古代的正统观,影响非常深远,是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说。
自17世纪起,欧洲开始有人认为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埃及。这是欧洲人倡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的假说。到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学者拉克伯里倡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巴比伦的巴克族。到20世纪20—3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主要依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的某些图案与西方某些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风格有相似之处,断言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首先开化于中国的新疆,然后才东移发达于中原地区。此为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新西来说”。由于安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做过开拓性贡献,其假说曾流行一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安特生后来对其“西来说”已有所纠正。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起源于中亚、南亚等说,均可归入“西来说”;起源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处,略可称之为“南来说”;起源于西伯利亚等处,可称之为“北来说”。凡此种种,以“西来说”最为流行,均可概括称之为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外来说”。
上述各种“外来说”的产生,一方面受着当时流行的学说与方法论的影响,有些也受着西欧中心史观的支配,同时也局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与资料的缺乏。这些假说提出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当时即已受到了驳难,终因考古资料的贫乏而未能消除其影响。
在当代,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说众多,其中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其《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玛雅文化)和秘鲁。值得注意的是,丹氏所举的六种文明,中华文明既不像两河流域与埃及那样地处五海三洲相接、四通八达之区,因而希腊、罗马文明受其启发而臻于发达,与印度文明也有较密切的联系;也不像美洲印第安文明那样被两大洋隔绝,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不为世人所知。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上述六种古老的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从起源,直到发展到今天,一脉相传,源源不断,从来就未被割断过。中华民族这种独树一帜的特点,在起源时代就已经萌芽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这一阐述很好地表述了中国60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是出现小石器最早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