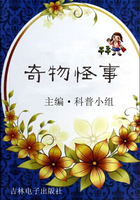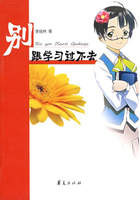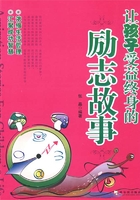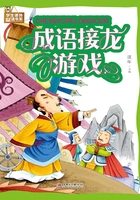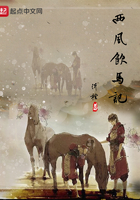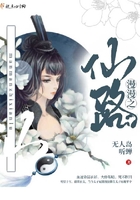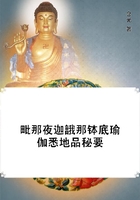我们中的很多人总是被逼着不断前进,而哲学会让我们停下脚步。
比如,人们在种菜、写书、驾驶推土机、出售商品的时候,会考虑如何避开拥堵,按约定时间到达客户的公司,但是却不会问“人为什么要工作”;人们会思考怎样才能提高销售额,但是却不会去思索“工作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赶不上约定的时间,原本好卖的东西也会变得卖不出去。越是工作顺心的人就越是不会去思考这些“多余的事情”吧。
但是,哲学问题会让提问者暂停脚步。一个正在思考“工作是什么”的人会不想去做任何其他事情。在那些被“不断前进”的压力束缚着的人看来,这些人就像是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蚂蚁搬家的孩子吧。哲学问题只属于那些不受“不断前进”咒语管制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孩子才会思考哲学问题。
但是同时,孩子又不会思考哲学问题。只是一味地想“为什么要工作”并不能算是思考哲学问题,仅仅把“为什么要工作”挂在嘴边的行为也根本算不上提出哲学问题,那很可能只是类似叹息之类的东西。
哲学问题,不仅是没有明确答案的,而且连同问题本身的含义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发问者必须在探寻问题的答案的同时,思考自己所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提出哲学问题,需要独特的技术和能力,这对于孩子来说还太难。
此外,哲学还必须是“轻松”的。没有工作过的人对劳动没有确切的概念,但是过于埋头苦干的人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劳动。从未工作和埋头工作,如果身处这两种状态中的任意一种而不能走出来的话,那么就无法将“工作”这件事作为一个思考对象客观对待。哲学不仅要求从实践参加者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行为,也要求从未参加实践者的视角来进行思考;不能局限于自己目前的视角,而是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而孩子还不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孩子们还不会思考哲学问题。
只有孩子才能思考哲学问题,但是孩子又不会思考哲学问题。在这样的矛盾中,哲学家出现了。他们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孩子。
他们是哲学家。
这本书采取的是孩子向哲学家发问的形式。老实说,提出这些问题的其实都是我——如果允许我带着一点点害羞和一点点自负来说的话,是作为哲学家的我,而且我并不是真的变成小孩子,来想一些孩子才会提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本书的副书名叫作“小孩子的哲学大问题”呢?
事实上,我自己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研究者,在哲学研究领域深受各种规则的束缚,被“不断前进”的压力追赶着,一定要出多少多少成果(坦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有丢面子、不知所措的感觉)。正因如此,我才想要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站在小孩子的角度,以一种毫无防备的野性的姿态来提出哲学问题。
老实说,在做本书的策划时,我对很多哲学家都抱有偏见。他们遵从研究者的规则,作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已经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我提出的这些过分朴素却又直指根本的问题会不会感到无从下手呢?事实上,要写出有影响力的论文,最好不要直接回答这样朴素的——孩子气的——问题。适合写论文的是那些更容易得出结论的问题,是那些被专业细分的、被明确公式化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些哲学家多少抱着一点想要故意为难为难他们的心理,想借孩子之口来让这些作为大人的哲学家头疼一下。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的这种打算意外地落空了。
确实,突然接到这样不带一丝掩饰的直指根本的问题,哲学家是会感到头疼。但是,没有一个哲学家因此逃避或者糊弄,甚至还有人非常开心能够回答这样近乎野蛮的提问。我不由得心花怒放。同时,哲学家的回答虽然采取的是面向孩子的口吻,但是回答的水平并没有丝毫下降。当然,因为篇幅的限制,所以哲学家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是也因此,他们都将核心提取出来展现给了大家。所以虽然读来很轻松,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值得反复阅读的。有的回答有极其新颖的切入点,而有的回答会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我所提的问题。根据你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人生以及你目前所处的状态,这些回答将带给你不同的意义。
希望孩子们能够阅读这本书。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这本书,希望读者有空的时候就能拿起来读一读,即使是成人之后。对于已经不再是孩子的诸位也是如此。
远离“不断前进”这一魔咒带来的压力,进入哲学开辟的世界,大家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啊,请停下脚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