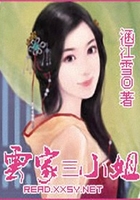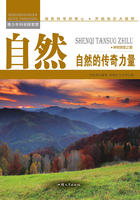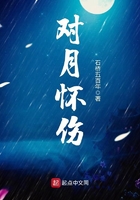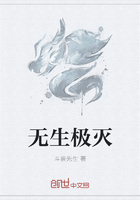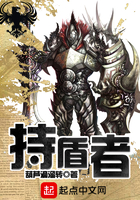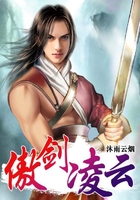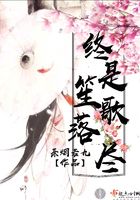——《白色花》出版轶事
若琴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书:黑色的封面背景上,一朵素色小花傲然挺立;书名《白色花》下方,作者署名的位置,仅有“二十人集”几字,这是一部诗歌合集。
该书面世后,年轻的读者突然发现:原来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批诗人,写过这样一些诗篇。文学界传递着一个似旧还新的专有名词——“七月诗派”;一段时间里,《白色花》似乎成了“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事实上,《白色花》并非一般的文学书籍,也不是单纯的流派之作,它原本是部平反诗集,一部名副其实的平反诗集。平反所指,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轰动一时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称《白色花》为平反诗集,自有缘由,不妨先了解一下选题目的。
该书扉页标有两位编者名,但他们却不是《白色花》的选题者,选题者另有其人;主张为“胡风集团”案中的诗人出一本合集的提议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组组长刘岚山先生。刘岚山1919年生人,人称“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于四十年代开始从事编辑工作,1952年调入人文社,1960年担任诗歌散文组组长。他提出该选题时,平反“胡风集团”案的中发(1980)76号文件尚未下达,选题具体时间应早于1980年初夏。
日后,刘岚山在自己的《业务自传》中提到《白色花》:“这本书的出版,在落实党的政策、体现双百方针的贯彻等方面,都不无某些意义。”《白色花》出版前,刘岚山发表述评说:“从三十年代末起,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熊熊烈火中,冶炼出一大批热爱祖国、向往革命和投入战斗的青年诗人,铸造出许许多多经历过时间风雨的冲刷而仍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诗篇。现在还活跃在诗坛上的许多老诗人和陆续出版的他们的选集,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另有一部分诗人,则由于历史的错误,就像行进在沙漠中的骆驼队突然遭遇到漫天风暴的袭击,他们被深深埋进了沙丘;经过二十五年漫长的岁月,他们有的已经‘凋谢’,化为‘猿鹤虫沙’,多数还活着,但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好像老树逢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耀下,正舒展青枝绿叶,张臂欢迎得来不易的春天。”
身为一名老编辑,刘岚山颇具前瞻眼光。之前在艾青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时,他即提议组编《艾青诗选》。在“胡风集团”案尚未平反前,他再次想到,要为该案受伤诗人出本合集,与久违的读者见见面。人文社领导眼亮心明,顺应形势,无障碍地通过了该选题。
选题确定即该组稿,但“胡风集团”案长达25年,情况错综复杂,如何联系相关作者呢?正好,人文社内就有两名“胡风分子”:1953年来社的牛汉,在胡案中被“隔离”两年,后被定为“一般胡风分子”,留在原单位,但被开除党籍;1962年来社的绿原,原是中宣部的干部,在胡案中被“隔离”7年,进过秦城监狱,被定性为“胡风骨干分子”。曾有人撰文说:人文社有三名“胡风分子”,还有一名是舒芜。这种说法纯属政治误解,不知晓“胡风分子”是一顶政治帽子,它的全称是“胡风反革命分子”,舒芜与这顶帽子从来一毛关系都没有。牛汉涉案浅,1979年他的“胡风问题”提前获得解决,恢复了党籍。他与刘岚山同为现当代文学的编辑,先得知合集选题信息。绿原在选题确定时,尚未政治平反,但出版社领导于1979年曾推荐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对他迈进历史新时期不乏鼓舞作用。既是“分子”,又任本社编辑的牛汉、绿原,为这本诗合集出力,自然责无旁贷。刘岚山因而与二人密切合作,他代表诗歌组说明:诗合集是“为了平反,主要不是为了彰显流派”。当年案中人往来信件也有类似记录,绿原曾给鲁藜写信说:“那本诗集,是由诗歌组主动约编的。初步决定,不标什么派别,只是把这一批为诗受苦的人们的早年作品搜集起来,给今天的读者看看。”
牛、绿二人商研后,达成共识:合集作者以“胡风集团”案受牵累诗人为主,收集作品以新诗为主,其中又以曾经发表过的在读者中有影响的诗作为主。随后他们联系了北京的同案人,大家又分别与外地的朋友设法沟通,共同打听其他同案人的下落,组稿工作就此铺展开。牛汉已具自由人的身份且有《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稿的方便,诗稿就由他汇总。
25年来“胡风集团”案涉案人之间大多失去联系,有的音讯全无,生死不知;有的虽近年“出土”,但手头空空如也;资料散佚,搜求困难,连图书馆当年都和他们的著作划清了界限,旧作多被淘汰干净。开始组稿进度不太快,曾卓6月知晓,9月才寄出自己的诗稿;鲁藜则艰辛地从图书馆内部搜寻到自己的旧作。
9月底平反“胡风集团”案的中发(1980)76号文件传达后,进度明显加快了。
确知已经离世的同案朋友(如阿垅、方然、芦甸,传说还有化铁),他们不可能再自己提供诗作了,幸存的朋友则设法找到旧日期刊,抄出他们的一首首遗作。彭燕郊11月4日写信给牛汉说:“我的诗,‘文革’中全烧了,我在省图书馆找到《战斗的江南季节》,抄下三首,你看可以用不?”曾卓12月6日写信给绿原说:“信收到,《诗选》不知定稿否?郑思的诗集我已清了出来,既已有十八人,他应该也可以算一个的,《秩序》可以入选。如需要,我可马上寄来。”《秩序》是郑思(1955年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在《希望》上发表的唯一诗作,后收入合集。这期间,有同案人寄来旧体诗,也有入选作者将新旧诗作同时寄来,结果旧体诗都未选用。
诗合集计划第二年5月出版,最后截稿时有20名作者。若问“为什么是这20位”,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在组稿的时间窗内,他们的诗作因缘际会地被选留。如延长组稿时间,肯定还会收入更多的人与诗。绿原日后就遗憾地提到伍禾、罗飞、林希等写诗的同案友人未能入编,其实还有更多人,只是时间老人无法再等了。
这20名作者作为一批人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与胡风先生有过或多或少的关系。其中,有15名为胡风刊物作者:三位为单纯的《七月》作者(彭燕郊、钟瑄、杜谷),七位为单纯的《希望》作者(郑思、绿原、胡征、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五位是《七月》和《希望》两刊的作者(阿垅、鲁藜、孙钿、方然、冀汸)。另外5名:牛汉为《七月诗丛》第2辑作者,曾卓为《诗垦地》作者,芦甸为《平原》诗刊作者,徐放为《现实诗丛》作者,罗洛为《呼吸》《泥土》作者。这里提及的“青年同人刊物”,据说与《七月》《希望》的创作倾向大体相同,几位作者也都与胡风本人相识。
但是,与胡风及其刊物有关的诗人远不止这20位,而这20位同时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所以他们主要不是作为流派的代表入集的。曾卓寄诗稿时就说:“不过,我算‘七月’,总像有点勉强。”
再观察案情层面:20名作者全都在“胡风集团”案中受到牵连伤害,四分之三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所谓“骨干分子”约占一半;1958年被公安部门留下来的“问题严重者”,在20人中近三分之一,他们是阿垅、方然、徐放、绿原、冀汸、芦甸。6人中3人在平反前就已身故:方然于1966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阿垅1967年瘐死狱中,芦甸1973年在劳改中死于脑溢血。可见。被邀入集者,更应被视为“平反诗人”,而不是单纯的“流派诗人”。
似乎还有一个疑问:既然是平反,为什么没有收入胡风的诗作?
由于选题者与编者都已谢世,无法解答,笔者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胡风的身份与20名作者不同,他是诗人不假,但他更是一位理论家,让他挤在这些较他年轻甚至可称为后辈的诗人中间露面,混淆了他的学术身份;二是社会的思维是层层推进的,如同剥笋:先简单后复杂,先边缘后中心。数年后,胡风的《诗全编》独立问世。
诗集内容基本确定,就需作序了。序言是桥梁,是读者与作者间的桥梁,对于在文学史上几近湮灭的一群诗人,重新面世的序言十分重要。
写序的最佳人选自然是胡风老先生,但是高龄的他离开高墙未久,尚未对接红尘,就又被疾病缠身。其次适宜人选是阿垅: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令人难过的是,他离开人世已13个年头。组稿当初,商讨选定的序作者是曾卓。他那首《悬崖边的树》感动了无数读者,而且除了写诗,他还写散文,其抒情笔调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只是,多年的政治灾难损伤了他的肺脏,此时他旧病复发,无法紧张地写作。
发稿在即,时间不等人,于是出版者的眼光转向了绿原:他是本社编辑,理应为本社出书救急;刚获政治平反,为同案人代言,也是情理中事。而绿原内心明白:在“七月”队伍里,他是“后来的”,且并非理论研究者。虽然过去25年他一直也在思索,而要代表20名作者与新时代对话,手中之笔也着实不轻。不过正如台湾农村俗语所言:“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番薯汤”,此刻自己必须“直下承担”了。
写出序初稿,绿原拿给牛汉、徐放、鲁煤和来京出差的罗洛细读,请各位朋友“字斟句酌,加以修改”。四位朋友对局部细节提出了补充意见,对全文却未做原则性的改动。之后,上海的同案朋友耿庸来京开会,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理论工作者,也是一名所谓的“骨干分子”,绿原又征求了他对序稿的意见。耿庸“边读边有点感想”,却认为“不必有所改动”。
1980年12月27日,绿原在给上海的何满子、耿庸的信中说:“《白色花》(诗集)已发稿,争取明年五月出书。序言将另发《当代》,领导的批示。责编还将写文介绍。牛兄说,想不到如此顺利。那篇序言虽由我执笔,但观点是大家的。如能要到清样,当寄一篇给你们。”
“耿兄动身次日,徐放、鲁煤和我一同到医院去了。谈了两小时,病人(指胡风先生)哭了三次。就便谈到诗集(指《白色花》)事,问他如何看待‘流派’创作的特点,他断断续续地说:‘时代的真实,加上诗人自己对于时代真实的立场和态度的真实,才能产生艺术的真实。’足见思维能力未衰。已将此句纳入诗集序言中。”由此可知,经过绿原的消化整理,《白色花》序吸纳了胡风本人的观点。
合集作者的三分之二生于20世纪20年代,绿原也在其中,所以他写序的思路带有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序言首先介绍合集作者多是在四十年代初20岁上下开始写作的,是同抗战文艺一同成长的。回顾他们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民族危机笼罩,政治形势严酷,在中国的苦难土地上和人民炽烈的斗争中,诗作者们在政治上有共同的信仰和向往,坚信并热望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因而,现实生活是他们创作的唯一源泉。
尽管风格各异,他们在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却又有基本的一致性,即努力把诗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中国自由诗传统的肯定和继承。
对于人与诗的关系,他们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诗的生命不是格律、辞藻、行数之类所可赋予的,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其次,诗的形式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而是和内容不可分割地成为整个诗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才是诗的极致。而最重要的,由于历史环境、时代性格和个人经历对于诗人的主观性的教育作用,他们进而要求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通过严格的自我审查,争取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相通,反射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光泽。
序言认为,生活在四十年代的时空,对于合集作者这一批文学青年,诗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他们坚定地相信,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依靠时代的真实,加上诗人自己对于时代真实的立场和态度的真实,才能产生艺术的真实。这种创作态度是他们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序言还认为,在新文学史中,四十年代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块巨大的里程碑。不但诗人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新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高峰,其深度与广度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无法企及的。
诗合集记录了作者们当年所走过的一段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为自由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过力所能及的促进作用。但到了五十年代,这批诗人一齐被迫搁笔,有的接着相继谢世。序言最后说:作者们愿意借用“白色花”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从序言结尾可见,《白色花》作为平反诗集,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白色花》序,绿原日后曾说:“里面有些看法未必完全属于我,又不能说完全不属于我。”因为他毕竟不是代表个人执笔,而“我们”这个称谓却是有时空性的,不同的阅读者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内涵。
1981年8月《白色花》终于“开放”。
之前绿原将序的校样转给上海的朋友,何满子拿给王元化看,王看后回复说:“满兄:绿序奉还。稿上我作了两处记号略有点小意见,指出当时不可能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故题材狹,知识分子味浓,这是从文艺工农兵方向去评骘。我觉得今天还是强调马恩文艺观重要。”何满子同意王元化的看法,同时认为序文应增加对于诗派所受限制的外在条件(历史条件等)的阐述,例如拉普思想的干扰,当时浮嚣的文风等等,认为这对现实和未来都有教育作用。耿庸将何、王的意见寄给绿原时,仍认为序文“不必有所改动”:因为鲁迅先生早有联系人民大众的教导,文字上别人如何理解则可不必计较,一些问题正面阐述就可以了。
胡风先生可能认为《白色花》序文是代表“七月派”发言的,他在给诗评家周良沛的信中说:“艾青,是对读者影响较大的一位。但对七月派诗人们本身,有的有影响,大多数没有影响。《白色花》的断语是欠慎的。”虽然序文实际仅代表诗集的20名作者(更是代表其中的青年作者),而平反诗人与“七月诗人”的内涵虽有相交却不完全相同,但绿原认为,胡风先生的意见对于新文学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何剑熏先生也曾是胡风刊物的作者,说话一贯俏皮,他写信对绿原说:“《白色花》序拜读,写得好,是一篇《翻案宣言》,你把胡的那个‘主观战斗精神’,解释得比他自己还清楚。”
但绿原在主观上恐怕没有想去阐述胡风先生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自己只是写诗之人,阐述理论更是学者的任务。自己在非常时期代言写序,仅是尽一份历史责任。介绍平反诗人,不能不涉及文艺观,不能不涉及流派,话到嘴边,不得不说,不足之处自然难免,因而对于各方意见,他都乐于吸纳,以做进一步的思考。
他认为,所谓“七月诗派”,就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这段艰苦岁月以内,环绕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而平反诗集《白色花》反映的只是该流派的局部投影,尚不能从艺术倾向上完全代表这个流派。
不过“胡风集团”案的平反和《白色花》的及时出版,客观上促成“七月诗派”在历史中复活重生,同时有力地证明了四十年代的新诗绝非空白,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承不承认,这一历经了两个战争时期并与斗争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诗派,都真实热切地存在过。
绿原还相信,这一群诗人尽管被时光的尘土湮没了,但绝没有在文学史这片“战场”上就此“阵亡”,他们当年永不满足、永不停滞、永不迷狂地为诗献身的精神将会长存,如同无数躁动不安的溪流一样,在从来并不平坦的大地上,绕过大大小小宁静而自得的池塘和沼泽,勇敢而自信地向着大海的方向奔去……
近20年后,《白色花》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原载《随笔》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