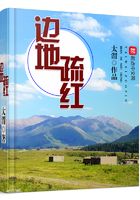陈家琪
阿伦特诞辰一百周年了。她生于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因心肌梗死病逝,享年69岁。
当我想到应该写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纪念之意时,曾列出了四个不同的题目,其实也就是想通过阿伦特的著作来理解她的基本思想,这就是: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极权主义的起源;康德政治哲学的讲座,以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与现代性有关的话题,阿伦特讲的是“人权现象学”,其核心意思就是作为一种标志,人们从对自然法(不能违反自然秩序)的敬畏转向了对个体的人的权利的维护,而人权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康德则是第一个发展了对人类尊严的非神学意义上的辩护(参见塞瑞娜·潘琳的《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于是这就又与她对康德哲学(特别是判断力批判)的重新解读发生了关系。关于现代性的特定条件,潘琳根据阿伦特的思想概括为“超验的不可能、权威的丧失和传统的断裂”。所以,阿伦特认为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出一种能够理解我们的经验共同性的方式,也就是说,当超验的存在已经无法再给我们提供共同经验的依据,当一向被认为是权威的言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已经受到了各种质疑,当传统的习俗也不再能为我们人类生活的共同之处提供证明时,尽管我们仍然不得不与他人生活在一起,但人权,这种单单属于个人的权利如何得到维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结构又当如何得以证明和论证?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影响很大的一部巨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必说更多的话了,但有一点必须强调,这就是个人的孤独感与缺乏正常的社会联系(公共生活),会变成一种哲学(把历史解释为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和种族之间的自然混战),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失落、厌恶、排外和盲目仇恨,于是有了暴民们想走向历史、改变历史的政治冲动(参见林骧华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所写的“译者序”,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著作有《犹太复国主义的困境:随笔和评论》《以色列和反犹主义:论文集》。她的《论革命》《过去与未来之间》《权力和暴力》《论时代:政治随笔》都与上述四个话题有关;而这四个话题,又可以集中概括为人的处境、人的情感、人的精神生活(思想,意志)与人的判断。当然,这里所说的这些“人的”,都指的是人与人的,或人在共同生活中的。
但如果仅仅这样提出问题,还远远无法满足我内心深处对阿伦特的崇敬,以及那种有着深深切肤之感的对友爱与交往的渴望。
我曾经读过的一本《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是2001年4月29日崔卫平寄给我的,我读了两遍,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在此之前,我在海南大学时的研究生王凌云翻译的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当时就给了我一本,而这本集子中的第一篇《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又涉及我来同济大学后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乐燕蓉所写作的硕士论文,当时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解读莱辛的剧本《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所有这些往事,在瞬间忽然汇集成一个词语,这就是“爱”,或者可以理解为阿伦特在特定场合下所强调的“友爱”。我的博士生陈郑双所写的博士论文就是《政治哲学中的友爱问题》,而随便抬眼一看,又是托克维尔的一本讨论“政治与友爱”的书信集。
阿伦特无疑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也没有问题,他讨论的就是政治问题。为什么要讲政治中的友爱?柏拉图在《吕西斯篇》中到底是如何讨论政治与友爱的?《智者纳旦》又与友爱有何关系?
所有这一切又使我不得不重新打开陈郑双的博士论文和乐燕蓉的硕士论文。
事情过去了十来年,自己的学生当时也许无意中所写下的一句话,竟如此投合我此刻的心情。这也正迎合了阿伦特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念:思维不是一种主动状态,而是一种被动状态,它有赖于世界的现象界向你敞开,而且被你所感知。存在和显现同时发生;而显现的多样性与人所感知的多样性总是相对应的。你永远也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什么样的显现被你所感知,以及如何感知,有何意义(参见阿伦特的《精神生活·思维》中的“导论”与“显现”一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现在我们只讨论阿伦特的《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这是她1959年接受汉堡自由市所授予她“莱辛奖章”时所发表的演说。
什么是阿伦特所理解的“黑暗时代”?她说,历史上有过许多的黑暗时代,它的特点就是“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况长了,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这就是《智者纳旦》中贯穿始终的一句体现主题的台词:“做一个人就足够了”。或者换一句话说:活着就行,还想怎样?
幸好我们已经是人,而且还活着,还想怎样?还要怎样?除了广场舞、各种健身方式,养生秘籍,我们还想、又能到哪里去寻找“人性的踪迹”?
于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智者纳旦》中的另一个主旋律就是“做我的朋友吧”。
在人生中,朋友总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该书第21页,我刚刚在杭州讲过什么叫“值得过的生活”,可惜没有想到这句话。)朋友,指的是“无须证明就被视为真朋友的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患难知真情”的朋友。
为什么她要强调“无须证明”?因为在她看来,当“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时,能够比较私密地进行言谈的人就是朋友。言谈什么?言谈政治。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言谈”本身就视为一种“证明”,但它毕竟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阿伦特说,对古希腊人来说,友爱的本质就在于言谈,也只有不断地言谈才能把公民聚集为一个城邦(polis)。谈论政治就是关心我们共同的世界,“这是由于,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对象时才会如此。”(同上)阿伦特说,她的意思是要讨论“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才能使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同上,第19页)
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更根本的了。莱辛从未与他的世界和平相处过。他认为激情,哪怕是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一种激情,都是让人快乐的。他最怕的就是当人们在抛弃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的同时,也抛弃了人性。于是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非人的世界。莱辛试图从恐惧中剥离出逃避现实的方面。于是就有了与恐惧相关的同情。是的,当我们感受到恐惧的同时,也一定感受到了同情或怜悯。但从另一面来看,无论是恐惧还是怜悯,都使人无法行动。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同情与恐惧都看成是纯粹被动、限制人行动的感情。恐惧比较好理解,说它是被动的感情,因为权力(暴力)总比个人的力量大,碾死个把人完全不算什么;同情为什么也让人被动呢?阿伦特说,因为古希腊的人把同情理解为胆怯,它其实是恐惧的另一面:恐惧发生在自己的外面,同情则是对自己的同情。尽管这里面可能有误导的一面,但毫无疑问,都会使人无法行动,不敢交谈。于是阿伦特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近一个时期,“外在移民”在我们国家已经蔚然成风,但对更多无法移民的人来说,不妨听听阿伦特的分析。她说:“这是一种奇特的暧昧现象。它一方面意味着,某些人身在德国但其行为却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家,他们在感觉上像是移民;另一方面它又说明,他们并没有真的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第16页)当然,与之相对,阿伦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内在未移民”:人已经走了,已经移民了,但心还在这里,也并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这都是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奇特的暧昧现象”。关键的问题在哪里?阿伦特说,“内在的移民”(在我看来,也包括“内在的未移民”)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遗产就是:人们把1933年到1945年这段历史当成仿佛从未存在过的一页,不但从史书上抹去,而且也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由于某种困扰,由于无法直面历史,由于大家都曾被直接卷入的有组织的犯罪,所以最好的逃避方式就是外在或内在的移民。阿伦特也假设,也许只有对“局外人”而言,才可能更好地交谈这个世界。交谈,特别是“叙事”(narrative),本身就是“对过去的征服”,因为叙事会把我们的生命经验作为新芽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于是就会不断激发人类潜在的可能性,它比我们活得更长,而且,“所有的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第19页)
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就是也许从未谋面的朋友。这也就是阿伦特所理解的友爱,双方都既没有不当的内疚感,也没有不当的优越感或自卑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友爱仅仅视为一种私密现象:彼此敞开心灵,不受当时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困扰,而是通过交谈,让过去的一切变得“属人”,也就是“人性化”。这种友爱,在古代的希腊社会也被称为“仁爱”(philanthropy),亦即“对人的爱”;到罗马帝国时,这种普遍性的“仁爱”或“善意”就在“人道”(humanities)的意义上有了许多的改变:因为罗马帝国种族庞杂,哪些人才能获得公民权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教养或教化就被提到了日常生活的议事日程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孩子在接受小学教育时,并不特别偏重于课程、作业,而是要学会与人交往,在交往方式上要显得有教养。阿伦特更看重的是交往中的友爱,这种友爱不是私密的个人行为,而是政治的要求和对世界的防护。《智者纳旦》中的冲突发生在友爱与真理之间。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亲亲相隐”——只是有点形式上的类似而已,因为对纳旦而言,他心目中所要维护的并不是“亲”,即父子或兄弟姐妹的关系,而是朋友间的友爱,这种友爱高于真理。
这并不是说莱辛不要真理,而是说真理一旦说出,便立即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不断地被人争论、重构,简化为谈话的话资。假如只存在一条唯一的真理,就等于宣布了谈话的死亡;而谈话的死亡,也就是人性的终结。
所以和康德比较一下,康德在道德上无疑是冷酷无情的,他提倡宁肯为了真理而牺牲友爱,因为道德的“绝对命令”至高无上;而莱辛则要温情脉脉得多,他通过智者纳旦告诉我们,在人性与真理之间,人们当然不会陷入康德的二律背反,而会更加婉转地寻找到一种妥协,因为友爱是可贵的,而真理则需要不断证明。既然没有谁说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那么“真理”这个概念就应该改换为更贴近我们生活经验的词语,比如“正确性”“客观性”“事实性”等等,但无论怎样,“任何学说,无论它们得到了多么令人信服的证明,它是否值得人们为之牺牲两个人之间那独一无二的友情呢”?(第26页)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真理往往是为政治服务的;一般来说,真理也就掌握在手握大权的人手中。那么我们也就由此看出《智者纳旦》是一个政治戏剧,而莱辛则是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正因为他关注政治,才相信真理只存在于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所以当莱辛说“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第27页)时,阿伦特说,这是一句在所有有关真理与人性之争中最为深刻的一句话。
也就因为这句话,阿伦特这个人,而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阿伦特,在我们的心目中也就渐渐清晰了起来。我看过一部有关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电影,那是一段她最为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也是她几乎就要丧失掉她维护了几十年友情的一段日子;但电影让我们牢牢记住的,除了她永远不停地在抽烟之外,就是热情地与人拥抱,哪怕刚刚猛烈抨击过她的人。然而该坚持的,她还是坚持住了。所有这些,我们只要看看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就清楚了。
对这个让她受尽了屈辱与苦难的世界,她有的只是爱;对那些与她一起从纳粹的魔爪中逃了出来的朋友,无论是犹太教的、基督教的,还是穆斯林,她都充满了友爱,当周围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个她深爱着的世界时,她给她的好友玛丽·麦卡锡写信说:“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树叶凋零’(或者叫‘树倒猢狲散’的过程使得我的感觉都有点麻木了。)好像衰老的过程并不——如歌德所说——意味着‘逐渐从现象世界引退’(我对此没什么反对意见),而是一个熟悉的世界(无所谓朋友敌人)逐渐(很突然)变成了一片充满了陌生的面孔的荒芜之地。换句话说,并非我引退,而是这个世界正在垮台。”
“并非我引退,而是这个世界正在垮台。”她竭尽努力地想挽救这个日渐垮台的、她所深深爱着的世界。但,这个世界还是垮掉了。
在她的写字台上,永远摆放着她的母亲玛尔塔·阿伦特的照片,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另一个就是她早年的恋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她并不赞同海德格尔的所有学说,认为这个人有一种“冷静的沉着”,表现为完全放弃了意志而听任事物存在。这既指的是他在纳粹执政时的一些往事,也可能包括当她晚年三番五次地去探望海德格尔时,这个人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当然也并不一直这样)。去世那一年的八月,她还去见了海德格尔,而结果比她预料的还糟。她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海德格尔现在突然间真的老了,与几年前相比变化很大,耳聋得很厉害,过着隐居的生活,拒绝和人交往,我以前从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这儿被那些突然之间变老了的人们包围着。”
她被变老了的人们包围着,她不知道她自己也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四个月后,她去世了,再过一年,海德格尔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或者无法想象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想与海德格尔谈些什么,我们只知道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是他“彬彬有礼的敌人”,而她自己在海德格尔八十华诞时写了一篇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文章,里面说海德格尔与柏拉图一样参与了政治,但他却始终不肯直面盖世太保的黑暗世界和集中营的刑讯逼供中的真实,这是一种“职业的畸形”。但所有这些话,都没有改变她对海德格尔在感情上的依恋。(参见阿洛伊斯·普林茨所著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的最后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这也许是另一种“人性的畸形”,即对人在交往上的执着,以及对事在探究上的不懈。
人生,就是人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中分享阿伦特的爱。这种爱贯穿在人与自己的关系(哲学),人与他人的关系(伦理学)和人与群体的关系(政治哲学)之中。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