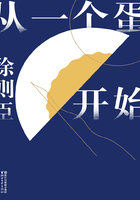我第一次遇见格伦·霍尔茨曼是在四月的某个星期二晚上。四月,据说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艾略特在《荒原》中如是说。那他总该明白他自己说这话的含意吧?我可不懂。对我来说,每个月份都挺难熬。
我们是在桑多尔·凯尔斯丁的画廊碰的面。那个画廊在五十七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一栋五层楼上。那栋楼里有不下十几个画廊。当天,一个现代摄影团体的春展开幕。三楼的一间大厅正在展出七位摄影师的作品。来捧场的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像莉萨·霍尔茨曼以及伊莱恩·马代尔这一行人。她们每星期四晚上在亨特学院修一门名叫“作为抽象艺术的摄影”的课。
桌上已经摆好了装着红酒、白葡萄酒的塑料酒杯,插着五颜六色牙签的奶酪,还有汽水。我为自己倒了一点,然后去找伊莱恩。她把我介绍给霍尔茨曼。
我只看了他一眼,就立刻断定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告诉自己,这太荒谬了。我跟他握了手,回以笑容。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四人在第八大道吃泰国菜。我们点了面,霍尔茨曼要了一瓶啤酒配肉吃,其他人则喝泰式冰咖啡。
我们之间的谈话一直没进入状况。一开始我们谈刚看过的展览,然后又随意聊了一会儿一般性的话题,诸如本地的政治、球赛、天气等。我已经知道他是律师,在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用大号字体重印已出版作品的出版社。
“挺无聊的,”他说,“大部分是合约。每隔一阵子,我得给人写封措辞严厉的信。哈,这可是一套我等不及要传后的本领。等我们的儿子够大了,我就教他怎么写这种信。”
“或是女儿。”莉萨接口道。
不论是女儿或是儿子,都还没出生,预产期在秋天。这是莉萨没喝啤酒改喝咖啡的原因。伊莱恩本来就不怎么喝,最近更滴酒不沾。而我,一天戒一次,也不喝。
“或是女儿,”格伦附和,“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跟着老爸重走这条无聊的路。马修,你的工作一定刺激多了。还是我电视看得太多,所以有这种想法?”
“有时挺刺激的,”我说,“但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例行工作,跟其他职业没什么差别。”
“在你自己出来做之前,你当过警察是吧?”
“不错。”
“现在,你给侦探社做?”
“他们来找我时,”我回答,“我替可靠侦探社工作,按日计酬,其他时间我自己接案子。”
“我猜,你一定处理过很多商业间谍的案子,一肚子怨气的雇员出售公司机密。”
“偶尔。”
“活儿不多?”
“我没有执照,”我说,“所以通常拿不到大公司的案子,至少靠我自己很难。侦探社是接过这种案子,不过他们最近找我办的多半与仿冒商标有关。”
“仿冒商标?”
“从仿冒劳力士手表,到运动衫或棒球帽盗用未经授权的商标。”
“听起来挺有意思。”
“不见得,”我回答,“以我们这行来说,就跟你写信逼人差不多。”
“那你最好有个小孩,”他说,“这正是你会想传给后代的看家本领。”
晚饭后,我们走到他们的公寓,非常尽责地赞叹从他们家看出去的景致。伊莱恩的公寓可以看到东河的一部分,从我的旅馆房间,则可以瞄到世界贸易中心,但可不能跟他们家相提并论。公寓本身倒不大,第二间卧室只有十英尺见方,而且像很多新盖的房子,天花板很低,粗制滥造,不过有这等视野,弥补了不少不足之处。
莉萨煮了一壶无咖啡因咖啡,开始说起个人征友广告,以及她知道有哪些正经八百的人都在用它。“不然,现在要怎么样才交得到朋友?”她质问,“格伦和我运气好,我带着我的书去见瓦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的艺术指导,居然就在走廊上碰到他了。”
“我在房间另一头,一看到她,”格伦说,“当下就采取行动,确定我们两人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
“但这样的巧事多久才发生一回?”莉萨继续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不介意我这么问吧?”
“征友广告。”伊莱恩说。
“真的吗?”
“不,事实上,我们多年前好过,吹了,也断了联络,然后我们又遇上……”
“而且过去的魔力还在?这可是个动人的故事。”
也许是吧,不过这个故事可经不起深究。我们是在多年前认识的没错,在一家开到深夜的酒吧。那时伊莱恩是个年轻甜美的应召女郎,而我是第六分局的警探,在长岛还有一个关系疏远的老婆及两个儿子。多年后,一个精神病杀手从我们共有的过去中突然冒出来,不杀我们两人誓不善罢甘休,于是又把我们弄在一起。不错,过去的魔力还在,我们找到了对方,厮守至今。
我也觉得这是个挺美丽的故事,但有这么些不便明说的情节,所以这个话题只能点到为止。莉萨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离了婚,应《纽约》杂志上的私人广告,到说好的地点准时赴约,结果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前夫。他们不禁感到冥冥中自有定数,宣告再度结合。格伦说他可不信,无稽至极,他听过半打类似的故事,但他一个也不信。
“都市神话,”他说,“这类故事满天飞,但总是发生在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从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人。事实上,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有些学者专门收集这类故事写成长篇大论,甚至还集结成册。例如那个旅行箱里装着德国牧羊犬的故事。”
我们看起来八成一脸疑惑。“哦,得了,”他说,“你们一定听过的。某人的狗死了,他心碎之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狗装进一只大旅行箱。然后,他不是要去找兽医,就是要去宠物公墓,反正就当他把箱子放下喘口气的时候,有人一把抢了箱子就跑。哈,你想想看,那个倒霉鬼打开偷来的箱子,里面没别的,就死狗一条,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我敢打赌,你们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那只狗是只杜宾犬。”
“杜宾犬,牧羊犬,反正是大型狗。”
“我听过的故事,”伊莱恩说,“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然,当然,而且一个热心的年轻男人自告奋勇要替她提箱子。”
“但箱子里面,”她继续说,“是她的前夫。”
都市神话就此告一段落,但莉萨仍兴致高昂。她的话题一转,谈到色情电话。她觉得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暗喻。它从健康危机中产生,用信用卡及九〇〇收费电话交易,因着愈来愈多人好幻想、意图逃避现实而盛行。
“而且那些女孩赚钱多容易,”她说,“她们只需要张张嘴巴就行了。”
“女孩?有一半恐怕是老祖母了。”
“那又怎样?年长的女人做这行可有这点好处。你不需要年轻貌美,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得有一颗色迷迷的心,是不是?你还得要有性感的声音。”
“我的声音够性感了吧?”
“当然,”他回答,“不过,这是我的偏见,可不能作数。你问这个干吗?别告诉我你想从事这行。”
“嗯,”她说,“我是在考虑。”
“你开玩笑吧?”
“哦,这可说不定,以后如果小孩睡觉,我又无处可去的话……”
“你真会拿起电话跟陌生人秽言秽语?”
“这个……”
“你可记得在我们结婚之前,你接到的那些猥亵电话?”
“那可不一样。”
“你吓个半死。”
“那是因为那人性变态。”
“是吗?你以为你的顾客会是怎么样的人?童子军?”
“如果能赚钱,那就又不同了。那就不是被骚扰,至少我不觉得。你怎么看,伊莱恩?”
“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行。”
“那当然,”格伦说,“你没那种肮脏心思。”
回到伊莱恩的公寓之后,我说:“身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你岂不占尽优势?只可惜你的心思不够肮脏,没法从事色情电话交易。”
“哈,这是不是很可笑?我差点想多说点什么。”
“我是以为你会多说的。”
“我几乎要说出口了,但又咽了回去。”
“嗯,”我说,“有时候是会咽回去。”
我第一次遇见伊莱恩时,她是应召女郎。我们再度聚首,她仍是应召女郎。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逐渐加深,但她并未改行。我假装毫不在乎,她也不露声色。我们只好避而不谈,让它成为一个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像是一头站在客厅里的大象,我们轻手轻脚地绕着它走,仿佛从来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们突然停下来,面对我们真实的感觉。我承认其实我在乎。而她告诉我,早在几个月前她就已经不干了。整个过程带着一种古怪的《麦琪的礼物》感。自此之后,我们不断调整,在一片茫然中寻找一条新路。
有一个她非得解决的问题是,她要何去何从?伊莱恩并不需要工作。她从来没有把钱交给拉皮条的,或抛给卖毒品的。她做了明智的投资,把大部分钱拿去买了皇后区的公寓。一家房地产公司代她全权处理,每月寄给她一张支票,再加上一些储蓄,足够她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伊莱恩喜欢上健身房运动,听音乐会,到大学进修,而且她又有身居市区的方便,永远不愁找不到事做。
但她一辈子都在工作,要适应退休并不容易。偶尔她会读招聘广告,边读边皱眉。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编一份履历表。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撕了笔记,大声宣布:“没救,完全没救,我甚至没法编出一套巧妙的谎言。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人上床,我可以声称我是家庭主妇,但这又怎么样?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色情电话怎么看?”
“嗯,聊胜于无,”我说,“当我们不能在一起时,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想,我会很难堪的,很难进入情况。”
“傻瓜,”她亲热地说,“我不是在说我们。我的意思是靠这个赚钱。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这很赚钱。你跟十几个女孩在一个大房间里,但每人隔出一间,所以有隐私。你就坐在桌边讲电话,一点也不必为顾客付不付钱烦恼,你也不必担心会得艾滋或疱疹。当然更没有任何人身危险,你压根儿不必面对任何人。你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你,他甚至不知道你名字。”
“那他们怎么叫你?”
“编个花名啊,只不过不是真的花名,因为你并不是真的在花街上。一个电话花名。我敢打赌,法国人一定有个专有名词称呼它,”她找了一本字典,翻来翻去,“他们叫‘电话之名’,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的提法。”
“那你想叫什么?特丽克西?瓦妮莎?”
“说不定就叫奥黛丽。”
“你根本早就想好了吧?”
“几个小时前我跟保利娜正谈到这事儿。想个名字要花多少时间?”她吸了口气,“她说她可以介绍我去她做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说,“真的很难说,你先去试试,再看我们感觉如何。你想去,是不是?”
“我想是吧。”
“以前有人是怎么说手淫来着?不干到戴老花眼镜,绝不罢休。”
“或戴助听器。”她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她就开始上班,但只做了四小时就退下阵来。“没办法,”她说,“我办不到,我宁可跟陌生人睡觉,也不能忍受跟他们淫声浪语。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是没法儿干。有个蠢蛋想要听他的那话儿有多大。‘大极了,’我说,‘从没见过比你更大的。老天,这么大,怎么能放进去?你确定这是你那话儿吗?我敢打赌那是你的手臂。’他一听非常恼怒。‘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以前可没有人说我不会做。‘这样胡乱夸张,被你搞得很滑稽。’哼,居然是我不对。我说:‘滑稽?你坐在那儿,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那玩意,付钱给陌生人让她来说你有多了不起,还说我滑稽?’我告诉他,他是个混蛋,然后就挂了电话。当然,我是不该挂电话的。这种九〇〇电话按时计价,只要他们还在线,我们就赚钱。所以只要他们不挂……我们就不挂……不过我可不在乎。”
“另一个神经病要我给他说故事。‘告诉我,你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一块儿干。’哼,我不是没有实战经验,但我干吗要告诉他这种无聊鬼?让他去死,我就顺口胡编。当然啦,三个人都很火辣,干得火热,配合得天衣无缝,同时爽翻天。简直是活见鬼。你真去试试看。有人一嘴口臭,有人一身暗疮。女的在那儿叫半天,男的却不举。”她摇摇头,一脸憎恶。“算了吧,”她说,“幸好我存够了钱,看来我没法找工作了,我甚至连色情电话的工作都做不了。”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说格伦和莉萨?他们很好啊,我愿他们一切如意。”
“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你也不在乎,是不是?”
“你说得过火了些,不过我得承认,对于没事时跟他们厮混我可不感兴趣。像今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彼此年龄有差距?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大太多啊。”
“她是挺年轻的,”我说,“不过我想这不是理由,最主要的是彼此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你跟她一起上课,我住在他们隔壁街区,除此之外……”
“我知道,”她接口,“是没有多少共通之处,这我早该想到。不过我看她挺讨人喜欢的,因此不妨一试。”
“嗯,不错,”我说,“我可以看得出为什么你喜欢她,我也觉得她不赖。”
“但不包括他?”
“是的,不包括他。”
“什么缘故呢?”
我想了一会儿。“呃,”我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可以指出一些他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就讨厌他。我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不是那种我会喜欢的人。”
“他长得不难看啊。”
“不错,”我说,“他是不难看。嗯,我懂了,说不定我察觉出你对他有兴趣,所以我就看他不顺眼。”
“哼,我可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你不觉得?”
“我觉得他好看,”她说,“就像男模特儿的那种好看一样,但不像现在流行的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不过我对漂亮的小男生没兴趣,我只爱脾气暴躁的老狗熊。”
“谢天谢地。”
“说不定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你对她有兴趣。”
“我还没看到她之前,就讨厌他。”
“哦?”
“而且我为什么会对她有意思?”
“她很漂亮。”
“像个一摔就碎的瓷娃娃,一个脆弱而且怀孕的瓷娃娃。”
“我还以为男人最容易对孕妇着迷。”
“哼,你最好再仔细想想看。”
“安妮塔怀孕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忙着加班,”我回答,“把一大帮坏蛋送进牢里。”
“就跟她没怀孕时一样?”
“嗯,差不多。”
“说不定你警察的直觉,”她说,“才是你不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吗?”我说,“我想你说对了,但这实在毫无道理。”
“为什么?”
“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有个怀孕的老婆,一套高级公寓,迷人的笑容,与人握手也很有劲,我干吗会觉得他有问题?”
“你自己说呢?”
“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听我说话时全神贯注,好像想听出一些我不愿告诉他的隐私。今晚的谈话是很没劲,但如果我讲一些案子,那会大大不同。”
“那你怎么不说呢?”
“说不定正因为他太想听了。”
“像是色情电话?”她说,“他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他那话儿。”
“是有点像。”
“怪不得我想摔电话。老天,你可记得上回的惨剧,足足一个星期,我上了床简直不能开口。”
“我记得,你连哼也不哼一声。”
“哦,我不想那样的,”她说,“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装出一副纳粹的腔调:“我就是有办法让你达到高潮。”
“你说真的?”
“我想,这位女士显然要求实证。”
“那就证明给我看。”
隔了好一会儿,她说:“好吧,我得承认今晚并不特别愉快,不过至少结尾很不错,嗯?我想你大概没错,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对劲,但管他的,我们再也不必看到他们了。”
当然,我又见到他们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星期之后,有天晚上,我走出我住的旅馆,在第九大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不是别人,正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穿西装,拎着一只公文包。
“今天他们留我办事办晚了,”他说,“我告诉莉萨先吃,不要等我。你吃过晚饭没?要不要去哪儿吃一点?”我已经吃过了,我告诉他。“那么,你要不要来杯咖啡,陪我聊聊?我并不去什么时髦地方,不是火焰,就是晨星,你有空吗?”
“老实说,”我回答,“我正巧没空。”我指向第九大道,“我正要去见一个人。”我说。
“好吧,那我跟你走一程,我会乖乖到火焰那儿要个希腊沙拉,”他拍拍腰围,“免得发胖。”他说。其实我看他已经够瘦了。我们走到五十八街,过了第九大道。在进火焰之前,他说:“我进去了,希望你的会面顺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吗?”
“就目前的阶段看,”我回答,“实在很难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案子。这是一个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举行的匿名戒酒会。一个半小时里,我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用一只一次性杯子喝咖啡。十点一到,我们含糊地念过主祷文,堆好椅子,然后一伙人一块儿到火焰去要点吃的,听大家闲扯。我以为可能还会撞上霍尔茨曼在那儿细嚼慢咽他的希腊沙拉,不过他已经走了,回到他高空中的小屋。我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英式松饼,就此忘了他。
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我曾看到他在第九大道上等公共汽车,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我。还有一次,伊莱恩与我很晚在阿姆斯特朗吃东西,我们离开时,霍尔茨曼正巧在对面他们家的大楼前下了出租车。另外一天下午,我站在窗前,一个很像霍尔茨曼的人从对街的照相馆里出来,往西走去。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只是那人走路的样子及举止让我想起了霍尔茨曼。
直到六月中旬,我们才再度说话。那是一个周日,而且已经很晚,至少过了半夜了。我去了匿名戒酒会,之后又去喝咖啡。回房间后,我拿起一本书,就是看不进去,开了电视,同样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尽力耐住性子,不愿像这样坐立不安。挣扎到半夜,我骂了一声,一把抓起夹克走了出去。我往西南方向走,走到葛洛根酒吧时,进去坐了下来。
葛洛根位于第五十街与第十大道的交会处,是一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过去这种酒吧在地狱厨房这一带很多,但现在逐渐少了。不过葛洛根倒也没有因此赢得一块地标保存委员会的铜牌,或是跻身于濒危物种名单上。进门后,左边有一个很长的吧台,右侧则是餐桌及雅座。后面墙上挂着一块飞镖盘,瓷砖地上散布着锯屑,头上老旧的锡制天花板该修理了。
葛洛根很少有人挤人的时候,这个晚上也不例外。伯克在吧台后看有线电视放的老电影。我叫了可乐,他给我送过来。我问米克来了没。他摇摇头说:“过会儿。”
对他来说,这句话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葛洛根的酒保一个个都沉默寡言。这是在葛洛根干酒保的必备条件之一。
我一边啜着可乐,一边环顾四处。是有几张熟面孔,但都没有熟到我可以去打声招呼的。于是我开始看电影。我不是不可以在家看同样的片子,但我不只看不进任何东西,连坐也坐不住。而在这里,被烟味及溢出来的啤酒味所包围,我奇怪地平静了下来。
屏幕上,贝蒂·戴维斯叹了口气,一甩头,看起来比春天还年轻。
我试着专心看电影,正逐渐陷入沉思漫想之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我转过头,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穿黄褐色风衣,里面一件格子衬衫,我第一次看到他没穿一身正式的西装。
“睡不着,”他说,“我先去了阿姆斯特朗,但太挤了,所以就来这儿。你喝什么?健力士?嘿,你的杯子里有冰块,这里是这样调酒的吗?”
“这是可乐,”我答道,“不过他们有健力士生啤。如果你想要在酒里加冰块,我想他们一定照办不误。”
“我可没兴趣,”他说,“加不加都一样,嗯,我想要什么呢?”伯克就站在我们前面,仍旧一言不发。“你有哪种啤酒?算了,我不想喝啤酒,还是来杯红标尊尼获加吧,要冰块,加点水。”
伯克拿酒过来,旁边放着一小樽水。霍尔茨曼在他的杯里加了水,拿起杯子对着光,之后啜了一小口。过去喝酒的回忆立刻漫上我心头。现在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来一杯,但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尝到了酒的滋味。
“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不过我很少来,你呢?”
“我也觉得这地方不错。”
“常来?”
“不常来。不过我认得这家店的老板。”
“是吗?是不是那个被称为‘屠夫’的家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这样叫他,”我说,“我想是新闻记者给了他这么个名号,大概也是同一个人开始管地痞无赖叫‘西方汉’。”
“难道他们不是这样自称的?”
“他们现在才这样叫,”我说,“过去可不。就米克·巴卢来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叫他‘屠夫’。”
“如果我太莽撞的话……”
“别担心,无所谓的。”
“我来过这里几次,大概四五次吧,从没碰上他。不过我大概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块头很大,是不是?”
“不错。”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嗯,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我说,“很久以前,我们就这么碰上了。”
他喝了口威士忌,说:“我敢打赌,你有一肚子故事可说。”
“说故事我可不拿手。”
“是吗?”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有空跟我吃个午饭吗?马修,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如何?”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希望你会打来,”他说,“我真想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天知道,说不定我们会谈出点什么来。”
“哦?”
“比如说,出本书。想想看,你的经验,你认识的人。如果说有本书正等着你来写,一点也不为过。”
“只怕我写不了。”
“只要我们有材料,找个作家跟你合作一点也不困难。我可以感觉到材料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一块儿吃午饭时可以多谈谈。”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我决定等电影一完就离开。但电影没完,米克倒出现了。结果我们混了一整个晚上。我告诉霍尔茨曼,我并不擅长说故事。但那个晚上我说了我的,米克也说了他的。米克喝苏爱尔威士忌,我则喝咖啡,直到伯克把椅子倒放在桌上关起店门,我们都没停嘴。
等我们终于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米克说,“然后就该去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
“我可不成,”我说,“我太累了,想回去。”
“啊,你这人真没意思。”他说,然后送我回家。“聊得真高兴,”当我们到了我的旅馆时,他停下来说,“只可惜结束得太早了。”
“天底下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告诉伊莱恩,“就是写本书絮叨我的精彩经历。就算我愿意考虑,也不会跟他合作。他一开口,我就不由自主地想逃。”
“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起来找我出书。他的公司专门出版大号字体的书,何况他又不是编辑,他只是一个律师。”
“说不定他认识别的出版社的人,”她指出,“再说,难道他不能以安排出书为副业?”
“他正在进行某件事。”
“什么意思?”
“他暗中有个计划在进行,想弄点什么的,但他没说出来。我告诉你,我不信他真要找我写书。如果他真要找我写书,他应该还会有其他建议。”
“那你猜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不难发现,”她说,“就跟他吃顿午饭不就行了。”
“我可以这样做,”我说,“但也可以不必知道。”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下午时分,我坐在晨星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吃派喝咖啡,读邻桌留下来的《新闻日报》。报页上落下一片阴影,我抬起头,是霍尔茨曼,站在玻璃窗的另一面。他松了领带,领口敞开,西装上衣搭在手臂上。他微笑着,指指自己,又指指入口。我猜他的意思是要进来和我坐一起。我猜对了。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马修。不介意我坐下来吧?还是你在等人?”
我指指对面的椅子,他就坐了下来。女招待拿了菜单过来,他挥手把她赶走,说他只要咖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电话,等着跟我见面吃午饭。“我猜你一直很忙。”他说。
“是很忙。”
“我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我说,“说真的,我并不想写书。就算我有东西可写,我也宁可不写。”
“别再说了,”他说,“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谁说你非得写书,我们才能一起吃饭?我们总可以找到别的话题聊。”
“嗯,当我不忙的时候……”
“当然。”咖啡已经到了,他皱眉瞧了一眼,拿起餐巾抹抹眉。“我不知道我干吗叫咖啡,”他说,“天这么热,喝冰红茶还有点道理。不过,这里也算凉快了,是不是?谢天谢地,这儿有冷气。”
“阿门。”
“你知道吗?在一般的公共场所,夏天温度调得比冬天还低。如果在一月保持这样的温度,我们早就向经理抱怨了。难怪一般人老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会有能源危机。”他对我报以殷勤的微笑,“你看,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天气啦,能源危机啦。就当是美国民族性的特色吧,不怕吃午饭时会没话可说。”
“就怕时间没到,话题已经用完了。”
“哦,我可不担心。伊莱恩最近如何?自从课程结束后,莉萨就没见到她。”
“她很好。”
“她暑假有没有选课?莉萨本来想选的,后来她觉得怀孕可能对学业有影响。”
我说伊莱恩在秋季可能还会去选课,不过她决定把夏天空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共度长周末。
“莉萨说要找她,”他说,“不过我想她大概还没行动。”他搅了搅咖啡,忽然他说:“她流产了,我想你大概不知道。”
“老天,我真替你们难过,格伦。”
“谢谢你。”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清楚,大概十天前吧。胎儿差不多都有七个月了。还好,情形本来会更糟。他们说,胎儿是畸形,本来也活不了的。假如她真的怀胎足月生下来了呢?恐怕结果更令人伤心。”
“我懂你的意思。”
“是她想要小孩的,”他说,“没有我也不在乎。虽然我无所谓,但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想就要吧。医生说我们还可以再试。”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要,但绝不是现在。说来好笑,我原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些的。你瞧你是多好的侦探,不必开口问,就有人自动对你倾诉。我还是让你继续看报吧。”他站起来,向我推了两块钱过来。“咖啡钱。”他说。
“太多了。”
“那你就多留点小费,”他回答,“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一定得一起吃个午饭。”
我把我们之间的谈话转告给伊莱恩,她立刻起身打电话给莉萨。她打了电话,传来的是答录机的声音,她没留言就挂断了。
“我突然想到,”她解释着,“不需要我的帮助,她也可以应对她自己的伤心事。我们不过是一起上过课,课在两个月前就结束了。我是替她难过,真的,但我何必干涉她的私事呢?”
“是不必要。”
“这是我的决定,说不定我真从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①那儿学到了什么。如果我不是每隔三四个星期才去一次,可能我学到的会更多。”
“太可惜了,你并不喜欢去。”
“那些人老是在捶胸顿足,自怨自叹,简直令我作呕。不然的话,去那里确实有帮助。你怎么样?格伦告诉你他的伤心事后,你是不是对他有点好感了?”
“这是很自然的吧,”我说,“不过我仍不想跟他吃午饭。”
“哦,我看你别无选择,”她说,“他会不断黏着你,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从梦中惊醒,发现他是你最新的好友。你等着瞧吧。”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之后的六七个星期一晃而过,我既没有遇到格伦·霍尔茨曼,也没有想到他。但一个持枪的人改变了这一切,从此,不同于他生前,格伦常常停驻在我的心头。
注释:
①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Al-Anon)是一个成立于一九五一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向酗酒者的亲友提供帮助。